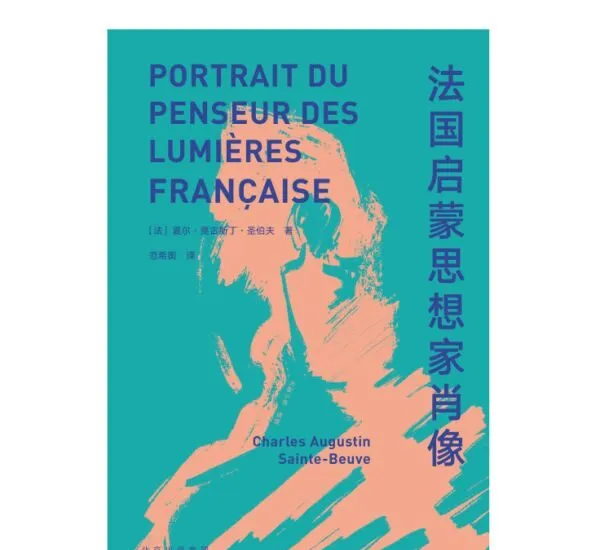
文丨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
伏尔泰是18世纪唯一真正的、唯一伟大的诗人。他的想象力永远是在那里。就整个的伏尔泰来说,他的作品常有差失,但是只要他的人在那里,诗人也就在那里。他是诗人,在一切自然流露中,在他的笔下一切无意的涌现中,小品文也好,讽刺诗也好,慧黠语也好,歌头也好,生就是谚语的警句也好,不管是什么题目,都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不胫而走地到处流传着。他还是诗人,在谈话里,由于慧心的迸发,由于灵机的不断闪烁,由于他说任何事物时都有那么一种活泼妩媚的语致。但是,他一受不到这种直接迸发的支持,一用心写文章,他就弱了,风格就不够了。在史诗和悲剧里,他都只满足于把他的时代应付过去,也就是说把那一个最缺乏诗意的时代应付过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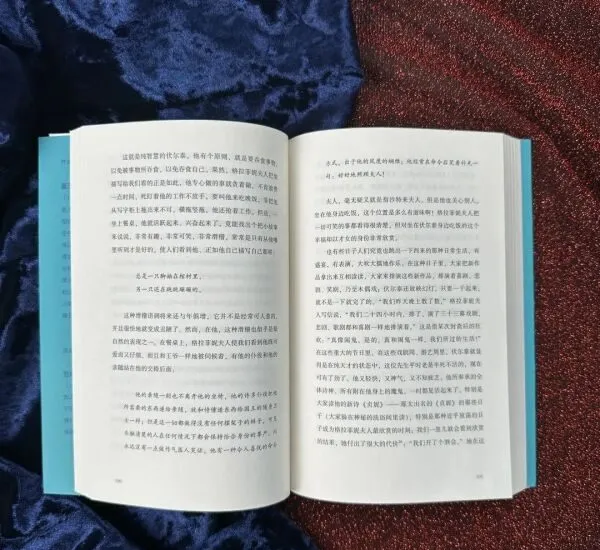
伏尔泰尽管有他的奇异的才华,却没有——大着胆子说罢——却没有适宜于赋予死者以不朽,给死者保证一个最后的、不凋的花冠的那种东西。是不是只在这种场合下他缺乏那种抒情号角的嘹亮声响呢?毫无疑义,在他那种种不同的天赋中,这种抒情的天赋他是没有的;他是个妩媚可人的诗人,活泼泼的,诙谐起来无法可学,甚至也有阵发的感动力,飘忽的柔情和闪电一般,但是他既没有形象的辉煌,又没有格调的壮丽,也没有班达尔所谓之「嘹亮的缪斯的纯粹光明」。他在他的才调中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那同一诗人所说的,并以其本身作为明显实例的另一句话:「语言从深刻的智慧中抽绎出来的文辞,再遇到妩媚之神,就能比行为更活得长久些。」妩媚之神,他是常遇到的,他很乐意亲近她们,但是那都是些家常的妩媚之神;而班达尔所要求的另一条件,深刻,他就没有了。他的缪斯在内心里太放荡了,口头上自难有持久的神圣情感的流露。因而,特别是在这里,既然这里是要对一个死者致敬意,我们就明白感觉到他所还需要的是什么,他还需要类似博叙埃热情的东西,不说类似班达尔的热情了。文辞的庄重、尊严,学理的尊严,那种出于信仰泉源的、口诵而心惟的灵魂不灭的思想,由说话的人扩及被颂扬的人身上,用他们的纯化了的懿德把他们裹起来,像一层洁白的、不朽的尸布,这一切,他都没有;同时,我们也该说,那位慷慨而高贵的邦主夫人所留下的印象也不适于引起这种宗教感。她的讥讽和她哥哥的讥讽太相近了;哪怕诗人再悲壮些、再庄重些,她的讥讽都够破坏他的愿望,搅翻他的意匠。佛勒德利克,请好好注意这一点,此时的做法几乎是与他生平所持的原则自相矛盾的。他要人家为他的妹妹做的是什么呢?他向诗人要求,向诗人索取一个苦痛的洪亮呼声,一种公开的、持久的、显赫的崇敬。但是,在这种庄严穆肃的动人时刻,他们都吃了自己的学理的亏了;他们此时却发觉了一种无法补偿的心灵枯窘。唯一的挽词,一个真诚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所能想到的,倒该是这样:「一切都完了,这是无可挽救的:我们自己明天也将同归于尽。我们沉默地哭着罢。」伏尔泰倒不是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但是题目却引着他走向这条路,所以就写出了一首振奋多于哀感的琴歌,费尽了平生之力;他叫道:
呵!巴蕾特啊!你,可佩的懿德与风姿!
你,无成见的奇女,无邪恶又无差错,
死神把你夺去了,从这可悲的尘世,
从这些杀人越货、惨象无穷的邦国,等等

但是这种趋势支持不下去;文笔接不上来了,韵律已经不算是完备的,但是就意思来说还是太宽,作者的思想由于作意求高、求充满这个韵律,结果疲乏了。伏尔泰暴露出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弱点,在最初发表这首琴歌时不得不以注释形式加上、连缀上种种与本题无关的廋语,都是些对哲学的敌人以及对自己的敌人的谩骂:他在这里特别看到一个机会,对全世界再散播一番讥刺,把它塞进这位著名的亡人的衣褶里。在这种庄严的哀悼中来运用缪斯们的、运用这些神圣使者的翅膀是太不合适的呀。
【法国启蒙思想家肖像】
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 范希衡译
北京出版社
审核丨猫娘
编辑丨阔洛 饱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