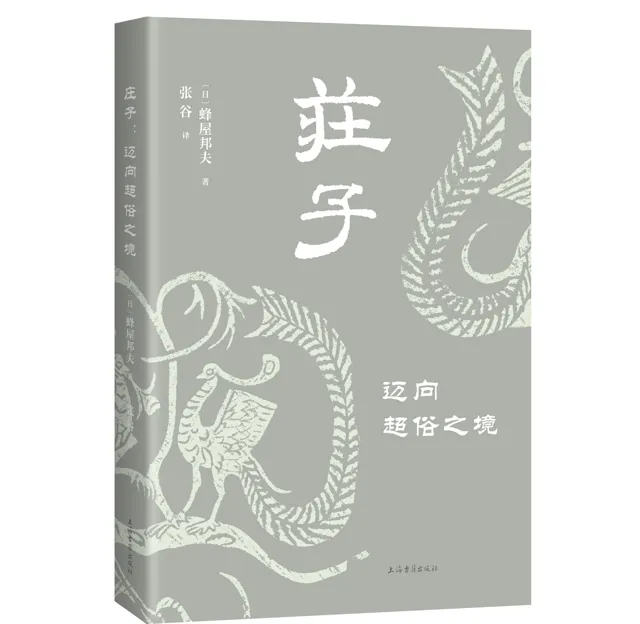
【庄子:迈向超俗之境】,作者:[日]蜂屋邦夫,译者:张谷,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5月
有死的存在者
我们都是作为有死的存在者在世上享有此生。即便有何时、何地、如何死等区别,在最终都会死这一点上,古今东西,没有一个例外。每个人都是主角,不是配角,不是旁观者,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之所以产生众多哲学和宗教的原因。
当然,庄子也对生死问题进行了种种思索。在这一点上,他与孔子有着显著的不同。当弟子子路询问生死问题时,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而岔开了话题。孔子意在劝诫,比起死亡,现实社会的问题更应该关注,但是,他非常尊崇以丧葬礼仪和祖先祭祀为中心的礼制体系,反复向弟子们教授仪式的程序和内在精神,并没有忽略死的问题。只不过,死作为当时社会中的事件而被深刻地社会化了。
与此相对,庄子是把死作为死本身来思考的。正因为如此,庄子的思想具有穿越两千数百年时空而逼近生活于异域的现代人的力量。人虽是历史性的存在,但仅在生死这一点上,又是超历史的存在。我们之所以能从庄子思想中直接学到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与庄子处在同一界域中。
上面已经对庄子及其思想做了各种考察,最后我们来看看,庄子关于死这个人生最重要问题的思考。

庄子像。
「寿则多辱」
近年来,由于人的寿命延长,死不再是本人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变成周围人的重大问题,真是使「寿(长寿)则多辱」(【天地】篇)成为现实了。从死的当事者性这一点来说,死对周围人而言无论是多么重大的问题,都还是另一个问题。顺便提一下,「寿则多辱」一句,兼好法师也在【徒然草】第七段引用过:「作为过客暂居于世上,等待老丑之年的必然到来,到底所图为何呢?寿则多耻。」这一段对【庄子】的引用很明显,不过,兼好是在寿命过长就会变得丑陋、羞耻心丧失而不成体统这个意义上引用的,他称这是「对人情物趣一无所知」。 「辱」和「耻」意思相同,耻辱一词就是两字合成的,但中文「耻」的原意是名誉受到损伤而感到羞耻,史载宋荣子倡导「见侮不耻」之说。相对于「耻」,「辱」则属于身体性的,是受到身体上的损害而具有的屈辱感。兼好在多大程度上严格区分此二字,还不清楚,不过,他似乎通过将原文的「辱」读为「耻」,而把庄子思想勉强解释为日本式的「物哀」审美感。
秦失吊老聃
如果不能逃脱死,在身心两方面都与痛苦相伴的话,对此的超越也应该涉及身心两个方面。但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在两千数百年前的条件下,从身体层面采取什么措施几乎不可能,而势必专门从精神层面来寻求超越。【庄子】中对完成超越后状态的描述很多,而关于庄子实际面临烦恼的叙述很少,但是,有许多小故事是围绕死展开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庄子及其后继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之深。
那么,就来读几个故事吧。首先,内篇的【养生主】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老聃去世了,秦失去吊唁,只是行了哭号三声的礼仪就出来了。于是弟子就问:「先生不是老聃的友人吗?」秦失答道:「是的。」弟子质问:「那么,这样吊唁可以吗?」于是秦失回答道:「是可以的。开始我一直以为他是老聃这个人(吾以为其人也),但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刚才我进去吊唁时,老人哭得像失去自己孩子一样,年轻人哭得像失去自己母亲一样。他们为老聃而聚集于此,一定是老聃不希望吊唁却来吊唁,老聃不希望哭号却来哭号。这些行为是逃遁天的道理,违背人的实情,忘掉受之于天的本分,古代称之为遁天之刑。应时而生,是老聃的机缘(时);随时而死,是老聃顺应道理(顺)。如果能安于时,置身(处)于顺,哀乐之情就不会进入内心,古代称之为帝之悬解。」
因为是从吊唁处出来后的对话,所以这个「弟子」应该是秦失的弟子。那么,这就是弟子在责怪他的老师礼仪太简慢了。老聃就是老子,把秦失设定为老聃的友人,这是虚构的。
「号」是在形式上哭出声的吊唁方式,「哭」是因悲伤之情而流泪并出声的哭泣。有恸哭的说法,「恸」是无所顾忌地悲泣痛哭,是偏离了礼的规范的。在此意义上,「号」和「哭」都是符合礼的规范的吊唁方式。像失去孩子或母亲那样哭泣的描写,显示出这种「哭」是接近「恸」的。在秦失的眼里,这些都背离了天的道理。
关于「以为其人也」的解释,是存在疑问的。原文作「其人」,也有的版本作「至人」,这样的话,意思就变成:「原以为是卓越的人,现在不这样认为。」比较起来,解释为「一直以为是老聃这个人」,似乎更接近庄子的思想。另外,还有「其人」非指「老聃」而是指他的弟子的解释,这样,意思就变成:「以前以为老聃的弟子非常优秀,但看到现在的表现就不这样认为了。」古籍的解释的确非常棘手,不过,这个解释是最缺乏动人力量的一个。
「遁天之刑」和「帝之县解」
无论是采「其人」说还是「至人」说,这个故事的要点都在于「遁天之刑」和「帝之县解」。就是说,人应时而生,应时而死,这是天地之间自然的运行。为情所动而沉浸于悲伤之中,就忘却了这种人之为人的本质,这正是「遁天之刑」,即因逃避天的道理而受到刑罚。
「帝之县解」的「县」与「悬」同,是垂吊、悬挂之意,「解」是解开、解放,「县解」意为从束缚中解放。「帝」即天帝,也就是绝对者,换言之,就是「遁天之刑」的「天」。因而,「帝之县解」就是为天所解放,也就是天地自然的解脱。这种存在方式必然是「安时处顺」的,就是将一切都托付给自然的运行而不执着于生死的存在方式。
三世纪的注家崔譔所谓「以生为县,以死为解」,是认为「县解」指从生中解放,这也是有所见的,但与下面的故事结合起来看,还是解释为「安时处顺」的境界这一观点更好。
莫逆之友
内篇的【大宗师】中有一个故事,生动地描写了人临终前的情景。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故事先描写子祀等四人成为挚友。「莫逆于心」是相互完全接受对方,成语「莫逆之友」就来源于这个故事。无为头颈,生为脊骨,死为臀股,这是说,我们从无中出生,经过一生,最终归于死亡。因此,生死存亡就成为「一体」。「一体」的意思,是拥有一个身体,也就是结构,而并不是说生死存亡是相同的,结构在这里是指整个生死的过程。所谓「遂」,是说事情是顺畅地推移的,而毫无「终于……」这种结局意外的感觉。
「以予为此拘拘也」
此间,子舆得了病。子祀前去探望,子舆非但没有消沉,还把自己身体的变化看作大自然的变化而享受着:
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拘拘」是身体蜷缩不能伸展的样子,用老话来说,也就是佝偻。「造物者」就是创造万物者,有时也称为「天」或「道」。
子舆的身体变成了这样: 脊背弯曲向上隆起,内脏移到了身体的上部,头朝下沉而使脖子比肩膀还低,因而发髻朝向上方,颌部比肚脐还低。
古代中国人认为,疾病是由体内阴阳二气的失调紊乱引起的,气的失调紊乱是难以忍受的,即使如此,子舆的内心依然平静而无事。他踉踉跄跄地走到井边,以井水自照,又说道:「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臂化为鸡和弓,臀化为车
以下是庄子风格的表述。子祀问子舆,变成这副模样是否感到厌恶,子舆尽管身患绝症,濒临死亡,却回答得富有幽默感:
不,为什么厌恶呢?随着身体的变化,如果左臂变成了鸡,那就来报时吧!如果右臂变成了弹弓,那就用它打一只鸟烤着吃吧!如果臀部变成了车轮,精神变成了马,那就乘坐吧,这样也就不需要驾驭马车了!
仔细想来,这个回答实在令人震惊。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臂,的确与鸡足相像。引文中的弹弓,类似旧时小孩子玩的Y字形弹弓,是用弹丸而不是箭射击的弓,这个弹弓正像是手臂弯曲僵硬而完全不能伸开的样子。
至于臀部变为车轮,人的筋肉下垂而腰骨外露,看起来正是车的样子。现在,我们大多是在医院里面对死亡的到来,但在过去,死亡就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场所中,谁都知道人死去的样子,臀部变为车轮的说法是对临终状态的如实描写。「神」变为马的说法不好理解,「神」大概是指寄寓于身体内的神灵,后来在中国产生的宗教——道教中,有人相信身体各部分都有神灵的存在,可以认为,这些神灵是上述古代神灵经过宗教性的发展的产物。
原文中说子舆的心是平静的,与此有微妙关系的是,古代中国人相信人的思维是心脏的活动,因而这个「心」表现了心情与心脏两个方面。就是说,「心」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是本来就内在于人的,而「神」则更倾向于与外部的关联。
子舆说,如果臀变为车,神变为马,乘坐即可,没有必要再驾乘现实中的马车了。更进一步来讲,也就是在说: 这不是很便利吗?
这样看来,子舆深知,一切变化都不过是造物者宏大作用的体现,由于彻底地融入自然的运行而撇开了自身去看待事物,因而能够随顺而享受这一变化。当然,悲喜之情是不进入内心的,所以虽然看起来快乐,实际上只是对顺应变化这一状态的譬喻。这里之所以能带来幽默感,是由于将常识所认为的悲惨的身体变化包裹在悠然的精神之中而完全加以承认的缘故。
「安时而处顺」
子舆接着说了下面的话,这与上述秦失的议论类似。
且夫(而且本来)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与秦失所说的话合起来看,这里所谓的或得或失之物,无疑就是「生」。在对「县解」加以解释后,接着分析,之所以不能「县解」是因为「物有结之」,也就是说,「安时而处顺」是自我内在的状态,不彻底实现这种内在方面的解放,心就会因「物」即外在的事物而受到牵累。「物」不必是特定的物,可以是任何物,例如在此处,子舆的身体、病症等也可以看作是「物」。
子舆说,在「天」这一宏大自然面前,一切事物终归是只能顺从的无力的存在,从来都是如此,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厌恶这个佝偻病呢?
在这里,丝毫没有把「物」作为对象而客观地探索其运行的所谓科学的精神,即使谈论「物」,也认为「物不胜天久矣」,而在源头处就关闭了对「物」的兴趣。在庄子看来,「天」就是如此拥有绝对的力量。
不过,如果「安时而处顺」并将一切都交托给「天」,的确能获得精神的宁静,这与其说是哲学性思维的产物,不如说更接近某种宗教性的情感。如果说庄子的文章对人具有疗愈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宗教性情感一定是其因素之一。
「为鼠肝乎」,「为虫臂乎」
接着,子来也病了,病得很重,「喘喘然(呼吸急促的样子)」地很快将要死去。子犁去探望子来,妻子和孩子正围绕着子来悲伤地哭泣。这里没有用「号」或「哭」,而是用了一个「泣」字,「泣」是不太出声而流泪的哭泣,也就是低声啜泣,可以说,这种啜泣才体现出家人深深的悲伤之情。
但是,子犁却说:「叱!避!无怛化(天地自然的宏大运作)!」而将家人支开,开始与子来对话。
(子犁)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这是一个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终极性的提问。「造化」是指大自然的运行,与「天」「道」「造物者」等并列而为庄子所擅长的词语。
「造化」一词也深为日本人所了解,例如,芭蕉在【笈之小文】序文中有「此类风雅人物,顺从造化,以四时为友」「顺造化而归于造化」等表述。
在伟大的造化运动中,子来究竟将变成什么?去向哪里?变成鼠肝还是虫臂(有版本作「肠」,若与「肝」对文,则作「肠」更切当)?这一提问,体现着一种转生的思想。人死后成为别物的思想,不只中国有,在古代其他国度也并不罕见。但是,【庄子】中的转生思想,也有为论述而使用的修辞的意味,很难说是被严肃地、虔诚地加以信仰的。
生死是气的聚散
外篇【知北游】中有这样的表述:
生也(所谓生)死之徒(伴侣),死也(所谓死)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聚集)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所谓「气」,在狭义上是类似「灵魂」的东西。说得再严密一些,可以看作是灵魂的构成元素。因此,也有「魂气形魄」这种常见的说法。「魂」(阳性的灵魂)结合于「气」,相应地,与作为身体的「形」结合的是「魄」(阴性的灵魂)。「气」聚集而寄寓于身体则为「生」,它的解散即为「死」。然而实际上,从广义上说,身体也是气的聚集,生命活动就是气的活动,所以问题就复杂了,在此意义上,魂、魄皆为气,气的聚集既构成身体也构成心灵。在上述故事中,秦失把死去的老聃说成已经是「非人」,这也可以解释为老聃这个人的气解散了。
在古代中国,一般认为人死后就变成鬼。这个鬼不是「魔鬼」,按日本的说法,就是「幽灵」,不是怨恨生者而变成鬼出现,而仅仅是死者的存在形态。因此,若用气的观念来解释的话,可以说,鬼也是一种气,就是说,魂气没有完全散去而停留于生者的周围。【庄子】中有关生死的议论,折射出人们的这种庸俗的想法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
上述【知北游】篇的议论是说,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而又散,散而又聚,这是无限循环的,如同鸡和卵一样无人知道哪个在先,因而就导向没有必要忧虑死亡的解释。根据气的聚散清楚地对生死加以解释,在【庄子】书中也是相当新的思想。【庄子】用气的观念将人们对生死的无尽思索做了一个明确的了结,这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所达至的终极理性的思想。
遵从阴阳的命令
如果生死是气的聚散现象,那么就能相应地解释说,人死之后,其气解散,以怪异的方式聚集就成为怪异之物。但是,子来和子犁的对话并不是那样好讲小道理,而是更加豁达和气度宏大。对于子犁的提问,子来这样回答:
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父母说向东孩子就向东,父母说向西孩子就向西,孩子总是听从父母之命。但是,阴阳的运行对于人来说,岂止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它是绝对性的。现在,伟大的阴阳运行让我走向死亡,我不听从它的吩咐,就是任性随意,阴阳又有什么错呢?
这个「阴阳」与「天」「道」「造物者」等意思相同,就是指造化的运行,这是着眼于气的自然运化的表述方式。「听」是听到并牢记的意思,也就是听从别人所说的话,与意为仅仅听到声音的「闻」是不同的。
死是大地赐予的休息
接着,子来语出精彩: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块」意为巨大的块,即指大地。大地以形体承载我,意思是人随着身体而诞生于大地之上。接下来,「劳」是劳动,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就劳作,「佚」是逸乐,进入老年后就安乐地生活,「息」是休息,死当然就是休息。因此,肯定自己的生为善,恰恰也就是肯定自己的死为善。
这一表述在【大宗师】篇开始部分也出现过,似乎是庄子喜爱的表达方式。大地与自己之间没有任何疏离感,真正在大地上悠然地活完天赋的生命。彻底地肯定生,也就彻底地肯定死,这看似简单的表达,实际上不正是蕴含着重大的真实吗?
锻冶的名匠
子来继续说:
锻冶的名匠正在铸造铁器,如果铁跳起来说「我一定要成为镆铘(古代名剑)」,那么锻冶的名匠必定认为这块铁不吉祥。现在,如果一朝获得人的形体,就说「一定要成为人、一定要成为人」,那么造化者必定认为是不吉祥的人。现在,如果把天地当作一座大炉,把造化当作锻冶的名匠,那么变成什么不可以呢!成然而眠,蘧然而醒。
这是子来对子犁「你将变成什么、去向何处」这一提问的直接回答。意思是说,伟大的刀匠在锻造刀剑的时候,如果作为铸造材料的铁跳起来说「我一定要成为镆铘」,刀匠必定认为这块材料是不祥之物。把天地看作一座大冶炉,是与把天比作辘轳同样的设想。
用天地之炉锻造器物
子来说,造化与铸剑名匠是类似的。天地犹如一座巨炉,用炉制造器物,就是造化的运作。因此,万物皆由天地大炉铸造而出。已经被铸造为人的,在重新铸造之时,如果仅为铸造的材料,却嚷着:「必须成为人!人!人!」造化者必定会认为是不祥之人,这就不是所谓「善吾死者」了。
「成然寐,蘧然觉」的「寐」和「觉」,是指死和生而言。「成然」,因版本而有不同写法,这里表述得不太清楚,「成」的本意是结束、完成、安定,此处意为成就人生而心安。「蘧然」也不好理解,「蘧」意为迅速、突然等,似含有不磨蹭、果断、达观等意思。成玄英解释为「惊喜之貌」,此说是依据【齐物论】,该篇庄子梦为蝴蝶的故事中,用「蘧蘧然」一词来描写从梦中醒来的样子。「惊」也是表示事出突然,所以「蘧然」就有吃惊地睁开眼睛之意。「喜」似乎有些多余,但表示出,即使吃惊地睁开眼睛,也并非感到厌恶和不安。因此,这个词就是安心地睡去、畅快地醒来的意思。
名剑镆铘
「必须成为镆铘」一句中的「镆铘」,传说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名剑。有位巧匠叫干将,其妻名叫镆铘。干将制作了一对剑(这种剑称为雌雄之剑)献给吴王,因为是一雌一雄,所以这对剑就分别称为干将和镆铘了。
日本的正宗、村正等名刀都蕴含着种种传说,同样地,围绕干将和镆铘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
干将奉吴王之命造剑,用了三年才完成。干将料想到,献上剑后会因延误之罪被杀,就向已有身孕的妻子托付了后事,然后只带了雌剑入朝。结果,因为花了三年时间,而且雄剑还没有献上,王发怒杀了干将。后来,干将的儿子长大,听母亲讲了父亲的遗言,并按照指引找出了雄剑。干将之子下定决心报仇,甚至在王的梦中现身。由于王悬赏搜捕他,干将之子逃到了山里。有一次,一位行路的客人询问缘由,他就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客人表示愿替他报仇。干将之子用剑砍下自己的头,与剑一起托付于客人,然后就倒下了。客人晋谒王,献出干将之子的头颅,说这是勇士的头颅,所以必须烹煮,就让人将头颅放在锅中煮。但三天过去了,头颅不但未煮烂,而且从汤水中跳跃起来怒目而视。于是客人说,如果王能亲自去看一下就能煮透了,让王俯身观察锅内,此一瞬间,他用剑砍下王的头。王的头颅落入汤水后,客人也将自己的头砍下落入汤水。三个人头在水中烹煮,变得不能辨别了。最后,大家只能将汤水中的肉分为三份加以安葬,三人之墓便被合称为「三王墓」了。
这是四世纪时干宝所著【搜神记】中的故事,这令人惊恐的故事与镆铘是相称的,但子来所讲的锻冶的故事,指的并不是铸造完成的镆铘,而是叫嚷着想成为镆铘的铸造材料。
据说,巧匠在石头上凿雕像时,会认真倾听石头的声音。如果石头无视巧匠的心情而随意地、人声人语地说话,巧匠就不能注意倾听石头的声音了。庄子观点的旨趣即是如此。
作者/[日]蜂屋邦夫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