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论】导论
作者 | (英)以赛亚·伯林
翻译 | 胡传胜
正文 | 20231字
阅读时长 | 约8-10分钟

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
——本杰明·贡斯当,【论征服的精神】

就理性的支持者而言,忠于决定论的动机之一似乎是担心决定论是科学方法本身所假定的。因此,斯图亚特·汉普希尔什诉我们:
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中,哲学迷信现在很容易取代作为进步之障碍的传统宗教迷信。在这个语境中,迷信是指这样两种信条的混淆:一种信条是人类不应该被当做自然物那样对待;另一种信条是人类实际上不是自然物。人们很容易从人不应该像其他自然物那样被操纵与控制这样一种道德命题,转到一种十分不同的、准哲学的命题:他们不能像其他自然物那样被操纵与控制。在目前的这种舆论环境下,对计划与社会控制技术的恐惧很容易被尊为一种非决定论哲学。
这段措辞强烈而谨慎的陈述,在我看来显示了我提到过的那种有影响的、分布很广的情感特征:如果决定论被拒斥甚或被怀疑,便危及科学与理性。在我看来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尽力去发现量的关联与解释并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称赞科学是对原因的寻求(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并不等于说每个事物都有原因。我所引证的那段话至少包括三方面令人困惑的因素。
(1) 我们被告知说「一种信条是人类不应该被当作自然物那样对待;另一种信条是人类实际上不是自然物」,而混淆这两种信条乃是迷信。但是,除了我的如下信念以外,我还有别的理由要求「不要把人当做自然物那样对待」吗?这种信念就是:从某些方面(使人之为人的方面)说,人是与自然物不同的;这个事实是我的道德信念一一我不应该把人当做自然物那样对待,即仅作为实现我的目的的手段一一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差异我才认为随心所欲地操纵、强制人们和对人们进行洗脑等等是不对的 。如果我被告知说不要把某物当做椅子,这样做的理由肯定是基于下述事实:所说的那个物体拥有日常的椅子所没有的特征,或者对于我或别人具有特殊的关系(一种可能被忽视或否认的特质),使得它区别于日常的椅子。除非人被认为拥有某些在自然物(动物、植物、事物)之上或之外的特征(不管这种差异自身被视为自然的还是不自然的),否则,不要把人当做动物或物体那样看待这条道德要求就是没有理性基础的。我的结论是,这远不是两种不同命题混淆的问题,如果不至少使其中之一显得没有根据,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结便不可能被切断;而且这肯定不会推动汉普希尔所谈论的那种进程。
(2)至于警告不要从「人不应该被操纵与控制」的命题转到「他们不能像其他自然物那样被操纵与控制」的命题,更合理的说法肯定是假定:我之所以叫你不要这样做,不是因为人不应该被如此对待,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容易被这样对待了。如果我命令你不要控制和操纵人,不是因为我觉得既然你无法获得成功所以不要白白浪费你的时间与精力,而恰好是因为我担心你做得太成功,以致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一一而这种自由,要是他们能逃脱太多的控制与操纵,我相信他们是能够保持的。
(3)「对计划与社会控制技术的恐俱」那些相信这些力量并非不可抗拒的人可能最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人们如果不愿被干涉太多,他们便应该拥有在可能的行动路线间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一去实现他们被决定了的可预测的选择(如决定论者相信的那样)。后一种也许是我们的实际状况。但是如果我们偏爱前一种状态——不管它阐述起来多么困难——这难道是一种迷信,或是「虚假意识」的另一个个案吗? 只有在决定论是正确的情况下才会如此。但这却是恶性的循环论证。决定论本身也许就是这样一种虚假信念一一除非接受决定论否则科学便受到危害——所产生的迷信,因此它本身就是误解科学的本性而产生的「虚假意识」的案例,这难道没有可能吗? 任何学说都可能成为迷信,但我自己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中必定有一种是迷信或将要变成迷信。
现在转到非哲学作者。那些强调自然科学范畴不适用于人类行为的人的著作,早已使十九至二十世纪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粗糙的解决方案名声扫地了。因此,现在对这个论题的任何严肃讨论都必须一开始就考虑过去一十五年里世界范围内对这个论题的讨论。当 E.H.卡尔认为将历史事件归因于个人行为(「传记偏见」)是幼稚或至少是孩子气的,认为我们的历史著作中非人的因素越多便越科学,因此也越成熟与有效时,他就暴露了自己是十八世纪教条唯物主义的忠实——太忠实——信徒。这种学说甚至在孔德及其弟子的时代,或者说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时代,也没有被当做是不容置疑的普列汉诺夫尽管非常天才,但他的历史哲学得益于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地方比得益于黑格尔或马克思的黑格尔成分的要多。
还是让我公平地对待卡尔。当他坚持物活论或拟人论——把人的特征赋于无生命的实体——是原始心灵的标志时,我不想对此加以辩驳。但是将一个谬误与另一个谬误相加鲜能得出真理。拟人论是将人的范畴运用于非人类的范畴之谬。但是的确可能存在一个人的范畴能够运用的区域,这就是人的世界假定惟有在描述与预测非人自然中有效的东西才必然适用于人类,假定我们据以区别人与非人的范畴因而必然是虚幻的——通过将其解释为我们童年的畸变而予以消除——则是相反的错误,颠倒过来的物活论和拟人论。科学方法能够达成的,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达成。自然科学中富有成效的统计方法、计算机、任何其他的仪器或方法,只要能用于人类行为的分类、分析、预测与「返测」(retrodict),当然都应该受到欢迎;出于某种教条的理由而禁用这些方法,纯粹是蒙昧主义。
不过,从这一点远远不能教条性地保证,一种研究主题越是能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我们就越能接近真理。这种学说,在卡尔那里,等于说越非人与一般,就越有效,越普通就越成熟;越关注个人、他们的气质与他们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虚妄,越远离客观的真理与现实。这在我看来与相反的谬误——历史可以归结为大人物的生平与言行——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断言真理存在于这些极端中间的某个地方,存在于同样狂热的孔德与卡莱尔的立场的中间,这可能是迂腐之论,但也有可能更接近真理。正如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哲学家,曾经冷冰冰地指出的,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假定说真理,当其被发现的时候,会是有趣的。当然,真理也不一定就是令人吃惊的和颠覆性的;它可能如此也可能并不如此;我们难以说清。
这不是个详细检视卡尔的历史著述观的地方,他的那些观点在我看来散发出理性时代最后的魔法气息,比理性主义还要理性主义,带着所有令人羡慕的简单、明晰,摆脱了这一思想领域甚至在伏尔泰与爱尔维修处于顶峰的灿烂开始时代就具有的怀疑与自我质疑的特质;在此之前,德国人以其特有的凿通一切的热情,毁灭了平滑的草地和对称的花园。卡尔是一个精力充沛和令人愉快的作者,虽然受了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基本上是一个过时的实证主义者,处于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与 HG威尔斯的传统之中;他是圣伯夫所说的un grand simplificateur」(一个大简化者)从不为自赫尔德和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起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学科的那些问题与困难烦心。他对马克思尊敬有加,却远离他的复杂洞见:他是一个走捷径的大师,是为那些巨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答案的人。
但如果我在这里无法详尽地讨论卡尔的立场,我至少也能够试图回应他对我的观点的一些最严厉的指责。他对我的最严重的指责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我相信决定论是错误的并且拒绝任何事物都有其原因这条公理,而这条公理,按照卡尔的看法是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的条件」;第二,我强烈坚持「谴责查理曼、拿破仑、成吉思汗、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屠杀」也就是说,裁定历史上重要的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历史学家的责任;第三,我相信历史学中的解释是一种根据人类意图所作的解释,对此,卡尔提出相反的「社会力量」作为替代概念。
对于所有这些指责,我只能再一次重复: 第一 ,我从未否认(也从未想到过)这样一种逻辑可能性:有一些版本的决定论在原则上(虽然,也许仅仅在原则上)可能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有效理论;我也从不坚持说我已经驳斥了它。我惟一争辩的是,对决定论的信念是与深嵌在我们普通人与历史学家的正常言说与思考中的信念不相容的,至少在西方世界如此;因此严肃对待决定论必然导致这些核心观念的根本修改,一种无论是卡尔还是其他的历史学家在其实践中都没有提供明显例证的剧变。我不知道有支持决定论的最终论据。但这不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正是决定论支持者的实践,以及这些支持者在这方面要勉强面对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会使他们付出代价;这恰好表明,这种理论支持在目前无法被严肃对待,而不管谁声称提供了这种支持。
第二, 我被指控要求历史学家进行道德说教。我从没做过这种事。我只是坚持,历史学家(其他人也一样)所使用的语言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带有评价性力量的言词,而让他们净化他们的这种语言等于让他们完成一项异常困难也是自我愚弄的任务。当然,就像任何希望在某个领域建立真理的人一样,客观不带偏见、不动情无疑是历史学家的美德。但是历史学家也是人,他没有义务在更大的程度上比其他人非人性化(dehumanise);他们选样讨论的主题以及他们对注意力与着重点的分配都受他们自己的价值天平的引导,而如果他们想理解人的行为或想与他们的读者交流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这种天平便不应该与人们共享的价值观相去太远。
当然,理解他人的动机与观点并不必然分享这些东西;洞察力并不包含赞同;最有天赋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也是最少偏袒的;与题材保持某种距离是需要的。但是,虽然对动机、道德、社会法规以及整个文明的理解并不需要接受甚至同情它们,这种理解也需要以「哪些价值对这些个体或群体是重要的」这一看法为前提,即使这些价值可能被发现是令人厌恶的。而这种理解依赖于一种有关人性和人的需要的观念,这种观念进入历史家自己的伦理、宗教或美学视野中。价值,特别是制约着历史家搜集事实的那些道德价值,以及他们在其中展示这些事实的眼光,被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传达出来,而且是不自觉地被传达出来,正像它们同样被任何一个试图理解与描述人类的人传达出来一样。我们用于判断历史学家著作的标准,原则上并非也不需要不同于那些我们借以判断其他研究与想像领域的专家的标准。在批评那些处理人类事务的作者的成就时,我们不可能将「事实」与其意义断然分开。「价值进入事实并成为其组成部分。我们的价值是我们作为人的那些配置的基本成分。"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卡尔自己(读者对此一定大吃一惊)。我原本是能对这个命题作不同阐述的,但我觉得卡尔的话已经足够了。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反驳他对我的指控。
很明显,历史学家没有必要像卡尔错误地认为我希望他们做的那样,去正式地声明他们的道德判断。作为历史学家他们没有义务告诉读者希特勒危害了人类,而巴斯德有益于人类(或者无论他们举什么例子)。正常语言的使用本身不可能不透露作者关于什么是常规什么是反常、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琐碎、什么令人喜欢什么令人沮丧的想法。在描述已发生的事情时,我可能说成千上万人被残酷处死;或者换一种说法,说他们遭受毁灭、牺牲生命、被屠戮;或者简单地说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人口的平均寿命降低了,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所有这些对已发生的事情的描述没有一个是完全中性的:它们全都携带着道德含义不管他多么小心地使用纯粹描述性的语言,历史学家之所言迟早会传达他的态度。超脱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使用中性语言(「希姆莱使好多人窒息而死」)本身便传达着自己的伦理语气。
我并不是说关于人类的严格的中性语言是无法获得的。统计学家、情报编辑者、研究部门、某种类型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官方记者、旨在向历史学家或政治家提供数据的编辑,都可能并被期望接近这种中性语言。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行动并不是自主的,而是被指派向那些以自身工作为目的的人,如历史学家和活动家,提供素材。研究助理并不要求去选择和强调人类生活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历史学家无法避免这点否则,他写出的东西将会与他、他的社会或别的文化视为中心或边缘性的东西毫无关系,因而也不再成为历史。如果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提供的,那么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逃脱的核心问题便是(不管他是否意识到):我们(以及其他社会)是如何到达今天这个境地的。这个核心问题 eo facto(实际上)必然要求对社会、人的性质、人的行为的根源、人的价值与价值尺度有某种特殊的洞见,而这种洞见却是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体质人类学家、语法学家、数量经济学家或某种类型的心理学家(例如为别人的解释提供资料的人)能够避免的。历史学不是附属性活动它试图为人的行动与苦难提供尽量完整的描述;称人类为人就是把我们能够识别出的那些价值赋予他们,否则对我们来说他们就不是人。因此,对于什么重要、在多大程度上重要这些问题,历史学家(无论他做不做道德说教)没有办法不采取某种立场,这就足以使得「价值中立」的史学观念,即历史家是 ipsis rebus dictantibus的抄写者观念,成为一种幻觉。
这也许就是阿克顿强烈反对克莱顿的理由:并不尽因为克莱顿使用人为的非道德词汇,而是因为他在使用这些词汇描述博尔吉亚家族及其行为时,实际上为他们进行了开释;不管他做得对还是不对,他还是这样做了;中立也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且认识到它的这种本性也是一种道德态度。阿克顿坚信克莱顿是错的。我们可能要么同意阿克顿要么同意克莱顿。但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我们都在陈述与传达(即使我们宁愿不直陈)一种道德态度。让历史学家描述人的生活,却又不根据穆勒所说的人的永恒利益来描述他们生活的意义,无论作何理解,都构不成对其生活的描述。要求历史学家尝试想像性地进入其他人的经验却又禁止他们表现道德理解,这是让他们只陈述他们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而剥夺他们工作的人性含义。事实上这是我对于卡尔那种反对道德说教的坏习惯的道德说教所要说的一切。
毫无疑问,下述观点仍然是值得讨论的:存在着客观、永恒且普遍的道德与社会价值,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任何一个理性之人的心灵只要选择正视它们便可以接近它们。不过,理解某人自己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人的这种可能性,以及人类不同部分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依赖于某些共享价值的存在,而不仅仅依赖于共有一个「事实的」世界。后者是人类交往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那些与外在世界隔离的人被描述为反常的,或者在某种极端的场合,被描述为神经错乱的。同样的情况——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也适用于那些远离共享的公共价值世界的人,一个人宣称他曾经知道好坏之分却又说自己忘掉了它们,这样的人是不足为信的,如果他可以信赖,也应该被恰当地认为是精神不健全的。但是这种情况也适合于这样一种人,他不单不赞成、欣赏或宽容,而且事实上无法理解其他任何人都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例如,对于毫无理由地屠杀任何蓝眼睛的人的法令的反对。他也许可以算作心智不全的人的活标本,这样的人算起来可能不足六人,或者想想大概也就只有恺撒之类。对这样一种错乱的标准(而不是描述性)检验,所依赖的是什么给予诸如自然律这样的学说以可信性,特别是在那些拒绝给它们以任何先验地位的版本中。对共享价值的接受(至少对其不能再少的最小部分)进入我们对于正常人的理解之中。共享的价值能将关于人类的道德基础的概念与诸如习俗、传统、法律风俗、风尚、礼仪的概念区分开来。有了这些价值,所有这些广泛的社会历史、民族、地方差异与变化,便不再被视为奇怪或反常的、极端自我中心不健全或根本不可取的;更不会被认为在哲学上是有问题的。
任何一种高于纯粹编年记述、涉及选择与重点的不平等分配的历史著述,都不是全然 wertfrei的。那么是什么把被正当地谴责为说教的东西与那种似乎无法逃脱的对人类事务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区别开来呢?并不是它的公开性:在不赞成作者观点的人眼中,仅仅从表面上选择中立语言可能显得更具说教性不过是更内在一些而已。在论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的文章中,我想我已经讨论了偏见与私心的含义。我只能重复说我们只能根据与那些被传达的,人类共通的核心价值的接近程度来区分主观的赞赏与客观的赞赏,也就是说,出于实际的目的,根据与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地点与绝大多数时间内共享的那些价值的接近程度来区分。很明显这不是绝对和严格的标准;存在着变数因此存在着不能忽视的(和明显的)民族的、地方的、历史的特殊性,存在着偏见、迷信、文饰以及它们的非理性的影响。但是这个标准不全然是相对和主观的;否则,人的概念将变得太不确定,面被无法沟通的规范性差异所分裂的人与社会,就会全然无法越过时空与文化距离而沟通。
道德判断的客观性似乎依赖于(几乎是存在于)人类回应的持久程度。这个观念从原则上说不能被弄得太尖锐和不可更改。它的边缘仍然是模糊的。道德范畴以及一般的价值范畴远不像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觉那样坚实与难以磨灭,但是它们也不像有的作者在对抗经典的客观主义教条时常常假定的那样相对与流动。最小量的、共享的道德基础,即相互关联的概念与范畴,对于人类的交往来说是根本性的。不管它们多么易变,也不管它们在什么力量的影响下会作多大改变(这些是经验问题)在道德心理学、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的领域内,这些范畴是什么,乃是有趣的、重要的和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做出再多的要求便超出了可交流的人类知识之外。
第三,我被指控假定历史学处理人的动机与意图,面对于这些东西,卡尔希望代之以「社会力量」。对这个责难我表示服罪。我必须再说一遍,任何人只要讨论的是人,就注定要考虑动机目的、选择以及专属人类的特殊人类经验,而不是只考虑在有感觉、有生命的人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尤视非人因素的作用,无视无目的的人类行为后果的影响,无视人常常不能正确理解他们自己的个体行动及其根源这个事实;在解释事件的发生及如何发生时在非常字面与机械的意义上不作更深的因果性探究——所有这些都是荒谬地幼稚与琐碎的(不要说蒙昧主义了),我从不主张如此。但是无视动机产生的背景以及动机在行动者面前展开的可能范围(它们绝大多数从未实现,有些则根本无望实现),无视人类——在我看来他们的世界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眼界与价值(幻觉连同其他一切)只能根据他们白身来理解——思考与想像的广度,就不再存在历史著述。在形成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或那个人的个人影响到底有多大作用,我们也许会对此争论不息。但是试图将个人行为归结为那些非人的「社会力量」的行为(它们是不能进一步分析为马克思所说的创造历史的个人的),乃是统计学的「物化」,一种官僚与管理者的「虚假意识」,这些人无视所有不能量化的东西,因此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人道的。
药方会引起新的疾病,而不管这些药方能不能治愈它们正在治疗的疾病。对人类说他们是他们很少或无力控制的非人力量的玩物,以此来恐吓人类,纵然诡称为了杀死别的虚构之物——超自然力量、全能的个人与看不见的手等等观念——也不过形成了新的神话而已。这等于是虚构实体,宣传对事件的不可改变的模式的信念,而对于这些模式,经验的证据至少是不充分的;这种做法虽然放松了个体的人格责任的重担,却在一些人当中产生了非理性的被动性,并在另一些人当中产生了非理性的狂热的主动性;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一种确定性更激动人心:星辰都为自己而战,「历史」、「社会力量」和「历史潮流都站在自己一边,背负着自己向上、向前对这样一种思考与说话方式进行揭露,是现代经验主义的大成就。
如果我的文章有什么论战锋芒的话,那就是对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构造物的不信任。谈论人却仅仅根据统计概率而无视人之为人的特殊性一一评价、选择、不同的生活见解——乃是对科学方法的夸张的使用,一种没有道理的行为主义,其误入歧途的程度不亚于诉诸想像性的力量。前者有其地位;它描述、分类、预测,即使并不做出解释。后者虽然解释,但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我称之为新物活论的词汇来解释。我怀疑卡尔维护这些方法时从不感到于心不安。但是在他对 naivete(天真)、矫矜、民族主义、阶级、人格说教的空洞的反驳中,他放任自己驶达另一极端一一非人格的黑夜,人类在其中被分解为抽象力量我对这种力量的激烈反对导致卡尔认为我赞同相反的荒谬极端。他的这种假定,即只能在这些极端中选择其一,乃是一种基本的谬误,而他(还有别人)对我的真实的与虚构的观点的激烈批评,全都源自这个谬误。
在此我想再一次重复我从未放弃的一些基本观点:因果律是可以运用于人类历史的(对不起卡尔,我认为否定这个命题就是心智不健全);历史并不主要是个人意志间的「剧烈冲突」知识,特别是那些在科学上已经确证的规则,会使我们更有效率并扩展我们的自由,这种自由易于被知识所培育的无知、觉、恐惧与偏见所遮蔽;许多经验证据表明,自由选择的疆域远比过去许多人假定的要狭窄,现在也许还有人错误地相信这个疆城很大;历史的客观模式,在我看来,甚至是可以辨识的。我必须重复,我惟一关心的是申明,除非这些规律与模式容许某种自由选择,而且不仅仅是那种其本身完全由前在条件决定的选择所决定的自由行动,否则,我们就必须重建我们相应的现实观;这项任务比决定论者认为的要更为艰难。
决定论者的世界,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其中,欧内斯特·内格尔所谓的属于人类意志力的作用的一切将仍然是完整的;人的行为将仍然受道德煲贬的影响,而他的新陈代谢(不管怎么说)则不直接受这种道德褒的影响;人们将继续按美丑来描述人与事,按有益与有害勇敢与怯懦、高贵与渺小来评价行动。但是康德说,如果支配着外部世界的现象最终支配着存在的一切,那么道德——在他的意义上——便会被废止另一方面,在论及道德责任观念所假定的自由概念时,康德采用了非常激烈的手段来拯救这种观念。我觉得康德至少显示了他对至关重要的东西的深刻把握。他的解决是不清楚的,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尽管这种解决遭到拒绝问题依然存在。在因果性地决定的系统中,通常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观念便不复存在了,至少是没有用了。行动的观念也将不得不重新考虑。
我认识到这个事实:有些思想家在解释诸如责任有罪性自责等概念与严格的因果决定相一致时,似乎没有任何理智上的不安。他们至多把持不同意见者的抵制解释为将因果性与某种强迫相混淆了。强迫挫伤我的愿望,但是当我满足这些愿望时,我肯定是自由的,虽然我的愿望本身是因果性地被决定的;如果它们不是如此,如果它们不是我的一般倾向或我的习惯因素或生活方式的结果(它们可以用纯粹的因果性词汇来描述)。或者,如果这些愿望不完全出自物理的、社会的或心理的原因那么,肯定存在着一种打破因果链的纯粹机会或随机因素。是(论证继续)随机的行为难道不正好是自由、合理性与责任的对立物吗?而这些选择项似乎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性。没有原因的选择,这种观念就像某种从虚无中产生的东西,肯定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不需要再作论证)这些思想家所容许的惟一候选方案一一因果性的选择包含着责任、功过等等——同样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困境在两千多年里使思想家们陷入分裂。有些人仍然受其折磨或至少感到困惑,就像早期斯多噶派一样;其他人则觉得什么问题也没有。它有可能,至少部分地,起源于将机械模式运用于人的行动;在一种场合,选择被理解为因果系列中的纽带,这种因果系列的典型情形便是机械过程的做功:在另一种场合,即系列中断的情况下,仍然用高度复杂的机械论来解释。没有一种图景能很好地切合于实际情况。我们似乎需要一个新的模式、一个图式,把明显的道德意识从强迫性的传统讨论的构架所提供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中拯救出来。打破旧的、阻塞性的类比或(用一个熟悉的词)不适当的语言游戏规则的所有努力,至此都是不成功的。这需要至今尚未出现的第一流的哲学想像。怀特的办法一一将观点的冲突归结为价值的不同尺度或道德用法的多样性一一在我看来并不是出路。我不禁怀疑,他的观点是更大的理论的一部分,按照这种理论,对决定论或者任何别的世界观的信念,都是或都依赖于某种大范围的、关于如何处理思想或经验之某一领域的实用决定progmatic decision),这种决定的观念基础是:哪一套范畴能产生最好的结果。纵然我们接受这个观点,也难以协调诸如因果必然性、可避免性、自由选择、责任等等观念。我并不声称我驳倒了决定论的结论:但是我也看不出我们为什么非得接受这些结论。无论是诸如此类的历史解释观念,还是对科学方法的尊敬,在我看来都不必然蕴含着这些结论。
以上说法概括了我与欧内斯特·内格尔、莫顿·怀特、E.H卡尔、古典论决定者及其现代弟子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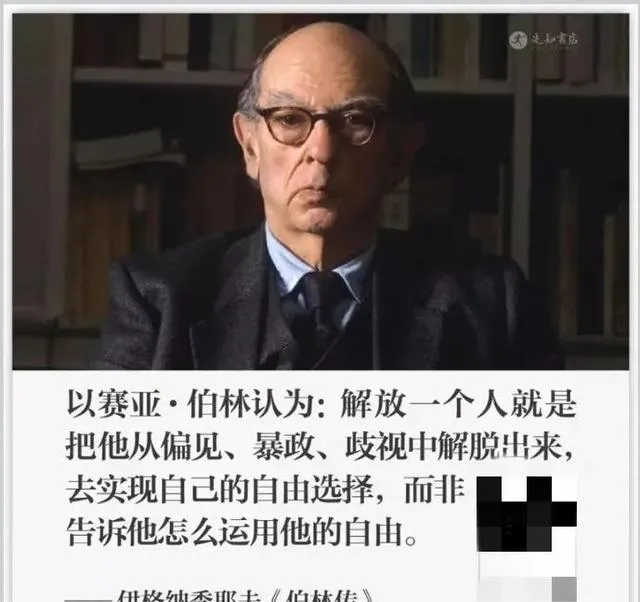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
自由论
/(英)伯林(Berlin,1.)著
胡传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12
书名原文:Liberty
ISBN 7-80657-653-3
部分内容由编者整理,注释从略。
本文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自由 3个
#以赛亚·伯林 2个
#【自由论】 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