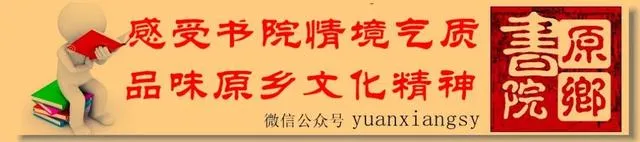
陪 同
阿杜拉錫克·古爾納作 徐德寬譯
我想他看到我走過來了,可不知何故,就是不露聲色。我站在開啟的汽車後門旁,等著他擡起頭。他折起報紙,鉆出車門,瞥了我一眼,眼裏滿是憎惡。我一動不動地站著,驚訝得渾身直抖,身體仿佛都被掏空了。或許這並非憎惡,只是煩躁而已——根源在於對逃不掉的無聊存在有著躲不開的挫敗感——只是不滿而已。可就是感覺像憎惡。他微微翹起下巴,請我說明來意。我說出那家旅館的名字,他點了點頭,仿佛這不是太過分的要求,仿佛他之前以為我會說出一個不可能的去處。我不懼這頭巨獸,在汽車前排挨著他坐下,目的是讓他明白我並不像他最初認為的那樣,活該遭人憎惡,但這也算是承認了我的外表似乎有惹怒他的潛能。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對他的憤怒視而不見。
汽車座椅笨重堅硬(而且是綠色的),塑膠墊子已有些年頭,裂痕隨處可見。汽車突然轉彎,沖出了出租車站,座椅鋒利的棱角像生牛皮一樣卷起,穿透了我的襯衫,刺得我皮肉生疼。汽車儀表盤上盡是窟窿和纏繞的電線,裏面原先可能有打火器、收音機或者雜物箱。這些窟窿也不能說是空無一物:小紙卷塞滿各個角落,從一個窟窿裏垂下一塊用得灰不溜秋的抹布,等著晾幹。
我們在午高峰的車流中緩緩前行,他瞥了瞥我雙腿夾著的公事包,然後擡起眼,盯著我的臉,我假裝沒有註意到他的目光。「從哪兒來?」他問道,調節著自己的聲音,使提問不那麽唐突,但仍然試圖讓人聽著像是在厭惡地咆哮。不管怎樣,他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好像期待我會尊重他提這個問題的權利。「Unatoka wapi?」 【斯瓦希裏語「從哪兒來?」的意思。】 他又猛然加速,身體後仰,把翹起的胳膊肘支在車窗上。他身形清瘦,肌肉緊繃,雙腮凹陷,滿臉不屑的期待。至少我在仔細琢磨他的問題時是這麽認為的。那張肌肉靈活的臉上有種陰森而痛苦的神色,我不由覺得這是過著危險生活的人,有可能故意施虐,以減輕自身的痛苦。我對自己的好奇心感到恐懼和厭惡,希望旅程盡快結束。我應該一看到他的怨憤臉就立馬走開。他又瞟了一眼公事包,臉上掠過一絲嘲弄的微笑,似乎在暗示我太自以為是。這只不過是一件便宜的塑膠制品,提手硬而粗糙,拉鏈歪七扭八,我估計也就能挺上三五個月,不值得如此苛刻地審視。
「從哪兒來?」他問道,這一次,他沖那公事包點點頭,表示他註意到了那東西。
「伊榮格雷紮」 【斯瓦希裏語「英國」的說法】 。我答道。英國。我心不在焉地小聲搪塞他,以表明我對這場談話沒有興趣。
他也輕輕哼了一聲。「學生?」
很多人本想出門做大事,臨了卻只帶回諸多故事和一個廉價的公事包;他的意思是問,我是否是這些人中的一員。有些人雖然幹著令人羞恥的下賤工作,卻頻頻傳回自己如何好學上進、左右逢源(遇上好形勢註定能發一筆小財)的神奇傳說。我是否也是這樣的窩囊廢?他滿臉愉快的壞笑,等著看我會如何羞愧難當地回答。他開口說這些時,我是多麽希望能聽到他說,其他人都跑光了,自己必須留下來照顧生病的家人,師長們在他年輕的時候曾對他給予厚望,可他也就只能這樣了。我告訴他我是一名老師,他又輕蔑地哼了一聲,這一次毫不掩飾。就這些?
午高峰時,人群總是行色匆匆,汽車只要稍有猶豫,他們就橫穿馬路,猶如不息的川流。
眼前這位出租車司機儼然受到這些放肆家夥的冒犯,每當前面的車禮讓行人,他就狂按喇叭。
一群十幾歲的印度小學生在汽車之間閑庭信步,興致勃勃地談天說地,惹得他長長地按了一聲喇叭,嘴裏罵罵咧咧的。
「骯臟的屎刮刀。
他們在搞什麽把戲?
」靠近郵局時,交通最為擁堵。
成群結隊的人在人行道上走,一些身穿襯衫、打著領帶的人急三火四,而另一些人則慢慢悠悠,時不時停下來看看地攤上的劣質商品。
「伊榮格雷紮。」他一邊哼哼著,一邊左轉拐向碼頭——我住的酒店就在那兒。「伊榮格雷紮,」他重復道,「奢華之地。」
「你去過那兒?」我問道,能聽見自己的聲音裏帶著驚疑。你?為了抵制那厚顏無恥、自我陶醉的文化,我可是拼盡了全身氣力,才能小有進展,可是這家夥談起那個糟糕的地方竟會如此漫不經心。奢華之地。
出租車司機野蠻地按著喇叭,要叫擋在前面的一輛水罐車讓路。他按了有一分鐘左右的喇叭,似乎被水販子的冒犯徹底激怒,一邊大喊大叫,一邊在車窗外揮舞著右臂,仿佛隨時都會跳下車,掀翻水罐車。碼頭工人在路邊的小亭裏買午餐,他們也是水販子的顧客,此時興高采烈地朝出租車司機揮手。他開著車繞過水罐車,然後又長按了一下喇叭。
「你在英國有親戚嗎?」我問道。我無法想象,一個脾氣這麽壞的人,開著一輛快要報廢的出租車(我們正坐在裏頭)謀生,怎麽能夠掙到錢,在那奢華之地的一張臭烘烘的床上睡上一晚,吃上一頓早餐。
「我以前在那兒住過。」他猛速轉過身來,看著我,咧嘴一笑。我們現在已經下了大路,到了碼頭倉庫和停泊機車的場地後面,在酒店前的最後一段路上迂回行進。路面上一會兒是峽谷般的坑洞,一會兒是陡峭的鐵道線的路基——在這崎嶇不平的道路上,他不得不集中精力。他剛開口講話,但路面上的危機一個接一個,應接不暇;他搖搖頭,不想中斷自己的故事。在這兒開旅館本來就是瘋狂至極,院子另一邊又到處都是廢棄的機器和工人丟棄的垃圾,但在碼頭和鐵路變成肆意蔓延的廢墟之前,在馬路荒廢之前,旅館就已經在那裏了。

「我有過一個馬來亞女人,那是歐羅巴人種的妓女。她帶我去過英國,還有法國,甚至澳洲。我們哪兒都去。都是她出錢。要是有人講這樣的故事,你會覺得他們肯定在說謊,幻想著賣身給有錢無腦的歐羅巴妓女。在遇到這個馬來亞女人之前,我也這樣想。」說話間他已把車停在了旅館外面,掛在空擋上,車子抖個不停。「斯利姆。她以前叫我斯利姆,」他一邊收錢一邊說著,臉上洋溢著沈浸在回憶中的微笑,「其實我叫舒利姆。我一直都在郵局旁邊的出租車站。什麽時候來找我都行。」
我找到這家旅館純屬偶然。移民局官員對我解釋說,我必須在申請表上明確寫上目的地國家的地址,否則不能發給我簽證。他說這話時帶著歉意,因為先前他看過我護照上的出生地後,不禁熱情地說起桑給巴爾,還說他也有親戚住那兒。他給我看一張寫著旅館名字的單子。「隨便選一個,」他說,「你不必真在那兒住。填表而已。」 【原文為斜體英文,作者很可能想暗示移民局官員在用斯瓦希裏語與「我」交談。】 於是我就隨便挑了一個。當我在機場外找到一輛出租車時,唯一記得的就是這家旅館。這旅館很難找,停泊機車的場地和倉庫在工作時間之外靜得嚇人,這些都正合我意,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來拜訪我,要是我住在城市另一邊那帶有賭場和遊泳池套間的華麗宮殿裏,也許就會有人來打擾。
可第二天晚上,總台打電話告訴我有人來訪,這讓我吃驚非小。來人正是舒利姆。我從未料到他會來,可這會兒他就在我面前,讓人覺得我一直都知道他會出現。他上身穿了一件綠色絲質短袖襯衫,圖案是白色花朵和配有舷外支架的藍色獨木舟,胸前口袋裏露出太陽鏡的一條腿。一件寬松的燈芯絨牛仔褲繞在腰上,系著一條寬大的帶扣皮帶,褲腰在皮帶下折了好幾層。他堅持要請我喝一杯,要請酒保喝一杯。大堂酒吧裏空空蕩蕩,除了正在招待朋友的一對比利時夫婦(這家旅館的老板)之外,再也沒有別人。「Ces gens sont impossible.」 【法語,意思是:「這幫家夥真是無藥可救。」】 女客人惱怒地說。在她提高的嗓門裏有著不受外界影響的自信。這幫家夥真是無藥可救。這個女人四十多歲,身材苗條,穿戴整潔,打扮時尚而又不失莊雅。舒利姆瞥了一眼那三個歐洲人,好像聽懂了他們在說什麽,可人家似乎並沒有註意到他的存在。
「她給我買的這些,我的馬來亞女人。」舒利姆說,小心翼翼地扯了扯自己閃亮的襯衫,然後又使勁捏了捏藍色燈芯絨牛仔褲。他微笑著——這一次沒有譏嘲的意味——毫不介意酒保也加入進來。「想知道她是怎麽看上我的嗎?」他等著,直到我和酒保都點點頭,「那好,我告訴你們。她那天在北海岸塔姆碧麗酒店外等車。知道那兒吧?我看見她站在入口附近的一棵樹下,好像在等什麽人。通常都是酒店服務員把我們領到車道上後,客人才會從店裏出來。你們見到過他們怎麽打扮那些狒狒 【指酒店服務員】 嗎?他們將那些狒狒從山上帶下來,給他們圍上黃圍裙,紮上黑領結,然後管他們要服裝費。這些我都知道。」酒保穿著白襯衫,打著黑領結,腰上圍著黃圍裙——他可能也得為自己的服裝買單,但他盡量裝作若無其事。
「不管怎樣,」舒利姆繼續說,「我猜她在那裏等人來接她,可我想,不管咋樣,我該試試。她不年輕,也還沒那麽老。她聽我說了一會兒……呃……我照例跟她聊到在政府關稅處的遊覽經歷,於是,她上了我的車。我整天載著她到處逛,遠的地方到過馬林迪、懷塔姆、塔卡溫古 【馬林迪、懷塔姆、塔卡溫古三處皆為肯雅地名】 。每到一地,我就跟她介紹當地的情況。要是我高興,或是她問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就順口胡謅一番。傍晚時分,我開車送她回賓館,經過海灘時,她讓我把車停下來,我們就在那裏做那事。在戶外的沙灘上,像兩條狗。每天都這樣。我早上去接她,拉著她到處逛,給她講故事,天黑後帶她去海灘。幾天後,她告訴我她要帶我一起去烏拉亞 【斯瓦希裏語「歐洲」的說法】 。她把一切都弄好了。機票,護照。錢都是她來出。」


「你在海灘上肯定十分了得。」我很不情願地沒話找話說,因為我不相信任何女人,隨隨便便勾搭一下,就會看上舒利姆,而且看不到其中的危險,不管怎麽說,我不想再聽到瘋狂的歐洲人渴求非洲大雞巴的故事了。酒保無聲地笑了,舒利姆看看我,又看看他,似乎有點小受傷。
「叫我斯利姆吧,」他說著喝掉了杯中酒,輕輕地把杯子朝我推過來,「要是從外幣換算成本幣,也沒多少錢。你知道的。不管怎樣,她很有錢。」
我付了他的酒錢,坐著聽他繼續講他的馬來亞女人的故事。那女的離了婚,拿了自己的那份錢,決定到處旅遊。她帶他去了利物浦,她在那兒出生,還是嬰兒的時候,父母就移民去了澳洲。對他來說困難嗎?和她在一起?他聳聳肩。她負責一切,帶他看各種東西;那母狗每天都要做愛,有時一天兩三次。這並不難。他們在那兒待了幾個星期。他交了兩個住在附近的朋友,都是穆斯林,一個是索馬里人,另一個是毛里裘斯人。他們教他如何領取失業救濟金。他和馬來亞女人過著奢華的生活。英國政府是個大蠢蛋。利物浦到處都是黑人,粗野的混蛋,喜歡幹什麽就幹什麽,政府就只管給他們錢。英國女人們總是愛撫摸他,擺弄他的頭發,往他身上擠,給他買酒喝。過了幾分鐘,我跟他說再見,起身離開了。我有幾封信要寫,我說。
第二天晚上他又來了,換了另一件花襯衫。我之前告訴過總台,說我不在,可也許接待員受制於我不能理解的情義,沒有幫我的忙。我本想在走過總台時扭頭留下句話,可此時值班的是另一個年輕人。「這是在澳洲買的,」舒利姆扯著他的襯衫說,「我們在法國待了幾天後就去了那裏。貝蒂。她的名字叫貝蒂。教名叫貝瑟尼,但她自稱貝蒂。明晚你想去夜店嗎?你還要在這裏待一晚上,對吧?馬堅戈 【肯雅地名】 那邊有個好地方。不像這裏,盡是些旅遊垃圾。我們明天去那兒。澳洲女人總想要那個,可她們的男人性欲 【原文為nyege,斯瓦希裏語】 不足。所以,那幫女人總是熱情似火。熾熱地燃燒。馬來亞女人並不介意我和她們搞在一起。」他還講了很多細節:女人們為了搞到他先是各種精心設計,而後便是不知羞恥恣意淫樂。
「你怎麽又回到這兒來了呢?」我最後問道,強行要把故事拉到結尾處。
「總得有停下來的那一天,不能老玩兒,」他輕蔑地說,「回到自己人的身邊。在其他任何地方,你終究不過是個小醜。」
這似乎是說再見的好時機,可舒利姆不讓我走,顯得非常嚴肅。他一邊抓著我的手腕,緊緊攥住不放,一邊又點了一輪喝的,記在我的賬上。酒保上了酒水,讓我簽了賬單,退了下去,目光小心地避開舒利姆抓住我手腕的手。酒吧裏沒有別人了。酒水一放到我們面前,他就笑著放開了我,在他抓著我手腕的地方,留下了一圈淡紅色的肉痕。我起身離開,看到他想說點啥,卻又改變了主意。「你的酒怎麽辦?沒關系,我喝了。那我們明天見。」他說,「你沒忘記那個夜店,對吧?」
一整天,我都竭力不去想要是他再出現,我該怎麽辦。這一天我專門用來充實前一周積累的一些參觀和采訪筆記。舒利姆的造訪臨近了,這會兒做這些事再糟糕不過了。充實筆記既非善行,也無痛苦,既不能轉移註意力,也不能令人精神振奮,只是意味著疲憊地追溯那些影響已經消退的陳年舊事。傍晚來臨時,我已經說服自己,我如此小心謹慎,真是愚不可及。我來這裏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位鮮為人知的詩人潘杜·卡西姆的情況,世紀之交時他住在這裏,我希望能找到一些關於他的資訊,而馬堅戈那邊的夜店則與此毫無關系。可去一趟又不會有任何損失,反過來還可能有點幫助。之前並沒有尋訪到任何關於潘杜·卡西姆的有趣資訊;而去一趟舒利姆經常光顧的夜店說不定會帶來意外的收獲。去這樣的地方絕非我願,再說要了解這座城市,也並不一定非得看清它油膩的下半身,可除了讓我感到惡心之外,去看一下倒也並無大礙。我並不期待走進舒利姆的朋友圈,因為我料到他們和舒利姆一樣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在返回英國之前,我就只剩下不到兩天時間了。我想在這麽短的時間裏,也不會有什麽危險找上我。筆記可以留待以後再去整理。我可能不得不花上一個晚上的時間去聽那些用床上功夫征服極易上當的女人的乏味故事,可這難道不比竭力趕走舒利姆,成為他怨恨和氣憤的物件要好嗎?
所以,舒利姆到達的時候,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我甚至認為他可能不會出現了,作為我懷疑他的故事的懲罰。我下來的時候,他正悶悶不樂地坐在車裏。咕噥了一句問候語,他就開車上路了。這種神奇的問候讓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不由打了個寒顫。為什麽不幹脆叫他走開呢?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前方,沒有註意我們要去往何處,盡管我很清楚我們身在何處。我想剛才肯定走神了,因為我突然意識到舒利姆已經離開了大路,在一條崎嶇不平、沒有燈光的小道上行駛。灌木林從四周向我們壓來。車燈的水平光線使這種感覺更顯壓抑,就好像在地底下一樣。這本該是一個微風習習、心曠神怡的夜晚,可在這隧道裏,空氣潮潮的,彌漫著濕泥土的味道。舒利姆扭頭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咧開嘴笑了。「就快到了。」他說著哼唱起來。一條狗在夜裏尖叫,不一會兒,汽車穿過的動靜攪得黑暗的灌木叢枝葉亂動。又過了一會兒,舒利姆開足馬力越過一個小土堆,進入一片被漆黑的大樹包圍的空地。已經有一輛車停在其中一棟房子前。肯定還有三四棟房子,只是光線太暗,很難看清楚。他把車停在那輛車旁邊,我們下了車。
夜店原來是一座用板條和泥巴蓋成的房子的前廳,掛著一盞昏暗的煤油燈。有兩個人早來了,看見我們,就站起來打招呼,顯然是在等我們。「這是從伊榮格雷紮來的貴客。」舒利姆笑著說。
其中一名男子和舒利姆年齡相仿,有著猶如毀容一般的相似長相。另一個更年輕,塊頭更大,他瞥了我一眼,嘴角不自覺地飄過一抹得意的笑。他叫馬吉德。一開始我沒聽清那個年紀更大些的男人的名字。(後來才知道他叫布達。)還沒等我們在那張粗糙的舊桌子前坐好,馬吉德就大聲喊著要啤酒。從裏屋走出來一個中年模樣的婦女,穿著一條磨破的緊身裙,腋下被汗液染成了黑色。她頭上裹著和衣服同樣材質的頭巾,身上穿著一件褪色的肯加。她強顏歡笑,和這些家夥胡亂打趣了一會兒,又走開了,去準備我這些快樂同伴點的飯菜。
桌上放著空啤酒瓶,這些瓶子將作為飲酒壯舉的勛章放在那裏。馬吉德和那名男子每人拿著半瓶啤酒,時不時喝兩口;喝的時候,往往把冒著啤酒沫的瓶子往嘴裏倒,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這些瓶子真大。屋裏看不見杯子。那天舒利姆說要去夜店,我當時想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幫男人聚在樹林中的黑房子裏偷偷喝酒。
「還會再上一些的。」布達以勸人放心喝的口吻說道。他的表情復雜,一半是勉強抑制的慍怒,一半是與愁悶相伴的怨恨,這表情我之前在舒利姆臉上看到過。也許是因為喝了酒。在這樣一個穆斯林小鎮上,一個人對成為酒鬼這類問題,必須慎重,甚至要時刻念念不忘,畢竟在這裏,謹慎行事是不可能的,被發現是不可避免的。或許是對不當行為的內疚產生了憤怒的自卑,或許是在貧瘠文化中對破壞性毒藥的消費需求造成了他們痛苦的表情。抑或是無法平復的憤恨驅使這幫男人不顧一切去飲酒取樂。我怎麽知道?
「我看得出來,你們這幫家夥今天都懶得去做昏禮 【穆斯林每日五次祈禱中的第四次,日落至天黑前進行】 了。」舒利姆一邊陰陽怪氣地說,一邊對著桌上的空瓶子點點頭。那兩人並不在意他的譏嘲,舒利姆勉強擠出笑容,緊繃的臉上一時間起了皺紋。他看上去氣得夠嗆。
布達又矮又胖,身體滾圓,但給人很結實的感覺。好像這一身肥肉並不是因為他縱欲放蕩,而是因為他有著比純粹享樂更深的圖謀。他朝我擠眉弄眼,一臉怪相:「給我們說說伊榮格雷紮的新聞吧。那兒真有在水下行駛的火車嗎?」
「瞧這個野蠻人說的,」舒利姆喊道,「你從來沒聽說過地鐵嗎?」
「你這麽一來,會讓這個英國人覺得我們都和你一樣無知。」馬吉德說道,聲音裏沒有一絲調侃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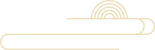

一個女孩從裏屋走了出來,穿著又臟又破的長筒連衣裙,手裏拿著兩瓶啤酒。她眼裏空無一物,似乎能夠把眼前的一切看穿。她把一瓶啤酒放在我面前。她向前探身時,我從她連衣裙的腋下裂口處看到她年輕豐滿的身體。她把另一瓶酒放在舒利姆面前,舒利姆摸了一下她的屁股,她退縮了。
「阿齊紮,我們從烏拉亞來的朋友想要你。」馬吉德突然說道,大笑著叫了兩聲。
她轉過臉來,饒有興趣地看著我。然後站在那裏等著,好像要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跟她玩玩。」舒利姆說道,同時,像屍體一樣朝我咧嘴笑著。我看到她又退縮了。
我看著那女孩,看著她尖尖的小臉和苗條的年輕身體,她沒有任何反抗。我搖搖頭,她垂下眼睛。馬吉德大笑著,站了起來。女孩轉身向裏屋走去,雙手已經撩起了連衣裙的下擺,馬吉德大搖大擺地跟在她身後。布達溫和地笑了笑,開始問我有關英國的問題。舒利姆回答了大部份,時不時會跟我確認一兩句。我想有一瞬間我聽到了一聲尖叫,煤油燈的火焰閃了一下。馬吉德似乎在裏面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出來時樂呵呵的,光滑的面龐煥發著健康的光澤。
「渴死我了。」他說著,拿起還剩著酒的酒瓶。他一口氣喝光了瓶裏的酒,帶著征服的微笑放下了瓶子。「輪到英國人了,我想。」
他們喊阿齊紮,過了一會兒她進來了,眼睛和以前一樣空洞無物,嘴角向下耷拉著。我為他們點了啤酒,並對舒利姆說,等他喝完後,我就走。我們點的吃的怎麽辦?布達問。我還有活兒要幹,我說。女孩端上啤酒後,布達站起身來,輕輕地跟在她身後走了。
「什麽事兒?」馬吉德面無笑容地問。「你不喜歡女人?去那裏面幹事吧。還是說,你不喜歡女人?她和他沒任何關系,」他說著朝舒利姆擡了擡下巴,「你把她怎麽了?」
舒利姆喝了一大口酒。「我們得去參加一個婚禮,」他喝完酒說,「你們留下來玩那骯臟的遊戲吧。」
「你把她怎麽了,你這個變態?」馬吉德問道,咧嘴笑著,享受著生命中純粹的快樂。
我們到婚禮現場時,正好趕上新郎家人和朋友陪同他到新娘家門口。兩個年輕人在敲鼓,他們瘦得皮包骨,長相相仿,臉上表情緊張、冷漠,在震天的喧囂中,似乎將目光轉向了自己的內心。房前立著棕櫚葉拱門,房子的正墻上搭著彩燈裝飾的花環。從屋裏傳來了女人們唱歌的聲音,新郎一走到門口,歌聲突然變成了愉快的歡呼聲。人們圍著新郎轉圈,跟他大聲開著下流的玩笑,新郎被請進屋時,他們突然大喊大叫起來。年輕人的眼睛開始焦急地四處張望,尋找即將要上桌的食物。舒利姆嘲弄地哼了一聲。「新娘是我妻子的親戚。」他說。
我沒想到他有妻子。「你在和貝瑟尼私奔之前就結婚了嗎?」他開車送我回旅館時,我問他。貝瑟尼是個好聽的名字,我一直希望有機會提到它。
「是的。」他說。我們正在那條通往停車場的燈光昏暗的路上行駛,但即使在那暗淡的光線下,我也能看到他臉上的怨恨和憤怒。「我和她結婚好長時間了。」
「你回來是因為她嗎?」我問。
他輕聲地笑了。過了一會兒,汽車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轟隆作響時,他開口了。「最終她給了我一份豪禮。那個馬來亞女人。我和她幹那事時,流血了。她帶我去看了醫生。醫生說不礙事,可她說我不能留下來。我不知道是什麽毛病,可我一和女人幹那事,就會流血。」
我們一直沒有說話,直到汽車停在旅館外面。「你回來後看過醫生嗎?」
「什麽醫生?這裏沒有醫生。」他說,眼睛盯著前方。然後他轉向我,帶著忸怩、溫和的微笑。「明天帶我一起走吧。到那兒我可以去看醫生。帶我走吧。你讓我做什麽都行。」他向我靠過來,那張臉緊張、興奮到了怪異的地步,笑容裏竟然主動多了哀求的意味。
第二天他來找我,盡管我頭一天告訴他,我會自己去機場。他說話時帶著平日裏的惡意和傲慢,對看到的一切都嗤之以鼻。盡管我一再讓他放下我就走,可他停下車後,在我旁邊走來走去,手裏拿著一張卷起的報紙。「像這樣的公事包要多少錢?下次給我帶一個來。要不寄一個給我,我保證少不了你的錢。我並不是說你在奢華之地需要我的錢。不過,很快你就會玩夠了,要回到故鄉來。」他說,「每個人都得這樣,要不然,就會在異國他鄉淪為笑話。」
我和他握握手,把身上剩下的所有當地鈔票都給了他。他吃驚地看著那一大捆鈔票。「希望你能好起來。」我說。
「你說什麽?」他笑呵呵地問道。他把錢揣進口袋。「下次你可得留下來呀。」他說道,然後走開了,揮揮手,沒有回頭。
原載於【世界文學】2022年第2期, 責任編輯:余靜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