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臭鱖魚是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的產物,也是相對昂貴的食材,發酵風味、重火功,是徽菜當仁不讓的代表作;筍則是「山珍」,平易近人,唾手可得,代表了徽菜的鄉野風格。』
記者|駁靜
攝影|張雷

臭鱖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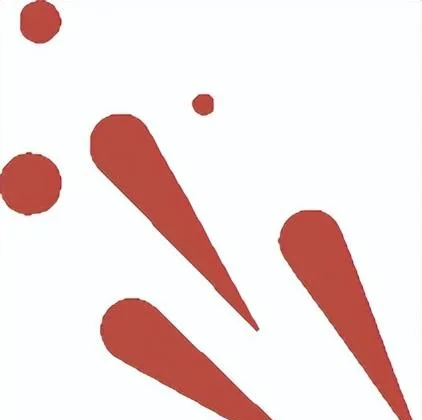
古徽州歷史悠久,可這臭鱖魚的歷史或許不足100年。時間有待商榷,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直到上世紀80年代,臭鱖魚還只是祁門人——至多徽州人逢年過節吃的一個大菜。徽菜廚師大規模開始學習鱖魚腌制,也要等到2000年以後。徽州攝影師張建平說他20年前聽朋友講起一樁笑話,說是1987年,也就是黃山設立地級市那一年,屯溪有個祁門人開的餐館,給兩位上海客人做了條臭鱖魚吃,上海人接著就將此事告到了衛生部,譴責黃山人做臭魚給他們吃。
但臭鱖魚在徽州地區流傳開來並不難,因為徽州人本就擅長吃深度發酵的東西,毛豆腐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我們到徽州的第12天,開始跟張建平走年俗的尋訪之旅,其中非常有意思的插曲,是到祁門縣城後,小小地探索了臭鱖魚的起源。
關於臭鱖魚的來源,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版本。 這個版本裏,徽州人所吃的鱖魚來自安慶與貴池,而從安慶到徽州走山路,路程需要走一周,過去徽商將貨物運至安慶後,會在當地采購鱖魚返鄉,為防變質,於是加鹽腌制。然而鱖魚仍然發臭,沒想到烹飪之後非常美味。這道菜由此開端。不過張建平一直覺得這個說法並不靠譜,他判斷的依據之一,在於祁門水系發達,徽商以陸路運魚,莫若水路合理。
舊時徽商進出祁門有三條道,去往江浙滬的走新安江,去南京的走青弋江,還有一條就是閶江,它發源於祁門深山,途經江西景德鎮,最後註入鄱陽湖。祁門三裏街沿閶江而建,憑借水路,一度十分繁華,特別是連線閶江與金東河的周家嘴碼頭一帶,商賈眾多。三裏街最西頭,曾經有座中和樓,創辦於1909年,創辦者陳鳳卿之子陳達人曾手寫過一本回憶錄。我在原稿上讀到他寫,中和樓到1942年,「因政局動蕩、通貨膨脹、紙幣貶值方歇業」。

▲鐘大廚做的臭鱖魚
中和樓的第三代陳再貴今年70多歲,他出生時中和樓就已經沒了,但從小聽長輩提及當年盛況。陳再貴退休之前,與張建平是同事,二人都在祁門縣教委工作。他現在仍然住在三裏街,只是中風後就不太能說話了,看到張建平,能含糊地吐出「教委」二字。張建平對一切有傳承的東西都相當留心,多年前,他聽陳再貴跟他談起過,說臭鱖魚就是他家發明的,也曾講述過當年中和樓是如何開始燒臭鱖魚的。
故事是這樣講的:祁門水系發達,但大多湍急,不產鱖魚,下遊鄱陽湖的鱖魚相當便宜,中和樓每年冬天都會從鄱陽湖流域買鱖魚。有一年春節後,中和樓想打個時間差,趁3月份的倒春寒,讓貨船再帶兩桶鱖魚回來。結果帶到半路天熱了,等貨船抵達三裏街,魚稍微就有點臭了。臭了怎麽辦呢?中和樓的大廚索性就用鹽腌一腌,腌完後他們自己燒一條來吃,徽州人本來就能吃點臭的東西,這一燒,發現魚肉有股特別的風味。
不過遺憾的是,陳達人的回憶錄中並未提到關於臭鱖魚的太多資訊。陳再貴的夫人不是祁門人,她告訴我們,她嫁到陳家之前,也不會做臭鱖魚,但長輩與左鄰右舍都會,她也很快就學會了。無論起源如何,臭鱖魚作為徽菜的當家菜,是確信無疑的。曾在北京一家徽菜館吃飯,一進門就有濃重「臭」味,這味道在食客與從業者心裏,或許已經代表了徽菜風格。
到徽州頭一天頭一頓,徽州文化博物館前館長陳琪帶我們到「鐘大廚」吃臭鱖魚。主廚兼老板鐘少華從業30多年,做臭鱖魚是一絕。後來再回想之後16天吃到的種種臭鱖魚,最大的感慨是,發酵食物果然風情萬千,在小飯館,在鄉村廚娘家中,在上過【舌尖上的中國】的知名館子裏,同是臭鱖魚,風味卻有很大不同。 比起烹飪手法的不同,更能造成差異的還是腌制鱖魚的手法。
鱖魚腌制之前,實際上得是新鮮活魚。但不像江浙一帶,不管多小的館子,都得備一個水缸,讓客人直接從水裏挑活魚,徽州飯館廚師備菜,通常在菜市場就讓老板殺了魚取走內臟。腌制的關鍵當然是碼鹽的量。廚師會說,這是非常依賴經驗的手藝,當天的氣溫、魚的大小,都是影響因子。少量腌制還相對容易控制,大一點的飯館,一天腌幾百斤鱖魚也是常事。那種時候需要廚師額外用心, 因為碼過鹽的魚要一條一條壓到桶裏,那麽上層的魚與下層的魚,所受壓力與鹽鹵浸潤也有區別,每隔一天需要翻桶,把底下的魚換到上面來。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
怎樣判斷腌制是否到位了呢?不止一位廚師告訴我,就看魚嘴,一旦變紅就要收手,等到魚嘴發綠,那就為時已晚。在這一點,鐘少華有不同看法。他腌制鱖魚的秘訣恰恰就在等魚嘴變綠,這個變化基本發生在第八天左右,這意味著魚肉開始二次發酵了,那時候的微生物更加豐富,也正是風味層次的來源。聞味道固然可以作為判斷依據,鐘少華說他光看流下來的鹵湯汁就能分辨,「假如湯汁是油性的,不是水水的感覺,就到位了」。
鐘大廚給我們燒的不是整條的魚,而是魚塊。原因很簡單,我們一桌四人,都是好這口的,一條魚大概率是不夠吃的,反而不如上一份塊大量足的鱖魚魚塊來得過癮。事實證明他是對的。鱖魚質地原本就緊實,腌過之後,魚肉變得更硬朗,吃進嘴裏,對牙齒會有微微的抵抗,這是魚肉少有的質地。我們一桌四人,包括鐘大廚和陳琪,很快就將其瓜分。這還不算,又要了米飯,拌進湯汁,一人又來了一碗。我一邊吃一邊心裏面擔心,吃過如此美味的臭鱖魚之後,恐怕將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會再想吃普通的魚了。
徽菜本來就註重火候,鐘少華現在教徒弟,會跟他們說有兩點很重要。一是蓋蓋燜燒的時間。菜籽油下鍋後,第一步就是把五花肉丁煸散、出油,再下生姜和大蒜等佐料,但魚要兩邊各煎烤一下,之後加入醬油、料酒和高湯,此時要蓋上鍋蓋燜燒起碼20分鐘,入味的秘訣自然在於時長,鱖魚好就好在這裏,它是很經得起燒的,一定不要浪費它的潛質。其次是大火收汁的尾聲,再加一勺豬油入鍋,能讓整個湯法變溫柔。這個臭鱖魚的醬汁,很多小飯館會因時制宜,比如到冬天,會加入冬筍丁提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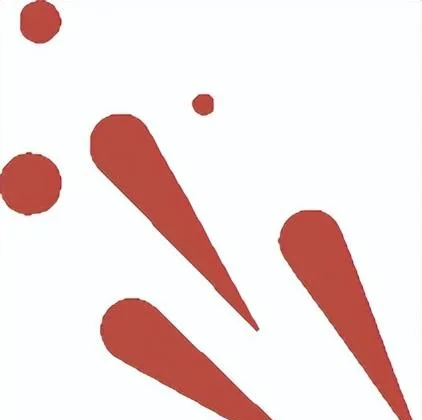
筍與筍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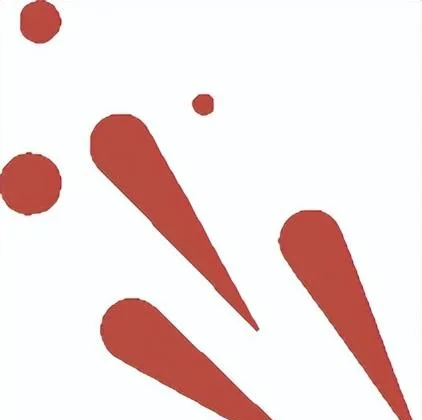
除了臭鱖魚,徽州另一樣深得我心的是筍。在歙縣的安若餐廳,小胡師傅打算給我們置辦一桌全筍宴。
我是在浙江山上見過「孵筍」的,在恰當的時節裏以水澆灌地表,就著濕潤的土地,鋪上厚厚一層竹葉。假如以溫度計測之,會發現竹葉底下比外面高上好幾度。這種欺騙的成果是,臨安春筍能比它原本的上市時節早上大半個月,那便是寶貴的溢價時機。在歙縣,一切服從自然。舉頭看問政山,滿山竹林,翠綠可親,小胡說這意味著今年算得上大年,冬筍產量不錯。像去年,下半年普遍幹旱,那個時候看到的竹林是枯黃的。他們餐廳去年也買不到冬筍,有陣子不得不拿福建和江西的筍代替,那是小胡頭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筍與筍之間可以差別那麽大。

▲最理想的筍是「兩頭尖」,這說明它很嫩
傳說中,歙縣的問政山筍嫩如嬰兒肌膚,吹彈可破。不止一個人向我描述,他們經歷過的神奇場景:一不小心將筍摔在地上,白花花地碎了一地。一個誇張的敘述一旦成勢,就容易在人們腦海裏固定為一種「事實」。我們當然是沒有榮幸見證這樣的現場的。不過問政山筍的確是鮮嫩可口,非常值得一吃。
關於筍,有三大樂趣。先是背著鋤頭去挖筍,其次是挖到筍,最後才是吃。比起吃筍,顯然挖到筍的樂趣最為無窮。
12月,農事已忙完,備年貨尚不緊迫,有山的人家會趁這時上山松土。我們在緊挨著問政村的範家村地界裏,碰到一位大爺。大晌午的,老人家在竹林翻土,半小時未曾停歇,只微微出汗。旁邊一只簸箕,裝著的三四顆冬筍有手腕粗細,頭上冒著尖兒,顏色嫩黃曲線伶俐,十分可愛。與此同時,隔壁山頭,還有小胡師傅與一位比他年紀更小的同事,正在為晚上的全筍宴全力挖掘食材。
我一會兒跑去大爺這邊問東問西,一會兒又去小胡師傅那邊指指點點。以我這個外行人來看,兩位小年輕的道行太淺,幾次見他們一鋤頭下去,就有一顆筍被攔腰斬斷。「挖斷筍」更好,或者幹脆「挖不到筍」?很難在兩個次級方案裏選出優劣。我像是在兩個直播間裏來回切換的獵奇觀眾,咂摸出一點味道後,便對兩位技藝不精的年輕人失去興趣,轉而專註地欣賞大爺松土。只見大爺的鋤頭輕起輕落, 有時明明已經擊中泥土裏的冬筍,卻能在感覺到阻礙後迅速收力,千鈞一發之時,總能保全冬筍的完整身軀。

▲我們在山上碰到的大爺正在給山松土
最後,我這位觀眾擅自為「兩個直播間」打分。只是為了松松土的大爺,戰果是完整好鮮筍七顆。小胡二人組收獲倒也不小,共計六顆,其中四顆有大破損。年輕人可以說是完敗。不過不要緊,小胡還可以憑借廚藝為自己扳回一城。當晚,小胡果然烹飪了六道菜。
餐廳裏頭吃問政山筍講究外形,所以會先拿整顆筍與整塊火腿先煨,入味之後再改刀,都切成薄片上桌前可以一蒸了事,切成塊那麽可以燉,都是鮮與鮮的組合。煨過的筍涼了之後還可以切成絲,拌上雪裏蕻,就是一個上好的涼菜。另有腌篤鮮和油燜筍,其實這兩道菜一般總以用春筍較為常見。春筍大量上市的時候,價廉物美,可以放肆地以筍為絕對主角去烹飪菜肴,但既然到了筍的產區,春筍能做的菜,冬筍當然也做得。
「山上筍,山下柴」, 冬筍埋在地下,更是見光就老。小胡說吃筍的極致體驗是上山的時候帶上塊火腿和一口鍋,挖到筍後,劈個竈,用山泉水直接煮,方法粗野,但是味道鮮美。徽州多山多茶,茶季上山勞作是很多村裏人每年必做之事,早上出門,中午吃幹糧,天黑回家,出門前煨在炭火上的鹹肉燉筍已經飽經火候。筍是最經得起燉的東西。
比起鮮筍與腌肉的組合,我更中意的卻是兩個小菜。
一個 是炒雜醬。 徽州人會制作冬醬。入冬前的小黃豆,蒸熟,讓它們發酵,與秋天下霜前采回來的新鮮辣椒碎拌在一起,加入蒜和姜,當然蒜要多一些姜要少一些。這幾樣主要元素混在一起後,就可以密封,讓它們二次發酵。過上一個月,時間也來到了深冬,冬醬就可以開壇了。春節期間,總得紅燒牛羊肉,這些腥味較重的肉菜裏,主婦可以大膽地往裏擱冬醬。在安若餐廳,小胡還會在冬醬的基礎上,再炒一個雜醬,五花肉、冬筍、茶幹,都切成丁,與冬醬炒制,就是一個上好的下飯菜,要拿去拌面吃也是不在話下。
另一個說起來也是小炒。在徽州,我發現當人們說起「澆頭」,大概率是特指筍幹炒肉絲。 起初是在歙縣的「兩棵樹餛飩」見到一大盆澆頭放在竈邊,老板娘說,她店裏老客人多,雖然都是沖餛飩來的,但一天下來澆頭面總也能賣出不少碗,總歸有嫌餛飩餃子吃不飽的客人。徽州人辦紅白喜事,鄉宴廚師一大早會燒好一大盆筍幹炒肉絲,來送禮的、幫工的,誰來了都吃碗面再走。廚師總會把這盆澆頭做得油水十足,除了筍幹,其實還有豆腐幹絲,加茭白的時候也是有的。不過有人說,不知怎麽回事,這澆頭,一大早趕做出來的,總不如頭天晚上的滋味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