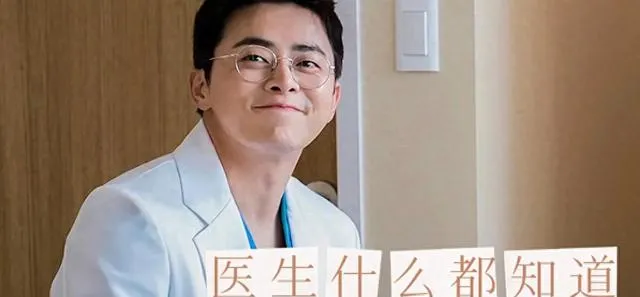
你有沒有發現,身邊堅持運動、準時體檢的人越來越多了?在不確定的時代,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態,保持身心健康,才是支撐生活的底氣。
這裏是十點人物誌系列專題報道「醫生什麽都知道」。我們每期會請一位資深醫生或醫療健康領域從業者,透過他們的講述,讓你了解更多與健康有關的知識科普。
中國醫院最缺人的崗位,醫生的死亡率比病人還高 ,十點人物誌,21分鐘
采訪、撰文 | 三金
十點人物誌原創
「外科醫生治病,麻醉醫生保命」,是行業內對麻醉醫生工作內容的普遍認知。做手術,離不開麻醉,但接受麻醉後,患者對麻醉醫生具體做了什麽卻不得而知。
麻醉醫生曾一度被認為是輕松的、受追捧的職業,只要給病人打一針就能出去休息,不需要跟病患打交道,醫患關系和諧,醫療糾紛也鮮少發生。
直到今年初,年僅46歲的三甲醫院麻醉科主任醫師、知名醫學科普博主朱翔醫生在崗位上猝死,引起一片嘩然,讓大眾重新關註到麻醉醫生這個行業:它真的如想象般輕松嗎?
早在2015年,麻醉醫生兼醫學科普博主潘傳龍就曾感嘆,中國手術中因麻醉而死亡的概率已經降到了十萬分之一,但麻醉醫生的死亡率接近萬分之二,「每當病人問我手術風險高不高,我都會說,在手術中我死亡的概率是你的十幾倍,別擔心」。2022年,他猝死的訃告沖上了熱搜。
工作強度大、時間長、心理壓力大,是麻醉醫生每天的日常。官方統計,中國現有麻醉醫生10萬人,實際需求可能達到30萬人,整個行業人手極度短缺,而一名麻醉醫生的培養至少需要十年。
作為所有科室中最容易被忽視、承擔著最多誤解的人,為了讓大家知道麻醉到底在做什麽事,31歲的麻醉醫生蔣政宇在【深呼吸,開始麻醉了】一書中記錄了自己經歷過的十幾場手術。從外科切除、兒科麻醉,到無痛分娩、無痛胃腸鏡,麻醉已經從手術室走出來,成為舒適化醫療的重要內容。每個人都得跟麻醉醫生打交道。
【深呼吸,開始麻醉了】,廣東科技出版社2024年出版
跟蔣政宇聊天的傍晚,他剛剛完成了一台持續4小時的手術,等患者醒過來,轉入ICU,他當天的工作才算是完成。從早上七點半開始,他那天一共做了三台手術,但「這遠不是最忙的時候」。
以下內容根據蔣政宇的講述和著作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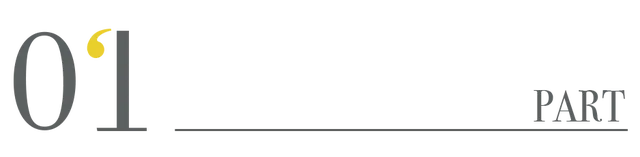
「麻醉醫生忙起來,
手術室裏沒人能好過」
暑假是我們一年中最忙的時候。一方面正常的手術在進行,另一方面,孩子們放暑假了,有時候一天一個手術室就要做七台以上的兒科手術,常常是上一台手術剛結束,下一台就來了,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最長一次,我在手術室裏呆了20個小時。
公眾對於麻醉醫生的工作不是很清楚,網上經常出現麻醉醫生猝死的新聞,但大家也不知道麻醉醫生到底在累什麽,看上去醫生不過是打了一針,患者不過是睡了一覺。其實並沒有這麽簡單。
麻醉通常是分為三個部份:鎮靜、鎮痛和肌松。「鎮靜」是讓患者睡過去;「鎮痛」是讓患者感受不到疼痛;「肌松」是讓患者肌肉松弛,在手術過程中肌肉不會因為神經反射而不由自主地動。要知道,只要動一下,手術刀就可能劃錯地方。
在麻醉狀態下,人體的保護性反射大多被抑制,身體對藥物、手術或刺激等反應不受控制。在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中,麻醉醫生需要處理可能的突發情況。換言之,病人走過的鬼門關,很多時候只有麻醉醫生才知道。
比如全麻都會面臨患者要插管的情況。這是因為肌松藥的使用,會讓患者的呼吸肌也停止運動,自主呼吸變弱,呼吸慢慢就沒有了,可萬一這根管子插不進去呢?有些人的喉嚨有畸形,解剖結構和正常人不一樣,如果沒有足夠的預判,麻醉藥給進去了,卻插不進管子,不出一分鐘,他就會窒息。
這是我們以前最擔心的情況。現在有了影片喉鏡和一些新技術輔助,發生率非常低,但也沒辦法保證百分百安全。

蔣政宇正在偵錯麻醉機。受訪者供圖
所以我們說麻醉最危險就是在進入麻醉狀態和從麻醉狀態中蘇醒過來這兩個階段,這就像飛機的起飛和降落,如果中間麻醉深度保持得好,外科醫生的操作不出大問題,一場手術其實是相對平穩的。
很多手術有一些共有的程式化的步驟。比如說肝臟手術,需要先把肚子開啟。「開啟」是比較漫長、機械化的過程,這時候大家可能會閑聊,醫生們說說最近發生了什麽事,有什麽新鮮出爐的八卦。
等到主刀醫生上台,手術就進入了關鍵步驟,麻醉醫生需要密切關註病人的各項生命指標,確保患者不會大出血或者有其他突發狀況。等到問題處理完畢,開始縫合,又是一個比較「無聊」的時間,大家繼續聊聊八卦。偌大的醫院有哪些新聞八卦,手術間都知道。
假設麻醉醫生忙起來了,手術室裏沒人能好過。這有可能是外科「捅婁子」了,需要麻醉醫生救場;也可能是麻醉或外科手術原因導致的突發情況,手術無法繼續進行,只能等麻醉醫生先忙完,穩定住生命體征,手術才能繼續。

麻醉醫生常常會戴「花帽子」。受訪者供圖
醫生難以避免遇到手術失敗的情況。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外科失敗,一種是麻醉失敗。舉個例子,有一種外科失敗的情況是病人被「開啟」之後,腫瘤轉移,或者達到無法切除的狀態,被稱為「開關手術」。這種失敗讓人很難過,相當於患者失去了手術機會。
還有一種是突發情況導致手術無法繼續進行。我在書中寫到一個例子,一個腹腔腫瘤患者,他的腫瘤重量高達60斤。對於外科醫生而言,腫瘤切除越多,患者的生存期越長。可對於麻醉醫生而言,患者的身體是否可以承受?手術帶來的出血患者是否能耐受?最後我們備血量真的不夠了,我告訴外科醫生,「主任,我們必須要終止這台手術」。
往往這種時候,可能會出現和主刀醫生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沒有誰對誰錯,大家都是基於讓患者達到最好的狀態,所以最後都會討論出一個共同的解決方案。那一次,我們叫停了手術,患者先轉入ICU,等生命體征穩定了,再去處理外科問題。
另一種麻醉失敗的情況發生率比較低,卻是很多患者做手術前會擔心的一點:我要是在手術中醒過來了怎麽辦?
這種情況是非常嚴重的麻醉事故。之前美國有一個報道,一位患者在手術過程中全程有知覺,能感受到疼痛,但動不了。這種情況很明顯是只使用了肌松藥,鎮痛和鎮靜藥物出現了問題,而麻醉醫生在手術過程中可能疏忽觀察了他的生命體征和監護器材,這種情況被稱為「術中知曉」。
還有一種術中知曉的情況,患者鎮痛和肌松藥物都有,但鎮靜不足,他會有微弱的意識,但睜不開眼睛,也可能可以聽到手術過程中醫生的對話。這是非常可怕的情況,雖然患者感受不到疼痛,但知道有人在扒拉自己肚子。
發生術中知曉有可能是因為一些人對藥物代謝情況不一樣,這也是為什麽麻醉師要一直盯著監護儀,比如麻醉深度監測、生命體征監測,如果藥物劑量不夠,我們可以加藥。另外可能有些藥針對一些患者沒有效果,這是我們需要實踐才能知道的。
每個人對麻醉的反應都是不一樣的,哪怕是一個相同體重、身高的人,也不敢斷言他們需要的劑量一模一樣,而我們在做一台全身麻醉手術的時候,需要用到十幾種藥。事實上,目前醫學界仍然沒有完全搞明白全身麻醉的原理,我們大概能知道它和大腦中某些神經的反應有關,但具體是如何反應的並不清晰。

給患者做椎管內麻醉。受訪者供圖
加上麻醉中本來就有很多「毒」藥,甚至有些劑量不正確是致命的。處方裏有的「麻精藥」(麻醉與精神類藥品)與「毒麻藥」(容易制成毒品的麻醉藥),是被嚴格管控的。這些藥用不好,就會對患者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我常說,麻醉醫生是需要在不精確中尋找平衡點的人,這個平衡點就是最佳麻醉狀態。
醫生會要求患者術前不能進食,如果吃了影響的不是外科,而是麻醉。麻醉醫生的壓力也來於此:我們永遠要等到手術開始做了,藥給進去,外科醫生切皮了,才能透過觀察患者的反應來調整麻醉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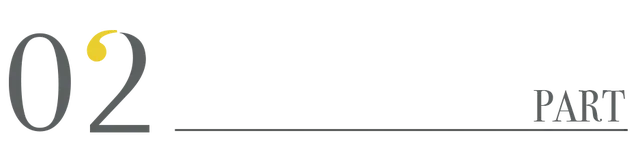
一生忍痛的中國人
大眾對麻醉藥常常有一些誤解。我們經常被家長問到,小孩打麻醉是不是會影響智商?
首先,兒童確實是比較特殊的麻醉群體,因為他們的生長發育還沒完全,相比於成年人,兒童更容易發生低體溫。術中嚴重的低體溫,甚至可能導致器官衰竭,所以要特別當心。兒科麻醉在麻醉中也是很專業的一項。
來自全球多項權威研究顯示,短時間、單次的麻醉並不會影響孩子的生長發育,而3歲以下的兒童接受3次以上長時間麻醉,的確會對智力發育產生一定影響。根據我的經驗,一個兒童如果在這個年齡接受多次手術,病情一定也不簡單。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判斷是否手術?
我們給一些家長解釋時會說,「對孩子來說的確存在一些風險,但這個風險是必須承擔的,這是為了TA能有更好的成長所必須承擔的風險」。
在手術前,麻醉醫生都會和病人進行麻醉的風險談話,我們會在這個過程中強調:你會在手術室裏看到什麽樣的場景?我們會在你身上做哪些有創的操作?你可能會面臨哪些問題?等你醒來身體會是什麽樣的感受?我們需要講清楚這整個過程,這是醫生的告知義務。
另一種誤解是針對孕婦的無痛分娩,很多人認為麻醉藥會影響嬰兒。其實無痛分娩麻醉屬於椎管內麻醉,會在孕婦背部穿刺,持續泵入一些麻醉藥物,減輕分娩的痛苦。這些麻醉藥物是不會進入血液或者透過胎盤,當然也不會影響胎兒。
電視劇裏經常有一個橋段,醫生快步走出來,問家屬:「保大還是保小?」其實我們醫生的選擇永遠是「保大」,如果成人保不住,大概率孩子也是保不住的。電視劇覺得這是個困難的抉擇,但在現實生活中,這只是一個權衡利弊的過程。
在中國,無痛分娩不是什麽新型技術,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所以我們在給孕婦和家屬介紹的時候,重要的不是這個技術有多新,而是它的普及率有多高。

【玫瑰的故事】中就曾出現家長認為「女人生孩子都是要疼一回的,用不著打麻藥,對孩子不好」的情節。
到今天,疼痛仍然是一種來自主觀的不適體驗。針對疼痛的評估是基於患者的自主評分:「假設你能想象的最疼的疼痛是10分,此時你的疼痛是幾分?」
這讓我們很難對他人的疼痛感同身受。
老一輩人愛說「是藥三分毒」,一方面擔心藥物影響智力,也擔心藥物成癮問題,結果是大家對麻醉藥敬謝不敏,反而對疼痛有了更大的忍耐度。
從2020年開始,我每年都會去西藏做醫療援助,在那裏,更多時候我會從手術室裏的麻醉醫生變成了一個疼痛科醫生。疼痛本身是麻醉的一個分支,疼痛科醫生需要治療一些慢性疼痛問題,不僅是要用麻醉藥物,可能還涉及一些註射療法。
但在西藏,最令我震撼的是,當地人非常能忍耐疼痛。我記得有一個老太太,她做農活的時候摔了一跤,左手骨折,必須用麻醉性的鎮痛藥才能緩解她的疼痛。但她自己修養了一段時間,等骨頭長了一點,繼續幹了半個月活。
我們都知道,骨頭不可能自己按照位置長好。
我問她:「你這樣咋幹活?」
她說:「我就讓它少用點力。」
後來骨科老師帶著兩個醫師給她做手法復位,老太太硬是忍著一聲不吭。

八宿縣人民醫院。受訪者供圖
我們醫療援助去的是西藏八宿縣,那裏有三個上海那麽大,但只有一個縣級醫院,除了老太太這種情況,還有非常多的民眾長期面對著關節疼痛問題,但他們也很少決定去醫院檢查。或許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長期缺醫少藥的現實,與病痛共同生活是這裏人們再正常不過的選擇。
離開西藏的時候,我在科普文章裏寫下一句話:最接近天空的地方,生活著最伏貼土地的人們。而伏貼土地的人們,也有著對生活異於常人的隱忍。

西藏八宿縣來古村。受訪者供圖
一直以來,疼痛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視的問題。我們相信吃苦耐勞的力量,認為忍耐是一種美德,對任何鎮痛藥都不放心,結果讓大家習慣了忍痛。
但在我看來,麻醉學現在有能力解決疼痛,那我們就有義務讓疼痛變成一種可以被攻克的問題。每個人都需要厘清一個概念:疼痛本身是一種疾病,而不是一種癥狀。比如我們說「頭暈」,這是一種癥狀,你可以休息;疼痛是一種疾病,它就應該被治療。
無痛是一種人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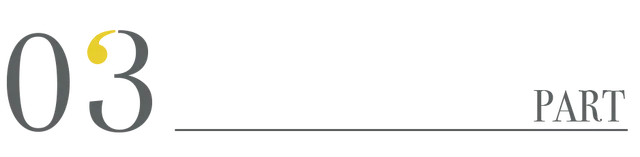
缺口最大的醫學專業,沒人報了
我高考的時候就立誌學醫,當時麻醉本科單獨招人,我想這應該挺輕松的,而且麻醉醫生挺神秘,做手術的病人都要跟他搞好關系。在我簡單的觀念中,這是個很好的工作。
一進大學就知道不太對了。因為我們的課程就比其他學科要多,實習的時候已經非常疲憊。其他專業的臨床醫學學生實習通常是在每個科室輪轉,主要工作是寫病歷、管病人,熟悉之後並不復雜。麻醉專業的輪轉有半年都在麻醉科內,雖然是實習,但由於人手短缺,在熟悉一些基本技能後,老師會把你當成一線醫生來用。別的醫學生已經下班了,我們還在手術室裏加班。

麻醉科醫生檢視每日手術安排。受訪者供圖
保研的時候,外科和麻醉科都向我投擲了橄欖枝,我心裏很猶豫,一方面感覺麻醉很累,另一方面意識到外科也不見得輕松。
我和導師討論這個問題,他告訴我:「你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在手術室裏工作時,更想要看著監護儀調控病人的生命體征,用藥、各種機器保護TA的生命,還是喜歡拿著手術刀站在無影燈下解決問題?」那時候,我還有些個人英雄主義,就覺得「你看我能讓這個病人活著」,最後選擇了麻醉。
目前為止,我已經作為麻醉醫生在手術室工作了八年。就這個職業而言,最基本的問題是人手不足導致的過勞。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如果有足夠的人手,都能得到改善。
每個醫院裏,麻醉科都是醫生需求量最多的科室,來應對內科、外科等不同的需要。一些大手術需要兩到三名麻醉醫生,並不是一個醫生負責一台手術就能解決問題,所以常常忙不過來。
【麻醉風暴2】劇照
隨著醫療越來越追求舒適化,麻醉的業務量在不斷增加。
十年前,無痛胃腸鏡還沒有十分普及,但最近幾年已經完全推廣開來。以前,我們可能有10萬名麻醉醫生來應對外科手術,但現在每年又多了幾百萬無痛診療、無痛分娩的業務,現在即使有很多孕婦想要進行無痛分娩,也可能等不到麻醉醫生。
另一方面,社會老齡化加劇,高齡患者越來越多,很多病人有既往病史和並行癥,這給麻醉手術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對麻醉醫生的要求更高。
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每萬人擁有麻醉醫生0.7名,但美國在2018年每萬人擁有2.5名麻醉醫生,英國擁有2.8名。
一個醫生的成長周期本身比較漫長,無法快速培養。
從疫情開始,國家意識到中國麻醉醫生短缺的問題,出台政策培養麻醉醫生,但四年過去,仍然只增長了兩萬人。目前的缺口是20萬,這會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問題。所以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職業吧。
我們的職業是在生命的各個階段去守護患者:孩子出生時,我們守護TA的安全;等到TA離開人世時,我們守護TA的尊嚴。
現代麻醉學創始人威廉·莫頓說:「以前,手術是一種酷刑,現在,科學戰勝了疼痛。」
到了今天,麻醉學已經從原本的手術室內麻醉,延伸到所有與舒適化醫療有關的事情。但說到底,麻醉學的初心就是維護人類在疼痛面前的尊嚴。我們就是那個「治痛」的醫生。(三金)
(摘編自微信公眾號十點人物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