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1976年7月29日上午10:30
地點:江蘇連雲港新浦區廣場
盛夏的街頭,陽光直曬。
易春利好像丟了魂一樣,在那個面積不足八百平米的小廣場上走來走去。他剛剛從軍營宿舍出來,自從知道唐山發生大地震的訊息後,他的心裏就開始忐忑不安。
易春利的老家是唐山的,剛剛結婚不到一年,老婆懷孕三個月,在這場7.8級大地震央,人究竟是死是活,一切無從知曉。
部隊領導還專門給他們這些唐山兵開了個會,說了很多安慰的話。易春利是飛行員,為了安全起見,讓他先暫時停飛。

前面蹲著一個白胡子老頭,跟前擺了個紙硬紙板,上面寫了幾個大字:蔔卦算命。
易春利心頭微微一抖,急匆匆走過去:「大爺,給我算一卦。」
老頭兒要了他和他老婆的生辰八字。
老者捧起煙袋鍋,吧嗒了兩口老旱煙,悠悠的說:「別著急,也別擔心,你婆姨命大,定能逢兇化吉,最關鍵是她腹中的孩子有福報,兒子護著娘啊。」
易春利笑了。
在那一瞬間,他感覺這個世界突然明亮起來,趕忙從衣兜裏掏出10塊錢,放到卦攤上,頭也不回的走了。
本來3塊錢的卦,他硬是心甘情願的付了10塊。

時間:1976年7月27日晚7:00
地點:唐山市針織總廠集體宿舍
這幾天,我妊娠反應強烈,吃飯老是沒啥胃口。
今天下午,突然想吃西紅杮和野菜了,讓同宿舍的季春霞下班陪我,到宿舍周圍挖了兩把馬齒莧,買了幾個西紅杮,在宿舍的煤油爐上做了一頓西紅杮雞蛋面和涼拌野菜。
季春霞也是孕婦,和我一樣懷孕三個月。
我們廠的宿舍是平房。
吃了飯,工友們聚在宿舍前,有的打撲克,有的下象棋,我和季春霞織毛衣。晚上9點多的時候,下起了雨,人們都早早回到宿舍休息了。
淩晨兩點,一陣大風夾雜著小石子打在玻璃上。我從睡夢中驚醒,只見窗戶外打起一道道閃電。半個月來,一直是這樣的雷雨天氣。
我喝了口水,躺下接著睡覺。

似睡非睡之時,耳邊響起了悶鼓一樣的雷聲,奇怪的是那雷聲不是來自天上,好像是從地下響起,從很深的地心深處傳來,接連不斷,越來越大,就像有數不清的巨石在地下翻滾碰撞。
不睡了,我心裏越來越煩。
想起身拉開燈,但就在那一瞬間,身下的床板開始了顛簸,緊接著,便是前後左右的劇烈搖擺。
轟隆一聲巨響,房頂塌了下來。
落下的房頂砸翻了我腳下的兩個水曲柳木箱,把東側的兩只床腿也給砸彎了,床板和屋頂拼結成一個大概30度夾角的狹小空間,我就被壓在這個小空間裏(以上情景來自震後我的觀察)。
想挪動身子,卻一動也不能動。
大約半小時後,倒塌的聲音完全消失,周圍的喊聲越來越大,為保存體力,我停止了呼救。
身上是屋頂,根本頂不動。我試了試挪動身下的枕頭,謝天謝地,枕頭被我從腦袋下面抽了出來,瞬間呼吸順暢多了。

又過了一個多小時,外面傳來工廠王書記的喊聲,他讓工人們趕緊去宿舍扒救工友。
沒多久,我聽到我腳下的方向傳來說話聲,腦袋上方也有腳步聲響起。
「我在這裏,快救我,」我用盡全身力氣,拼命喊了起來。
頭頂開始響起搬動磚石瓦塊的聲音。
過了一會,我頭頂上方便有光射了進來,他們打出一個洞。
有兩根椽子壓著我,一根在我頭上方,一根在我腰間。
「你看她臉都白了,不行了,」一位工友說。
「我沒有,沒受傷,」我趕忙提醒他們,生怕他們一著急,趕去別的地方。
我身上的大塊焦子頂根本搬不動,後來,有人說:「不行,就從椽子底下直接往外拉吧。」
就因為這一句話,二十分鐘後,我終於被艱難的從椽子底下拉了出來。

季春霞比我出來的早,我們倆披了件衣服,光著腳跑到2門宿舍,去找我的閨蜜於右華。
和於右華一個宿舍的王莉已經被人救出,正慢騰騰的穿褲子。那條褲子是她準備下個月婚禮上穿的毛料褲。
「感覺咋樣?」我問她。
「腰有點疼。」
「知道於右華在哪嗎?」
「沒聽到她說話。」
沒了具體位置,我和季春霞也就無從下手。
我們倆跑到男宿舍那邊。
我們先是扒出了王春友。他在二車間,開灤一中高中畢業後就到了廠裏,去年,還和我一塊參加了地委黨校和培訓。
當時,王春友趴在木板床上,身體被蚊帳緊緊包裹著。可恨的蚊帳,像一條巨蟒,纏在王春友脖子上,讓他窒息而死。

第二個扒出來的是修理工劉連江。劉師傅家在豐南,當時,他騎單車跑家,只有每個周日才能回家一次。
被救出時,劉春江臉上全是白灰,腿和床邊的單車絞在一起,費了很大力氣,才實作了「人車分離」,我們扶著他慢慢站起來。
「我不行了,不行了,啥東西也看不見,你們快去救——」話還沒說完,就倒了下去。
十幾個人,把所有的宿舍都繞了一遍,凡是能聽到聲音的地方,我們都把下面的人扒了出來。
兩排宿舍,實在聽不到任何聲音了,我們采取了一種新的辦法:耳朵貼著廢墟,仔細聽,然後拿個小木棍,咚咚的敲擊,再聽,生怕露過一點點聲音。
天光大亮。
我坐在廢墟上。不遠處,是老供電局的高壓線鐵塔,平時,附近有很多建築物擋著它,坐在這列根本就看不到它,如今,鐵塔就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
再近處一點,達謝莊的平房已變成平地,趴下的房頂,只有我腰這麽高。
宿舍前的空地上,不知啥時候冒出一個個小沙包,沙包上,從地縫裏流出的黑水留下一道道清晰的痕跡。
余震就像我此時的咳嗽一樣,不知啥時候就來一下或是幾下,大大小小的地裂縫在震動中一開一合,好像河裏的蛤蜊。

再往這邊一點,躺著十幾個傷員。我們這些沒受傷的人一起,把他們擡到沒震倒的車棚。
擡工友夏玉蓮時,大家都犯了難。
她兩條腿多處骨折,只有皮肉連著,其中的一條腿像洗衣服一樣,擰了幾道彎,要在平時,女生肯定會嚇得鬼吼,但在那時,看慣了血腥的我們,再也不覺得有多恐怖。
兩位男同誌兜住小夏的腰,我和季春霞,一個拽衣領,一個拉衣角,把他擡到車棚裏。
還沒等放下,小夏就突然喊了起來:「你們別害我行不,車棚馬上就倒了。」
我對季春霞說:「你們先去扒藥品吧,我在這裏陪她。」
旁邊的坐著的工友麻福利說:「我沒事,我只是腰疼,我來看著他們吧。」
7月29日上午,附近的居民渴得上我們廠找水。
廠裏有個大蓄水池,平時,為染布提供水源,這時卻成了大家的救命水。
人們拿著各種工具來打水,水桶,水壺,有的實在找不到盛水的東西,拿著個瓢來,再小心翼翼的捧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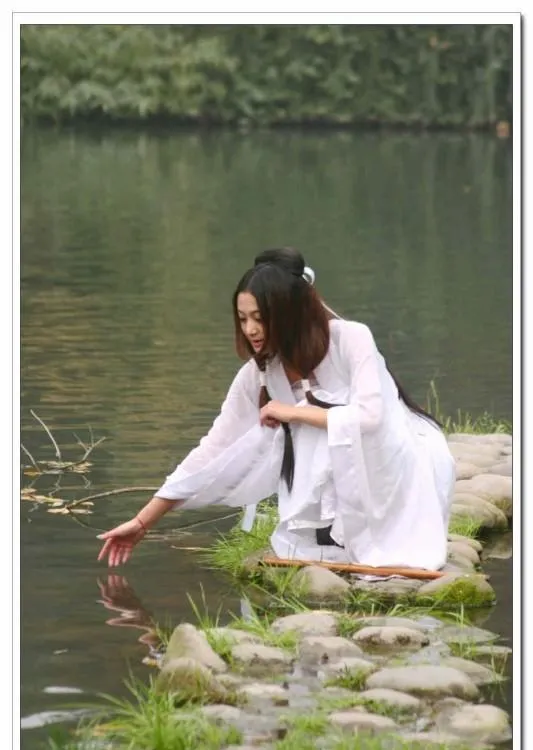
下午,姐夫騎單車從古冶來看我,見到我「完好無失真」,帶著一臉「土笑」,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
他本來是想帶我回家,見到我還要留下來看著廠子,就匆匆趕了回去。
我把他送到吉祥橋。
一路上,地裂縫一個接一下,最寬的二尺多,仔細看去,裏面好像無底洞一樣。
回來時,還見到了豬、牛、馬等牲畜,悠哉悠哉在馬路上散步。沒人找它們,也沒人打他們的主意。
迎面走來一匹棗紅色高頭大馬,奇怪的是,見了我,那馬像見到主人一樣,乖乖的貼近,頭一個勁往我臉上蹭。
我看了看馬眼睛,炸著膽子拍了拍它的鼻梁,趕緊跑開了。
唉,我騎著它,腰上再別一把盒子槍,帶紅纓穗那種的,到市裏跑一圈維持秩序,那該多好啊。
路上,太陽直直的照著,一個人也沒有。
有傳言說,陡河水庫大壩就要垮了,還有的說,市區東邊這一大片地方因為地震,再加上原來開灤采煤,馬上會地陷,從昨天下午開始,一群群人開始往市區北面奔逃。

7月31日晚,解放軍終於來到我們這裏,他們說是38軍機械化師的,來到這裏就開始扒人。
戰士們問:需要救援的人在哪,是否還有活著的。
他們把震亡的遺體全部扒了出來,碼放在車棚裏。
我把戰士們領到我閨蜜於右華住的宿舍,他們扒開廢墟,終於找到了於右華的遺體。
於右華趴在那裏,右腿向前,左右腿呈現出一個弓步,看來,地震時,她已經沖到了宿舍門口,卻沒有躲過磚石的攻擊。
本來,我們倆定好了,月底到工人文化宮看「八一」演出。
於右華的命很苦:一歲時母親去世,從小和奶奶在農村長大,兩年前,當軍官的父親把她從農村接到市裏上班。
不到二十歲,她就匆匆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看著於右華慘白的臉和額頭上一塊暗紅的血跡,再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這是三天來,我第一次失聲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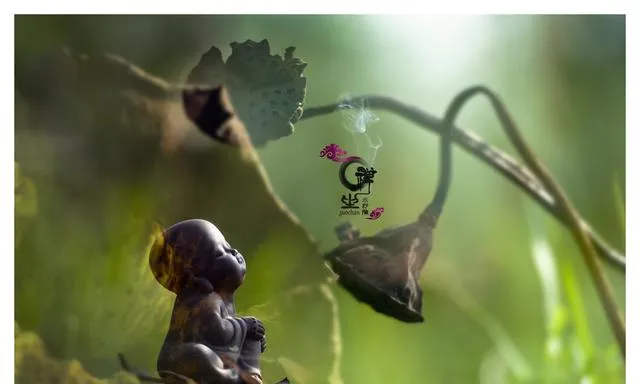
8月1日中午,我們剛吃完飯,正圍坐在樹蔭底下聊天,廢墟那邊突然傳來一陣撕心裂肺的哭聲。
是季春霞天津的丈夫來找她了。
丈夫剛剛從部隊復員,騎單車從天津趕來。進入市區後,連打聽再找,費了半天勁,終於找到這裏,看到宿舍房倒屋塌,又不見了愛妻身影,以為季春霞被砸死了。
我們找來季春霞。
季春霞也很激動,先是哭,後是笑,還輕輕打了丈夫一巴掌:「人家還沒死呢,你哭個啥?」
最後,說說幾個受傷工友的情況吧:
腿擰的像麻花一樣的夏玉蓮,半年後從遼寧傷愈歸來,精神飽滿,兩條腿完全康復,沒留下一點殘疾。

坐在車棚裏看著夏玉蓮的麻福利,不知下落。
後來,麻師傅的愛人從外地趕過來,我們查了廠裏的外轉記錄,沒有麻福利的名字。
大家反復回憶,再加上找人多方打聽,終於有了確切訊息:7月29日,麻福利坐上外轉的卡車準備去唐山機場,誰知,由於受了內傷,剛出市區不久就去世了,誰也不知道埋在哪裏。
麻福利媳婦有兩條大辮子,大眼睛,長得和電影演員似的,知道了丈夫死了,卻死不見屍,悲從中來。
她卻沒哭出聲,是含著眼淚離開廠子的。說實話,那模樣,比呼天搶地哭一場,看了還要讓人難受。
和於右華一個宿舍的王莉也死了。她平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樂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為什麽不讓自己快樂過每一天呢?
這個快樂的女孩,計劃八月份結婚。平時,我們去她宿舍,她都會把早準備好的嫁妝拿給我們看。誰也沒想到,她被扒出來後,還自己穿上了準備結婚時穿的毛料褲子。
她怎麽會死呢?
還有上文中沒提到的幾個人:
我好朋友劉樹影,地震發生時,正在家裏,被家人扒出來時,腰椎受傷。
地震第二天,我從工廠路過她家,她眼淚汪汪的告訴我,工廠有車,一定不要忘了把她送到機場去。
我沒忘記她的叮囑。工廠的卡車把她送到機場,她順利的轉機到遼寧住院。當時,在沈陽軍區籃球隊的丈夫一直陪伴在她身邊,但終因多發性感染去世。
廠裏我龐師傅,家住南廠工房,她愛人那天在單位值班,結果,龐師傅和三個孩子被埋家中,不幸遇難。
我曾經的舍友,後來結婚搬出去住的韓大姐,地震前兩個月,才從宿舍搬出去,帶著孩子住在唐山二中附近的新家。
由於和鄰居們都還不熟,地震發生後,韓大姐娘倆被埋廢墟,搶救不及時,全部遇難。
鐵路搶通後,韓大姐丈夫從外地趕過來,精神受到強烈刺激,逢人便講:「要是沒從宿舍搬出去就好了,都是命,命啊——」。
世事多變,人生無常,一場大地震把這句話演繹得淋漓盡致……
(感謝您看到文章末尾,如果您感覺上面的文字還有一點點不錯的話,那麽,可否動動您的手指,點個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