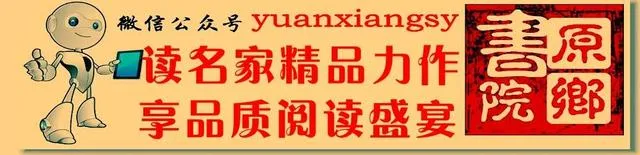
作為在中國詩史乃至中國文學史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詩人,汪國真無疑是一位聚光燈下的人物。他多才多藝,不僅是成功的詩人,還成功地成為了書法家、畫家和作曲家。但生活中的汪國真,卻優雅而質樸,待人真誠而熱情,因此有著好人緣。因為緣分,我有幸結識他、熟悉他,特別是在他不幸離世後,創作出版了他的個人傳記【遇見·汪國真】,使我越發對我們交往中的點滴無法忘懷。
我們相識在2003年年底,當時我在新華社某期刊擔任執行主編,正在為雜誌籌劃的一場論壇邀請嘉賓。我的好友,亦是我主管領導的張寶瑞向我推薦了汪國真。汪國真的名字我當然知道。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詩,在那個資訊閉塞的年代,著名詩人是個遙遠的存在,我甚至有一種錯覺,詩人這麽有名,一定是已經作古了。這種想法很可笑,可它應該是因為我心底的那種崇拜與對神壇上的詩人產生的距離感而產生的。如今,張寶瑞說起了這個名字,自然令我十分興奮,而後又聽寶瑞先生娓娓講述了他在汪國真當紅時遇見他、誌趣相投成為好友的故事,更是對與他的相見充滿向往。就在那一年的冬季,在我策劃組織的論壇上,第一次見到了久聞大名的詩人,他的儒雅、淡定與平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很快,我們又有了交集。2004年8月,北嶽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京城四大怪才」叢書,分別是汪國真的【國真私語】、張寶瑞的【寶瑞真言】、司馬南的【司馬白話】和吳歡的【吳歡酷論】。新書發行後不久,於2005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中關村書城舉行了一次簽售會。這四本書中,只有【寶瑞真言】是一本傳記,因為我是這本傳記的作者之一,便與四位名家一同參加了活動。我的位置是在最左邊,右側挨著的就是汪國真。活動開始前的間隙,我們一直在交流。他翻看著放在面前的四本書,忽然拿起【寶瑞真言】對我說:「傳記寫得好看不容易,【寶瑞真言】我已經看了,你寫的不錯。」這四本書在簽售會之前早已送到作者手中,汪國真所言不是假話,他一定是讀了。聽他這樣說,我心裏非常高興。其實,口述史的寫作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無論是哪位大家的口述史,如果成書,采寫者的二度創作都十分關鍵。此時,聽汪國真如是對我說,心頓時暖暖的,他讀了書,也對作者的辛苦有感知、有評價,雖然只是只言片語,卻足以令人感到滿足。我想,汪國真是經歷過多年退稿的煎熬後才迎來成功的,所以他懂得寫作的艱辛,更願意鼓勵年輕作者,這一點是作為名人的他極為難得的品質。此時,一個可愛的青年讀者忽然找到了我。他請我簽名的書並不是【寶瑞真言】,而是我在不久前剛剛出版的影星周星馳的傳記【周星馳外傳】。坐在一旁的汪國真看到了,問:「這是你的書?」我點頭。他又說:「回頭送我一本。」我以為詩人是在開玩笑,我便笑了。
那次簽售活動之後,我經常會在寶瑞先生組織的金薔薇文化沙龍的活動中看到他。每次見面,我們寒暄之後並沒有過多交流。這種不交流是有原因的。雖然我也行走在文學路上,但我並不寫詩,面對一位神壇之上的詩人,我很擔心會在談詩中暴露出我的不足;而除了詩,我在當時卻又找不出可以和詩人交流的其他話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每一次,汪國真只要出現在活動的現場,就會有很多人圍攏上來。他的朋友非常多,他會和大家一一寒暄,寒暄過後也不會清閑,老朋友們又會把慕名等候在一旁的新朋友介紹給他,所以他總是被眾人擁在中心裏,不得空閑。於是,我恢復了做記者時養成的習慣,只是靜靜地坐在一旁,在他與別人的交流中去感知他。
不久之後,我們有了一次偶遇。
那是2007年春季的一天,我應邀前往琉璃廠參加一位朋友的畫展,沒想到,我在那裏見到了同樣出席開展儀式的汪國真。我們打過招呼,一起參加活動。活動結束後,我便準備離開,恰好那天汪國真沒有開車,我們住的小區又不遠,他便搭上我的車一道返回。在路上,我們有了獨處的機會,也便有了暢談。
我告訴他說:「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同學之間有談戀愛的,就會把您的詩寫進情書裏,成功率挺高的。」
汪國真顯然對這樣的現象很了解:「這樣的事情確實非常多。有的人呢,可能就因為我的這些詩結合了,可有的人就沒那麽幸運,反而因為這些詩分了手。」說完,他便自顧自地笑了起來。
我很好奇:「因為詩分了手?」
汪國真邊點頭邊解釋說:「比如【河南日報】的一個記者,曾經跟我講過他自己的一段經歷。他當時跟他的女朋友正在談戀愛,就覺得我的詩特別能表達他的心聲,所以他就抄了我的一首詩送給女朋友,只不過他把詩署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結果女朋友一看就火了,說你拿汪國真的詩署上你的名字來騙我。」
我也笑了,問:「她知道是您寫的詩嗎?」
汪國真說:「對,她知道,那時候我的詩集還沒出版,但已經有很多人在私下裏抄我的詩,她很可能就是其中一個,所以對我的詩很熟悉。那個記者沒想到這個女孩子讀過這首詩,竟然知道詩的作者是我,所以就適得其反,女孩子認為他不真誠,兩個人就吹了。」
我把車開得很慢,就是想借著這樣難得的機會和他多聊聊。
我問他:「詩歌給您帶來最大的收獲是什麽?是名氣嗎?」
汪國真想了想,說:「最開始寫詩時並沒有想到會因此出這麽大的名,只是想把我的思想、感情透過詩宣泄出來、表達出來。可能我所表達的內容跟很多讀者產生了共鳴,所以會給我帶來這麽大的名氣。就像我搞書法一樣,開始練只是因為我的字不好,沒想到後來大家喜歡我的書法。我不是特意為之,只是想改變某種狀況,但這種狀況改變之後,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是出乎我意料的。」
我又問:「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您又如何看待您的詩產生的影響呢?」
汪國真先是露出了微笑,忽然又神情嚴肅,回答說:「雖然從我成名到現在已經過了快20年,可是我覺得,不管是在當時還是現在看,我的詩歌之所以能夠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還是因為詩的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你看,這麽多年過去了,我的詩集還是不斷在出版、再版,而且還有盜版,一些詩也在2000年以後陸續被選入了中學語文課本。詩集能夠被盜版,是因為在民間有讀者。我的詩集連續被盜版17年,在大陸我沒聽說過有第二個詩人。在我印象中,別的詩人的書就根本沒出現過盜版。至於我的詩被選入了課本,如果不是有積極意義的優秀作品,是不可能進入教材的,說明已經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我現在還經常會參加一些公眾節目,每次到了活動現場,主持人把我的名字一報出來,往往掌聲一下子就起來了,而且非常熱烈。所以我很高興,我覺得我的詩並沒有被遺忘。」
車還是很快到了他家的樓下,我和詩人的談話意猶未盡,可也只能就此別過。沒想到,汪國真卻問:「你下午有事嗎?如果沒事,就到家裏坐坐。」
那是第一次去他的家,裝修很簡單,也沒有想象中那麽多書。比書更明顯的是書法,墻上掛著他的字,書房裏除了筆墨紙硯之外,最有意思的就是改裝之後的墻。為了適應書法創作的需要,他把一面墻裝置成了他的桌案,由幾大塊木板組成,頂端固定在墻上,底端有支架,揮毫創作時,便不再是伏案寫字,而是垂直於地面寫字。汪國真指著墻上的木架,十分自豪地說:「在這上面寫字,可是需要功力的。」的確,在墻上寫字的功力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夠練成,汪國真這樣做,只能說明他已經把書法當成了他的事業。事實上,對於將書畫作為主要發展方向的汪國真來說,這面墻就如同他當年的書桌一般重要,已經成為他近年來使用最多的一塊創作園地。
不過,我們的話題還是沒有離開他的詩。我說:「當年的那些讀者,喜歡您的詩喜歡到了十分狂熱的地步,可是,竟然也有一些人在批評您的詩?」
汪國真眼望著窗外,神情是淡然的,他說:「當時的確有另外一種聲音,應該是說汪國真的詩俗、膚淺,沒有深度,而且這個聲音還不小,是有相當一部份人看不慣我的這些詩。」
我追問:「您那時也就30幾歲,聽到這種聲音是什麽樣的想法?」
汪國真回答說:「我是一個很順其自然的人,而且心態一直很平糊,我覺得,如果我按那些批評我的人的那個思路、那種寫法、那種追求去創作的話,那我的結局肯定跟他們是一樣的。我覺得他們為什麽沒有走出來?就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是深刻的、崇高的、有深度的作品,讀者卻並不買賬。如果讀者不買賬,事實上這些作品也就沒有意義了。」
那一天,一杯清茶,時光飛逝。詩人的話語如同我們相識時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樸實得就像個普通人,但樸實中卻讓我看到了深邃。正是這種思想上的深邃,才使他的詩擁有兩個與眾不同,其一是通俗上口,其二是富含哲理。這些都是我在這一天所領悟的,可以說,相識幾年時間,唯有那一天的談話讓我真正了解了他。
那次暢談之後,我們交往更多。比如2007年4月25日,我為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書擔任策劃,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辦了一場以青年成才為主題的交流會,汪國真作為主講嘉賓蒞臨現場,不僅與北大學子們分享了他的詩歌之路,還講述了他的散文【熟悉的地方沒有景色】的創作過程,以此勸慰大學生養成善於觀察、懂得發現的能力。比如2008年7月,作家出版社為家父的一部長篇小說舉辦研討會時,汪國真因為將赴外地參加既定的活動不能參會,便在臨行前將特意寫下的書法「風華妙筆」送給我轉交家父。當他日後獲知這部小說由郭寶昌導演改編為電視連續劇【翻手為雲覆手雨】時,他還特意給我發來短訊,表示祝賀。再比如2012年4月13日,我第一次申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他便是推薦人之一。我將我出版過的近十本書籍送去他家時,他還特意問:「有【周星馳外傳】吧?」我才意識到,當年在中關村書城簽售時,他索書的話並不是玩笑,不由得心生歉意,急忙把手中的書遞過去。他把那些書拿在手中,一邊翻看著,一邊說:「我這幾天有時間,正好都看看。」很多人都說過汪國真細致認真,那次我當真感覺到了,他那麽忙,還抽出時間看我的幾本拙作,的確難得,讀過後,他才在中國作家協會報名表的介紹人意見一欄鄭重寫下了推薦語:「欣平先生出版過許多著作和文章,其書其文都很有文采,產生較大影響,我願意推薦他入會。」雖然那一年我未能如願入會,但國真先生手書的推薦語,已然成為激勵我在文學路上努力向前的箴言。
近年來,我能夠感覺到他越來越忙,在北京的時間也越來越少。有幾次我和寶瑞先生趁他在京的間隙同去拜訪,他總是帶著興奮告訴我們一些他當時正在忙的事,比如他的書畫簽約了經紀公司,他可以安心投入創作;比如他在各地的工作室正在或即將建立;再比如他開始在電視台擔任主持人……總之,言語之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喜。或許,這種欣喜寄托的應該是他對再創輝煌的渴望。
不過,汪國真並不會因為忙碌而忘記朋友。聽說我近兩年轉向編劇、導演的方向發展,他經常詢問、鼓勵,在看過我執導的一部公益題材微電影後,還特意在微信上發來評語:「形式很新穎,主題很深刻。」
然而,我沒想到的是,這樣一位精力充沛、對生活充滿激情的詩人、書畫家、作曲家、主持人,竟然英年早逝,意外地離開了我們。
寶瑞先生是我和國真先生共同的好友,獲悉噩耗之後,他第一時間打來電話,談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建議我為國真先生寫一部傳記。他的建議裏含著深情——我記得,春節剛過的時候,寶瑞先生就曾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告訴我汪國真病重住院的訊息。我能感覺得到,他當時十分擔心,很想去醫院看一看,可是他也很清楚家屬並不想外界過多打擾的想法,因為汪國真患病的訊息當時還對外封鎖著,而張寶瑞也是從醫院的朋友那裏意外獲知的。無奈,去醫院探望的想法只能作罷。可是,已經獲知訊息的張寶瑞卻無法當作不知道,雖然無法去看望,卻先後給幾個關系密切的朋友都打去了電話,告訴大家做兩手準備——如果康復了,便組織大家去醫院探望,歡歡喜喜地去,給詩人一些驚喜,祝他早日出院;如果不幸走了,那便要盡最大力量組織起沙龍的朋友們前去送行,讓詩人一路走好。為此,張寶瑞透過醫院的朋友密切關註著汪國真病情的變化,甚至延後了去河南參加筆會的計劃。俗話說,患難見真情。汪國真溘然長逝之後,張寶瑞一直在為汪國真的詩壇成就鼓與呼,不斷在金薔薇沙龍的朋友群內轉發有關汪國真的訊息,並在追悼會之際積極組織沙龍朋友前往送行。如今,他希望能有一部汪國真傳記問世的建議,寄托的是他對老友的無限深情,而我,又何嘗不是呢?!於是,在得到家屬的授權後,我便著手采訪和收集資料,終於在2017年9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了【遇見·汪國真】一書。
斯人已逝,點滴回憶彌足珍貴。
2023年4月6日於京西禦廬
作者簡介
竇欣平,導演、編劇。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副秘書長、戲劇影視轉化創作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曾執導【止罪海】【梅花諜影】【春回櫻桃溝】【最遠的重逢】等劇情片及【北京師父】【神奇的嫦娥五號】【中華鱘的故事】等紀錄片。出版【北京古跡史話】等著作十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