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人文科學的研究中,對時間的分析始終被置於首位。空間僅被看作一個容器、一個無足輕重的舞台——眾生的命運在此展開。但近幾十年來,有生命之物的這兩類基礎座標的關系逐漸趨於平衡。【地理批評:真實、虛構、空間】一書思考了小說世界對空間的表現,並探討其與現實的緊密聯系。在後現代環境中,對現實的感知被削弱,虛擬取得了勝利。從而,文學所屬的模仿藝術得以提出一種解讀世界的全新方式,即地理批評,它同時涉及文學理論、文化地理與建築領域。本文為該書引言,澎湃新聞經新行思授權釋出。
對於空間的感知和再現並非顯而易見之事。對空間標準的理解不是永恒不變的,對場所資訊的解讀也不是靜止的。我們的文化仍受到啟蒙時代乃至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時間不能被簡化為河流隱喻,以展示其緩緩水平流動;也不能被歸結為矢狀隱喻,以建立其可逆性。同樣,空間也不是符合實證主義趣味的歐幾裏得幾何所界定的平面容器。愛因斯坦的革命由此而生。自那以後,一切都是相對的,甚至連絕對也是相對的。自20世紀初期以來,歐幾裏得已不是從前那個人,亦不再意味著相同的事。空間的標記在哪裏?空間的穩定座標在哪裏?或許,空間自一開始就逃避了歐幾裏得秩序的桎梏。一直以來,空間都被象征性地解讀。地理的具體細節屬於精神闡釋而非直接觀察的範疇。在談到基輔羅斯時期文獻中涉及的地理空間時,尤裏·洛特曼寫道:「地理學已經成為一種倫理學。因此,地理空間中的每一次運動在宗教和道德層面上都具有意義。」 當然,中世紀傾向於這樣一種觀念。聖奧古斯丁很早就定義了中世紀時期的時間觀,他認為,中世紀的時間強化了人向上帝靠近的節奏,上帝主導人的思想,控制人的靈魂。至於空間,誠如朱塞佩·塔第奧拉所言,「顯然是本體論的、精神的、指示性的;像時間一樣,空間也成為象征行為和宗教行為的場所」。當傳說中的愛爾蘭修道士聖布倫丹(Saint Brendan)離開克里海岸,向著天堂啟航(Navigatio)時,他選用了教歷,追隨的是【聖經】模糊記憶所標識出的航線。歐幾裏得被遺忘了,其實他從未被僧侶和經院神學家所重視。空間——以及在空間中展開的世界——是象征體系和思辨的產物。它還是彼時的一絲光亮,讓我們大膽地說出這個詞——想象。無論何時,這種想象都不會與真實割裂。二者依據受宗教正典支配的相容原則而相互滲透。上帝創造了萬物,萬物具有同樣的先驗的現實,預先規避了日後出現的真實與虛構的分裂。但丁正是根據這種全景(和垂直)的取向構思出【神麴】,這一取向賦予他理解彼世的三個維度:地獄、煉獄、天堂。和但丁一道,整個中世紀都理想地提出了米哈伊爾·巴哈金所謂的「萬物在永恒裏共存」的觀點。完整的空間是對超越自然的思辨和對創世的折射。如果在物質運動的尺度上時間概念是靜態的,那空間的概念則更具動態性。【神麴】中,但丁這個人物與其刻畫和面對的空間環境本能地結合在一起,而時間卻幾乎沒有流逝(除非主人公在逃脫永恒時間的煉獄裏失去生命,否則時間將永遠不會流動)。
時空概念的演變始於文藝復興時期。巴哈金曾在【美學與文學問題】(1975)中對這個過程做出評價。他強調了時間由垂直轉向水平這一根本轉變的重要性,這一轉變意味著 「一種向前的沖動」,甚至是向前的飛逝。巴哈金還補充道,相反,因為繪畫和繪圖中透視的引入,以及我們的地球列於太陽系中,人們對空間的感知變得垂直化。幾個世紀以來,這種轉變有所加強,至今也仍在被證實。但需要思考的是,我們的空間、時間和文藝復興前常見時空觀的一部份顯著特征再次建立了聯系。上帝可能已經死了,誰又知道呢?反正尼采死了。但無論上帝的命運如何,都不再是這些爭論的中心。我們的社會不再憧憬超驗。社會的時空布置還沒有重新回到垂直,但也不再是水平方向。定位的有效性減弱。後現代主義在對現代性的質疑中發展,並站穩腳跟,使當代與某種原初世界(proto-monde)產生調和。該原初世界宣告了以萬物相容和共存為標誌的世界的一致性。後現代主義還挖空心思,力圖在異質之中建立一個整體一致的王國。「一致」與「異質」,這兩個詞的結合有力地說明了新時空的混亂。本研究也將在後現代迷宮般的領域中展開。
通常來說,回顧後現代史比追溯空間的再現史更容易:因為前者最多六十幾年,而後者則經歷了整個人類發展的跨度。在這個令人沮喪的數據面前,我們放棄了。但是,後現代主義往往仍被定義為缺乏定義。這一由不恰當的語言詮釋的「矯飾主義」的空白,構建了不斷拓展的研究視角。沒有必要再對此進行回顧或再開展探索。總之,本文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會簡要涉及後現代主義。在此,我就【後現代主義的空間:人文地理解讀】一書中的若幹原則進行闡述。作者邁克爾·J.迪爾和斯蒂文·弗拉斯提認為,在一切普遍存在的體制中,後現代主義帶來了一種極端不確定卻具備準則的本體論。後現代主義在20世紀的滿目瘡痍中產生:沖突、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的硝煙未盡的斷壁殘垣,語言和再現單元的嘈雜廢墟。維特根斯坦及其後繼者曾揭示和分析過這種語言和再現的危機。歸根結底,建立在所謂「客觀」(實證主義的)感知上的和諧是意識形態上的,它曾經存在過,但在崩潰時釋放了各種各類的主觀性。話語在混亂中大量湧現……迪爾和弗拉斯提證實:「因此,我們的再現舉措(即在與我們研究「結果」的「客觀」關系方面)和調解沖突闡釋的嘗試註定會失敗。」追隨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和其他學者的思路,他們還補充道:「總而言之,後現代主義撼動了現代主義關於理論能夠反映現實的信念,代之以片面的、相對的觀點,強調理論建設的偶然性、間接性的本質。元理論和結構性思維被拋之腦後,取而代之的是微觀解釋和不可判定性。後現代主義者比大多數思想家更善於把相對主義語境化,容忍它,並時刻意識到差異。」 不過,在此種環境中,我們得承認: 相對主義也被相對化了,除非是百分之百的相對主義。現實成為一個「復數詞」 。這裏探討的現實顯然是「客觀的」現實。這是我們長久以來所期盼的,也是迪爾和弗拉斯提等執著的地理學家們所捍衛的。
在這個變得或被變得遊移不定的環境中,與世界保持著模仿關系的藝術角色取得了新的意義。文學、電影、繪畫、攝影(此外還有音樂、雕塑)等不勝列舉的藝術,能否沖破審美的禁錮重新歸入世界?這是個難題,答案從一開始就只是暫時的、隨機的。我們不想在此提前開始討論,先提出假設:如果對指涉的時空框架的感知變得模糊,那麽藝術承載的虛構話語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其獨創的意義。在長達半個世紀甚至更久的時間裏,這種虛構話語不再明顯地遠離真實邊緣,它獲得了強有力的說服力。如果可信度始終以「真實」世界為參照標準,那麽在後現代的廣闊天地下,人們不再會說水泥、混凝土、鋼筋搭建的世界比紙和墨水營造的世界更「真實」。我在上文提到後現代主義的迷宮,其實每一個在空間上被等級化了的迷宮的中心都有一只妖怪。古代畸形學裏的人身牛頭怪物一半是人一半是牛。而如今它是什麽樣的呢?如果它還繼續存活,又將會是什麽樣?可能它仍是妖怪,一種合成體,但像很多其他妖怪一樣,它已經重獲新生了。人們神往於不同的「金剛」電影中所交織出的扣動心弦的浪漫,想象著那些與美女相遇抑或相戀的野獸。這是因為時間是異質的。迷宮的中心,人身牛頭怪成了規範現實(可用「常態」一詞概括)之間的新聯盟的具體象征。這個規範現實不再脫離虛構且被置於規範之外。那如今是否還有訴諸至上地位的觀點呢?殖民統治土崩瓦解,此後一對多的文明、膚色、宗教統治分崩離析;同樣,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一種性別特征對另一種性別特征的支配統治也一去不返。在上帝的緘默之中,多元共存的時代來臨了。因此,這種類比與中世紀對存在維度的感知有關,差異是絕對的。統一、全面的規範的缺乏就意味著侯世達所指的「異質等級」(hétérarchie),一種去神聖化的等級,一切優先都消失殆盡。在失去規範的背景中,當虛構脫穎而出成為理性解讀世界的關鍵時,時空是怎樣的?設想怎樣的方法可以去試著體會無法認知的事物?上述疑問帶有悖論性質,我們將在下文用大量篇幅來嘗試解答,以謹慎和謙遜的方式來捕捉這種捉摸不定的環境。
還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我們所說的空間是什麽?乍一看,空間是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它要麽朝著無限大擴充套件,要麽縮減向無限小,這個無限小本身也是無限(無窮盡)的廣闊。總之,盡管我不甚了解這個宏觀或微觀的空間,但從宇宙的角度,從普遍的意義來說,那些專家似乎也沒超前到哪兒去。地理學家埃爾維·海格諾德認為,「我們不知道空間是不是無限的,不知道它將會無限縮小還是會無限膨脹,不知道它是什麽形狀的……我們只知道空間和我們對它的心理經驗沒多大關系,它更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感知」 。鉗制我註意力的並不是這個絕對的、整體的空間,盡管它在文學和電影裏的地位彌足輕重。這個空間實際上彌漫著科幻的色彩,是投射到感知以外而又不超出想象的全部可能世界所營造的空間。我將集中研究這些可以感知的空間,它們本身與定義格格不入,因為就像海格諾德在書中說的那樣:「涵蓋一切地理問題的整體空間並不存在,即使將其簡化為理論定律。」這觀點不僅對地理適用,對文學和其他模仿藝術也同樣適用。冒著些許風險,我們可以提出兩種研究可感知空間的基本方法:一種比較抽象,另一種則尤為具體;前者包括概念上的「空間」(space),後者是實際的「場所」(place)。但是兩者並不相互排斥,那是因為空間和場所的分界並不那麽固定。美國地理學家段義孚在他的【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一書中視空間為自由且流動的領域,而場所則是一個封閉的人性化空間:「與空間相比,場所是一個既定價值的安靜的中心。」 這個觀點在美國引起了特別的反響。段義孚認為,只有當空間有了定義並獲得意義時,才能轉化為場所。他還補充道:「所有人都試圖將難以名狀的空間變為清晰的地理。」對任何生物而言,場所都是一個目光停留的標記,一個停頓,「一個休憩點」。空間和場所的區別曾被地理學家、社會學家研究過,被那些意欲將理論思考套用到場所上的學者所研究。
面對「空間」和「場所」界定上的模糊,有些學者更傾向探索其他方法。意大利城市規劃家弗萊維婭·斯齊亞沃在主張適度和批判性地使用空間一詞後,又直接提出用背景(contexte)概念將其替換,因為背景凝聚了(空間和場所)這兩個詞所包含的物質和非物質價值。她認為:背景涵蓋了社會、文化等領域,這些領域「組織了居住場所的整體建築」。總之,被賦予特性的空間進入了對於場所的構建,空間與場所二者結合形成背景。現象學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們認為應當把作為男人(和女人)意向活動的場所——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爾·舒茨)——與完成這些活動的背景——自然環境(Umwelt)——分離開來。然而,難點在於廓清純人文的空間(生活世界)和環繞人類的空間(自然環境)相互影響的類別。此外,如果我們贊成另一位同為意籍的地理學家瑪利亞·德·法妮斯的觀點,那麽主體就可以被理解為「實體,在以空間為樣版進行自我塑造時,並讓空間承載了個體和集體的行為、觀點、價值,此三者把空間轉變為場所」。顯然,要想直截了當地跳出空間和場所的二元對立並不容易。接受批評研究的發起人漢斯·羅拔·姚斯也對這個辯論做出了貢獻。根據關聯軸理論的作者、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舒茨及其學生杜文·盧卡曼的研究,姚斯把一種日常現實納入時空的範疇,並將其「理解成一個我與他人共享的主體間的領域」。這種現實由「空間關系上的‘這和那’(ici-et-là-bas)構成,就好像面對面的位置關系所營造出的關系世界[人文關系(Mitwelt)]一樣」。如果說自然環境源於觀察,那麽人文關系則意味著一種行為,或更準確地說,是一種相互影響,它賦予了個體存在的意義。姚斯深受現象學家的啟發,並像他們一樣,提出了 「空間關系的‘這和那’,由此日常現實便在圍繞的環境中形成」。
事實上,這種關系的研究推動著整個地理批評的發展,透過文本、影像以及其他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化互動來深入研究模仿藝術布置的人類空間。在嘗試確定地理批評的方法論以前,我計劃透過三個部份勾勒出地理批評的理論基礎。本書將首先圍繞空時性(spatio-temporalité)展開思考。在這一部份,讀者將看到二戰以後時間隱喻如何逐漸得到空間化,空間以怎樣的方式重獲價值提升,並壓制了時間這一曾在文學批評和理論中占據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的元素。然後,我將思考當代空間的一種常態,即它的流動性,它很可能會具有長期性。當今是否存在一種永久違抗、持續跨越的狀態——一種可以讓所有空間成為完全流動起來的整體的越界性(transgressivité)?透過空間性,遊移構成了一次歷險,第三部份也由此應運而生,它將對世界空間與文本空間(或影像)、指涉物件與再現的關系做出理論的思辨。第三章將探究指涉性(référentialité),即真實與虛構以及世界空間與文本空間之間關系的實質。本章將為可能世界理論留得特殊一席,歐洲及盎格魯—撒克遜等國的思想家效仿艾力修斯·邁農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在所謂「客觀的」現實世界和抽象世界、文本世界之間搭建起一種類比。如果我們參考「空間」和「場所」傳統意義上的區別,便會註意到前三章優先考慮了空間,因為時空性、越界性、指涉性描繪出地理批評所構建的概念框架。然而,盡管二分法會在下文中得到消解(我認為,「空間」和「場所」會在「人類空間」中合流),但是得承認,地理批評和場所研究範疇更為匹配。第四章陳述地理批評的方法論。這將給我一次機會去完善我曾在【走向文本的地理批評】一文中首次提及的若幹想法。該文發表於2000年,並收錄在【地理批評的說明】一書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本書開啟了地理批評的冒險之旅。在臨時的而非總結性的最後一章中,我們將考察文本在場所建構中的重要性,並把文本的空間性轉變為場所的可讀性。我把指涉性問題放在最後,並自問是文本造就了場所,還是場所成就了文本。在結構主義日薄西山之際,小說文本回歸到了世界並在此安身立命。它能否投身於世界的創造之中?
我的目標之一便是開始起草一份「空間邏輯」 (spatiologique)的清單,打破批評場的國界限制,超越虛構語料的語言界限,跨越不同學科的門檻,因為文學在這裏,在一個給予地理、城市規劃,還有其他多門學科以重視的環境中被重新考察。如此就顯而易見了:千禧年之初以來,文學及其他模仿藝術,正因為它們的模仿性特征,不再能與世界隔絕開來。一切都在一切中,那麽反之亦然嗎?可能吧,這便是問題的所在。但並不排斥的是:正是在絕對的異質中,批評話語的自由才能表現得愈發從容且愈發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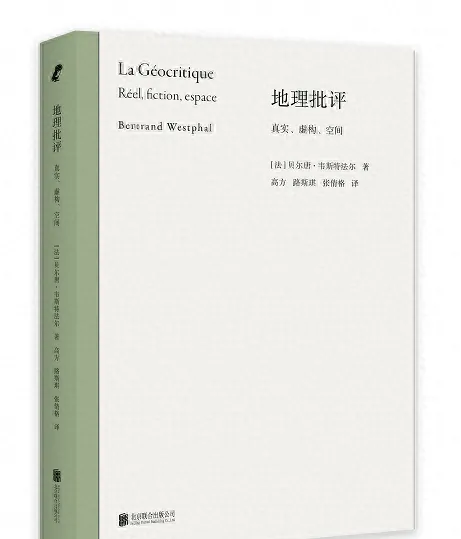
【地理批評:真實、虛構、空間】,[法]貝爾唐·韋斯法爾著,高方、路斯琪、張倩格譯,新行思|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