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是六七十年代建的二層筒子樓,每層有一個大長廊串聯起每間宿舍,走廊裏有公共水房和衛生間。
宿舍很小,一進門當間一張大條桌,兩邊靠墻擠放著三組鐵架子上下鋪,門正對著北窗。

我是宿舍最後一個到的,捷足先登的同學早已把好位置占了,只剩下門邊的一個下鋪還空著,我拆開行李鋪好床,拿出葡萄乾請大家吃。
宿舍有六位同學,其中三位是天津的,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就像頭車上搶行李架,先到先得。
靠窗的下鋪坐著一位同學和來送他的父親,他自我介紹叫王津,是個大個兒,差不多有一米九,家是天津寶坻縣的。聽說我從新疆來,父子倆用天津話好奇地問這問那:
「新疆都是大草原吧?」
「你們家有駱駝吧?」
「你上學是騎馬嗎?」
新疆人進入內地額頭上都頂著一個標簽「新疆」,好像我們都是騎著馬或駱駝來的。
八十年代資訊閉塞,沒有手機,電視節目少得可憐,內地對新疆的認識僅限於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和語文課本上那句「早穿棉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新疆不是騎馬、跳舞、羊肉串,就是葡萄、西瓜、哈密瓜。

這不能說是無知,這跟新疆人不了解內地是一樣的。地理空間上的遙遠和封閉,對應著心理和觀念的鴻溝。在內地人的潛意識裏,新疆地處邊疆,是貧窮和落後的代名詞,而在新疆也存在對內地人的偏見和貶低。
宿舍裏除了三個天津人,還有一個河北人,一個江西人。王津上鋪的同學來自江西,叫杜平,與他們對面的上下鋪住著兩位天津同學,一個叫陳樂,一個叫皮海東。
杜平說,對面兩個天津同學報到完放好床褥就回家去了。杜平一口的江西口音,他說自己是江西老俵,他的話我只能聽懂十分之一,而我對江西的了解僅限於井岡山和電影【閃閃的紅星】。

我上鋪的同學個子不高,人很熱心:「我叫郭冀,從河北邯鄲來。」
他帶著我到學校商店買了蚊帳、飯盒和臉盆、牙刷之類的洗漱用品,又去食堂換了飯票。聊天中得知他家在農村,家裏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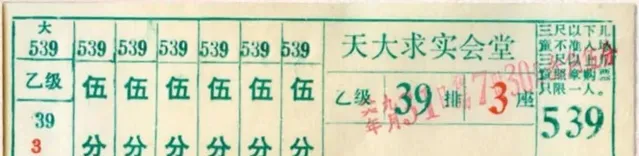
學校湖泊水系很多,後來才知道這是蚊子多的原因。
在天津住的第一晚,天津大學碩大的蚊子先給我一個見面禮。我一晚上沒睡,一直在蚊帳裏跟嗡嗡叫的蚊子作鬥爭,第二天起來發現撓出一身大紅包。我沒有使用蚊帳的經驗,蚊帳沒關嚴,蚊子從縫隙鉆進來,給我結結實實上了第一課。
新疆沒有蚊子,新疆少數民族有一個笑話模仿蚊子的聲音:蚊子圍著人轉圈,一直叫著「舅舅舅舅~」,於是人就放松了警惕,等到覺得疼想拍時,它已經吃飽喝足,一抽身喊一聲「驢肉~」便逃之夭夭了。

第二天,班裏同學都到齊了,在一間大點的男生宿舍,全班開了個見面會。輔導員叫王建強,天津人,人很年輕,今年剛在本系畢業後留的校。
全班有二十個男同學和六個女同學,男多女少、陽盛陰衰是工科院校的特點,漂亮的女同學更是鳳毛麟角,工科院校裏的校花、系花對於如饑似渴的青春期工科男來說,簡直就像羊掉進了狼群。
輔導員讓每個人介紹一下自己家鄉的風土,我想開玩笑,就說:「我家鄉新疆的確又有風又有土」,逗得大家笑成一片。

天津人愛說:真哏兒,以前聽範振鈺和高英培相聲裏常這麽說,當時不懂什麽意思,現在到了天津,才知道就是北京話「真哣」的意思。
天津話「女」不讀怒nu,讀nv,管婦女一般叫大姐。普通話有一二三四聲,天津話裏似乎只有二聲和四聲,一聲變成四聲,三聲變成二聲。
比如踢球說成「替球」,包子說成「報子」,馬三立說成「麻散立」,總之不是上聲就是去聲,這讓天津話聽上去就像彎彎曲曲的海河。(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