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蘇格蘭新的一則法案引起西方社會的關註。這則於今年4月1日生效的【仇恨犯罪與公共秩序法案】(Hate Crime and Public Order Bill)整合了包括殘障人士、種族、宗教、性取向、變性人身份等多個維度的保護條款,同時還引入了對受保護群體進行「煽動性仇恨」的罪名。
讓這一法案引起爭議的是J.K.羅琳——一位過去幾年始終處於輿論風暴中心的作家。在接受英國【獨立報】采訪時,蘇格蘭民族黨的安全部長西奧比安·布朗(Siobhian Brown)就表示,根據新的法案,羅琳可能因為此前一系列針對跨性別者的「不尊重」言論受到調查——當然,這一切需要等待警方的判斷。目前身在他國的羅琳也在社交媒體上不無嘲諷地表示:「自己等待著在回國的那一刻被逮捕」。
羅琳近年來的遭遇是一種時代的縮影。客觀來說,她有關跨性別人士的言論可以為公眾反思言論邊界提供一個好的契機。然而真實的網絡世界似乎並非如此:自從她2020年稱呼女性為「來月經的人」後,【哈利·波特】系列的眾主演聯同粉絲發起激烈抵制,她本人也接連收到郵包炸彈和死亡威脅。更重要的是,羅琳的支持者與批評者往往在開始爭論前就已經給對方打上了標簽:「恐跨癥」或是「獵巫者」。此時,具體而溫和地探討觀點本身的內容,已經不再重要。
2018年,美國電腦科學家積倫·拉尼爾出版了新作【立刻登出你的社交媒體賬號的十大理由】,他認為社交媒體正在「對我們的靈魂產生深層次影響」,社交媒體讓我們的觀點變得極化,從而降低我們對他人基本的理解和共情能力。這本書一經出版,很快成為了國際暢銷書,在不同國家都收獲了很多共鳴。近期轉譯出版的【打破社交媒體棱鏡】也對此作了討論。
撰文|劉亞光
走出資訊「繭房」,
對話也可能極化
莎拉·倫登自稱是一名「溫和的共和黨人」,她說自己「從來都不是非常忠於某一個政黨」。莎拉的祖父母來自波多黎各,她對美國的移民和少數族裔困境有天然的同情,也因此認為共和黨的很多對移民的主張無疑是對這些「陰影中的人」的傷害。在就讀大學期間,莎拉經常閱讀【紐約時報】和【紐約客】這些刊物——它們並不太會出現在許多共和黨人的餐桌上。在許多社會問題上,她都表現得像一個美國社會中純正的自由派:反對對同性戀者進行攻擊、支持變性人的公民權利以及女性的墮胎自由等。

紀錄片【推翻羅訴韋德案】(Reversing Roe,2018)畫面。
在莎拉看來,她之所以是一個溫和派,是因為政黨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候的結果會更加被她納入是否支持這個政黨的考慮。比如她認為在經濟問題上,「民主黨常常關註那些讓人有點分散註意力的議題」。然而這種立場卻給她與朋友相處帶來了困擾——當她的自由派朋友堅定地表達「俄羅斯應該對美國的一切負責」這樣的言論時,她盡管完全不贊同,卻礙於情面不想爭辯。久而久之,她只能選擇疏遠這些朋友。
更嚴重的困擾出現在她與家人之間。莎拉的一個阿姨是堅定的自由派,對杜林普「恨之入骨」,經常在網絡上發表「不知道為什麽會有人投票給一個性侵者」這樣的言論。每當看到此類動態,莎拉都感覺為難。「我很抱歉,如果那是她真正的感受,那麽我不再需要在社交媒體上與她聯系,因為我認為把未被法院判罪的人稱為強奸犯是精神錯亂的表現」。她接連在網上取關了幾個自由派的家庭成員,也表示不會再在網絡上發表溫和的觀點。
莎拉的處境是美國政治學者克里斯·貝爾在研究社交媒體極化問題的過程中碰到的一個案例,也是我們每一個身處社交媒體時代的人常常會遭遇的窘境。如今,我們可以「愉快」地使用的社交媒體可能只有永遠「歲月靜好」的小紅書,但凡去到任何「試圖」討論稍微嚴肅一點議題的網絡空間,只能目睹一片狼藉:對話從簡單的觀點分歧迅速上升到「地域黑」、貼標簽,乃至罵戰和網絡暴力。即便是在自己和親友相對私密的微信群裏,因為討論一言不合而相互拉黑、「友盡」的事情發生的也越來越多。如果分歧涉及的是「審美」,比如對藝術作品的看法——例如最近對奈飛版【三體】的爭論,這種相互的「拉黑」可能還有些挽回的余地;如果一旦涉及重要的社會公共事件,例如曾經的江歌案,討論中不同觀點的極化可能確實能到達「不共戴天」的程度。

奈飛版【三體】(2024)劇照。
在莎拉的遭遇裏,她面對的困難並不在於要如何解釋雙方觀點的不同,而是當阿姨用「強奸犯的支持者」來形容持對立觀點的人時,任何相對理性、溫和的立場已經沒有了對話的空間——作為對立方,你只能選擇用另一種具備道德制裁力的標簽形容對方,給自己「疊護甲」,才能擁有進行討論的資格——如果接下去的對話還能叫做「討論」。在網絡上進行有關性別、族裔、地域等涉及身份認同的討論時,這一點尤其明顯。近年來西方有關「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爭論雙方,也常常面對這種處境。2021年,【華盛頓郵報】一篇反思「取消文化」爭論的文章就指出,「取消文化」的擁躉常常對一個人的某一個想法和觀點產生「過度」的癡迷,即如果一個人此刻表達的想法不符合某一套價值觀,就意味著他全部的想法和行動都與這套價值觀背道而馳。這其實是一種多少有些畸形看待「異見」的態度,就像莎拉苦惱的一樣——一個共和黨人完全可以在某些社會問題上與自由派站在一起。

【打破社交媒體棱鏡】,[美]克里斯·貝爾著,李坤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潮汐Tides,2024年3月。
貝爾的【打破社交媒體棱鏡】認為,人們對「異見」的這種偏執化理解是讓人們難以好好對話的重要原因。他還進一步地提出,走出這種偏執、正確地看待「異見」,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容易。在這一點上,過往的研究者也許過分樂觀,他們認為人們不理解「異見」主要是一個資訊接收問題。只要盡可能地讓人們走出自己的「繭房」,接收多元的資訊、觀點,「繭房」就能被打破。但貝爾的研究發現,當走出「繭房」的人們暴露在和自己非常不同的觀點面前,人們的觀點反而可能變得更極端。
貝爾認為,這種現象與社交媒體作為一面「棱鏡」對使用者身份認同的扭曲有關。他援引社會學家保羅·迪馬喬等人的研究,指出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常常過高地估計自己與對立陣營的立場差距,而社交媒體則助長了這種「虛假政治極化」的現象。社交媒體能賦予極端的表達者更強的地位感,註意力經濟下引發爭議的表達所帶來的高關註度與流量,這些都使得社交媒體平台充斥著極化的言論,它們也扭曲了人們對自我與他人之間差異的認知。
在這種背景下,在網絡上理解「異見」就變成了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即便一個人有對話的意願,但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他也很難在面對一個充滿挑釁意味的極端言論面前保持耐心。因此,貝爾給出了一些更為「現實主義」的建議,比如,一旦我們希望開始關註與自己觀念不同的人的賬號,不要立即開始與對立立場的人對話,相反,我們應該花一些時間研究他們在「關心什麽」。對支撐對方觀念的底層世界觀理解越多,我們就越有可能使用對方容易產生共鳴的論點展開討論。
只不過,現實中更多的時候,人們的選擇是如拉尼爾建議的那樣:退網。
反省是溫和派的「墓誌銘」?
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政治溫和派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對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討論感到「精疲力盡」。與之相對,持相對極端立場的人在社交媒體上評論、釋出或與他人討論有關政治內容的可能性是溫和派的兩到三倍。溫和派的沈默與「退網」,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交媒體極化的惡性迴圈。
貝爾發現,這首先與溫和派遭受的攻擊相關。對於極端派來說,攻擊不如自己「純正」的立場是一種團結儀式,用於加強與自己觀點相似的人的連線與歸屬感。他調研的一名極端素食主義者埃倫·科恩就從指責自己黨派的人吃肉,到指責更大範圍的支持養殖業的人群。極端派的這種「觀念內卷」讓溫和派的活動範圍不斷縮小。

【敏感與自我】,[德]斯文婭·弗拉斯珀勒著,許一諾、包向飛譯,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3年4月。
溫和派感受到的攻擊還可能以另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呈現,那就是「溫和」本身遭遇的汙名。德國哲學學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與自我】中描摹了「雪花」和「潮生人」兩個群體,相對於二戰後嬰兒潮期間出生的這代人,年輕一代在觀念上變得更為敏感。他們鮮明地體現了社會學家萊克維茨所說的「獨異性範式」:極力強調每個個體的「不同」,「世上沒有兩片雪花完全一樣」。獨異性範式主張,個性應當被事無巨細地保護,「雪花」們高度敏感、獨特而不可觸碰。這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一種權利意識的崛起,但它同時本質上也是一種拒絕溝通的姿態:因為要盡最大可能保護個體的不同,因此試圖融貫不同立場的努力被詮釋為「和稀泥」。「做自己」「真性情」是社交媒體時代通行無阻的貨幣,而溫和派、「理中客」則被唾棄。弗拉斯珀勒也認為,「經濟方面不穩定的增加,生活中抑郁的加重,作為辯論場所的公共空間的侵蝕,這些都清楚表明了獨異性範式的問題所在」。
此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溫和派的主張本身可能就給他們帶來了過多的心理負擔。正如貝爾所指出的,極端派之所以轉向社交媒體,是因為社交媒體為他們提供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缺乏的地位感。但對於溫和派來說,正是因為他們更多地考慮觀點與人的復雜性,他們希望盡可能尊重人群之間的差異,也就更擔心自己的言論會對身邊的人形成冒犯。貝爾的調查發現,溫和派相對於普通社交媒體使用者,出於這種顧慮,更不會對與自己政治觀點不同的人發出回應。

電影【熱搜】(2023)劇照。
於是,社交媒體對話的吊詭與困難之處恰在於,極端是極端者的通行證,反省反而成為溫和派的「墓誌銘」。溫和派不斷反省,並力圖全面地呈現對現實的認知,卻內外受敵,同時遭遇來自自己內心和極端派的攻擊。溫和派的噤聲與極端觀點的盛行都在加劇,對話與溝通變得更為困難。正如【打破社交媒體棱鏡】一書的中文版序言所說,貝爾將改善網絡對話的希望寄於溫和派的反省與努力,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這是認知問題,
也是倫理問題
針對貝爾的主張,批評者認為他忽視了平台、政治應該在改善網絡對話的極化問題中的作為,實作人與人之間「明亮的對話」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其實貝爾也做過改善平台機制的努力,他和研究團隊設計了一個名為DiscussIt的實驗聊天平台,參與討論的人會在身份上被匿名化處理,同時,他們會被匹配到與自己觀點各不相同的使用者。真正的問題可能是,人們能否好好對話是一個社交媒體時代的顯著問題,而並不僅僅是一個社交媒體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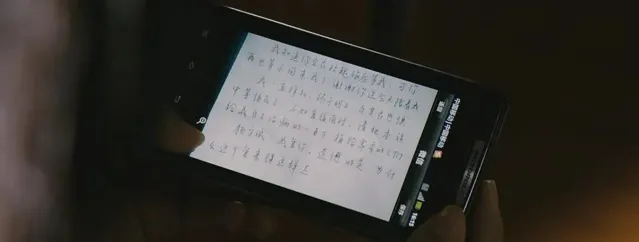
電影【搜尋】(2012)劇照。
美國學者莊拿芬·海特在【正義之心】中認為,我們在做出關於何為正義的判斷時,情感其實往往是先於理性的:當我們看到有人虐貓時,常常是身體反應先向我們推定了行為的不正義,然後關於不正義的邏輯推理才跟進。很多時候,我們在與他人對話和辯論時感到「我對你錯」,都不是基於理性理由,而是一些偏見和「捷思」。比如徐賁在【批判性思維的認知與倫理】一書中提到的「自欺」,自欺的人常常能比不自欺的人更容易達成自洽和快樂。而經濟學者泰勒·考恩則認為,人們在政治性自欺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價值觀和一種「附屬感」。這些都不是思考的結果,而和個人被自然賦予的那些特征:種族、成長區域、宗教信仰、階層高度相關。我們根據這些「棱鏡」過濾看到的觀點,以此對他人做出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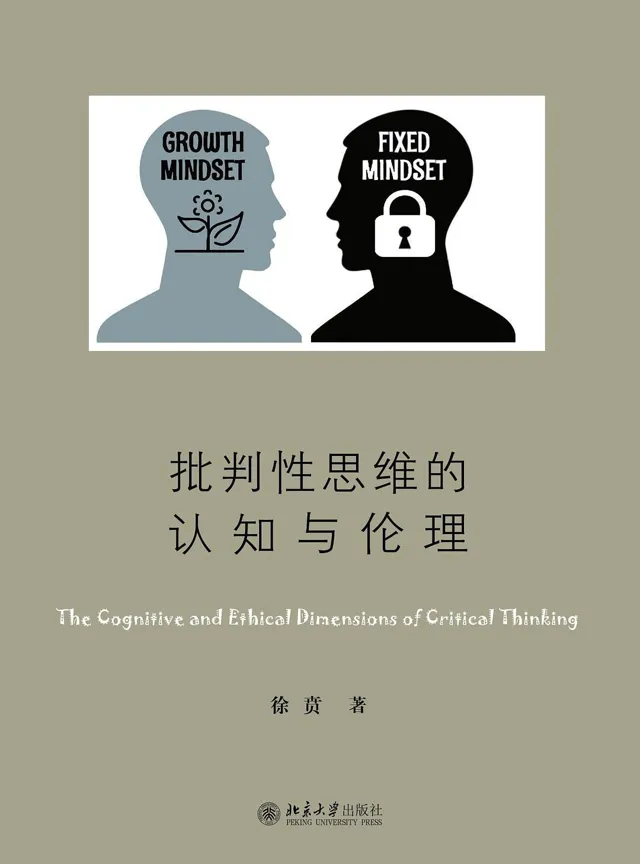
【批判性思維的認知與倫理】,徐賁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2月。
徐賁還指出,在公共辯論中,人們常常認識不到自己正被一些「捷思」所誤導。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李察·涅斯伯特(Richard Nisbett)和羅斯·李曾提出過一種「基本歸因錯誤」,即把某個人的行為、觀點歸因於他的個體原因,比歸因於環境影響要容易得多。這種「捷思」在網絡討論中常常發生,它使得人們誇大對話雙方的「本質性」差異,也很容易將事實問題的討論變成道德審判。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者約書亞·格林在【道德部落】中對這種討論道德化的傾向有更為深入的反思。他認為,人們在進行觀念交鋒時使用的話語本身會影響對話的走勢,如今,人們之所以會常常陷入大大小小分裂的「道德部落」中黨同伐異,很大程度上是大家經常將類似「權利」之類的詞語用作合理化自身觀念的擋箭牌。「權利」是一個從情感角度幾乎擁有天然正當性的詞語,但它又是抽象且容易將討論變得道德化,在網絡的語境下,人們常常從不深入地探討它在當下具體指的是什麽,就用自己是在聲張「一個群體的天賦權利」來阻斷自己被反駁的空間。「獵巫」「取消」這些詞匯同樣如此。

【道德部落】,[美] 約書亞·格林著,論璐璐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
格林建議,我們應該在觀點討論中盡可能謹慎地使用這些具有道德化意味的詞匯。海特也曾如此論述,在他看來,人們經常會用一套看似堅定不移的故事來論證己方立場的合理性,但這種立場的獲得很有可能是出於偶然。比如一位搖滾樂隊的吉他手選擇成為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可能僅僅是他才華橫溢卻屢屢因為不公的選拔被樂隊拒之門外,而一位堅定的動物保護主義者可能兒時親眼目睹自己的寵物被施以暴行。很多時候,選擇溫和,與一種道德化的表述保持距離,並不意味著放棄對錯判斷,或是對不公義、錯誤的觀點的縱容,而是對人性中的一些可能將我們帶入歧途的沖動保持警惕。在一個普遍極化的社交媒體環境中,為更有效的討論提供一定的緩沖。
格林認為,相對地,我們應該采用一種接近於功利主義後果論式的「深度實用主義」,更多地討論事件的細節,以及某個觀點實際帶來了何種後果,比如,在某個與你辯論的人表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時,追問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意味著什麽?正如貝爾此前的研究結論所示,人與人之間的共識可能遠遠多於差異。很多問題的分歧並非不同立場的差別,而是同一個立場的不同程度的差別。

紀錄片【虛擬革命】(The Virtual Revolution,2010)畫面。
在【批判性思維的認知與倫理】一書的結尾,對於公共討論的未來,徐賁提出了一個非常發人深省的觀點: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並不僅僅是解決認知問題,它本身也是倫理問題。換而言之,平台的治理、政府的幹預、對偏見與認知的澄清,一切有助於良善對話的條件都有賴於一個前提:我們是否是懷著對真誠對話的渴望而開啟對話的?很多時候,即便我們頭腦清明、知識豐富,也可能因為網絡流量的誘惑、彌漫於社會中的犬儒主義,或是純粹壓倒他人的欲望故意將對話引入歧途。正如貝爾在書中所說:當你打算在網絡上投入一場「戰鬥」之前,先問問自己真正的動機是什麽?這是一個你願意為之獻身的議題嗎?或者,你只是想透過巧妙地擊敗對手來為自己贏得一些什麽。
作者/劉亞光
編輯/西西
校對/劉軍
封面題圖素材為【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