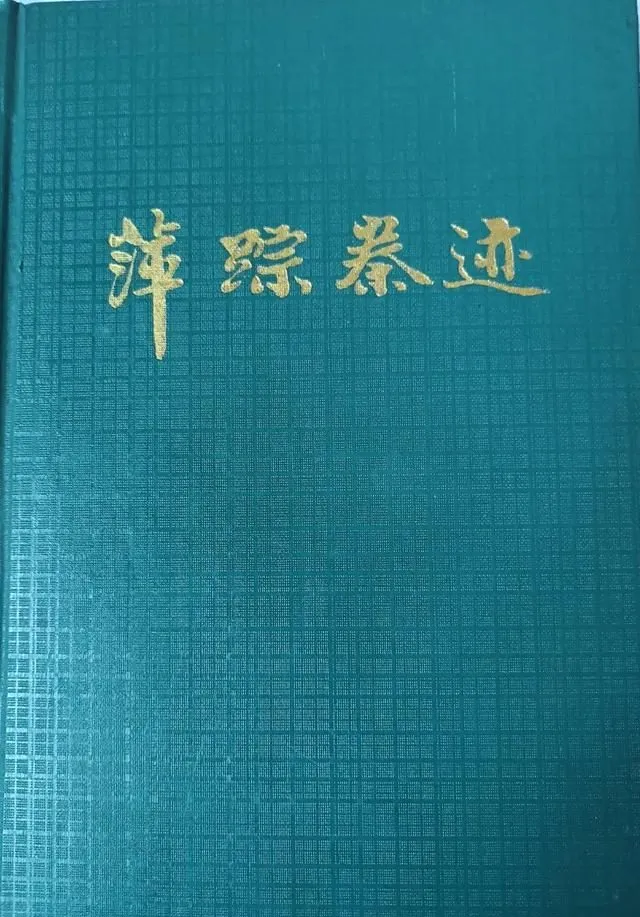泥沙混杂的社会熔炉
我所接触当年的白纸坊印刷局,是个有较长历史的老厂,性质也不同于一般的私营印刷企业,它好像是在受着当局财政官僚控制着的机构,早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
这些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我体会好像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会考虑工人的思想、生活以及什么生老病死的问题,是把工人看成机器转动中的一些部件,好用则用,不好用则扔掉;二是管理工人就是突出以摘去饭碗来控制,没有任何规劝和教育,够上「线」就开除。所以厂门的告示牌上,经常有开除工人的布告。我管它叫作「不教而诛」。
也是在日寇侵华初期,社会动荡大,厂内职工也动态多,经常有来有走,骑马找马。我在这个工厂生活了三年,所接触到的,像是个五花八门的小社会。人员的构成,好像比我以后工作的企业都要复杂。
我见到厂子里这些工人,年老的有六七十岁,年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这些人过去的职业和现在的兼职、副业,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出身成份,可以说是医卜星相,三教九流,贩夫走卒,车、船、店、脚、衙,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
他们也有业余文化生活和业余爱好。上品的是养花、养鸟、看书、下棋或武术锻炼和唱京剧等。属于下流的,那就是不属于文化生活的吃、喝、嫖、赌、抽(指吸毒)了。那时不像现在,能把「赌」也硬往「文化」里塞;本来是穷奢极欲地吃得脑满肠肥,硬讲这是属于「食文化」;本来是醉鬼酗酒,还厚着脸皮往「文化」上拉,管这个叫「酒文化的负效应」。那个时候的善良老百姓,虽然不懂这些弯弯绕,但是,正直人一样会以深恶痛绝的态度,对待这些丑恶现象。
当时的物价上涨,生活窘迫,使厂子里的工人不能不在业余时间干点副业。他们为了一家老小的糊口,都各自去找出路,比较多的是上夜班的下来,不能立刻休息,先去批发市场趸菜,再下街去卖;也有的沿街收买破烂,挑着大筐收来以后,再送卖给收购点(那个时候北平收旧货的,都手敲寸多直径大的小鼓,因此俗称「打鼓儿的");还有的是专门上日班,夜间出去「拉晚儿」(夜间拉人力车)。除此以外,还有根据自己条件兼干点小贩或壮工的。
当年我还见到过他们,给人加工过刨铅板丝,是把一种薄铅板(也可能是锌板),立着往下刨细丝,说是刨一斤给多少钱加工费。我在厂子附近的同事家里,看见过他们干这种活。开始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反正加工给钱,后来才慢慢知道了,据说那是填充炮弹用的。现在想,中国人给他们加工这个,用于去伤害中国人,这也太愚昧了。好像时间不久,这种加工活就没有人干了,是这些人觉悟起来了,还是其他原因,那就不明白了。
我在这个工厂的几年里,亲眼看到过,嗜于吃、喝、嫖、赌、抽、扎(扎吗啡)的人,虽他们各有不同的程度和表现,但行为都是可鄙的,结果都是可悲的,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其中尤其是吸毒的,后果立竿见影,先是因吸毒走险违法,继是被工厂开除,结局都是沦为饿殍,很快就会在社会上消失掉。
我在厂子里,当年看到过一个吸毒人的沦落经历,他是在裁切班的一个中年人(可能姓田,记不清了),那是一个做得出,说得响的壮汉,曾对我们这一堆小孩,说过吸毒的害处和可悲的下场,他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当时还真有点敬畏他。
时隔不久,好像我们在厂子里看不到他了。后来听人说他抽上白而儿了。当然,吸毒和开除,在当时是绝对联系着的「程序」,这个人自然会先在厂内消失掉。
几个月后的一个发工资的日子,我在黄昏时离厂回家,那次正巧是一个人走,没有搭个伴,抄近路斜穿于印刷局路东侧的菜园与坟地中间。没有注意时,由坟头后边跳出一个人来,吓了我一跳。他伸手要我给一点「帮助」,用力辨认,我才在这一具蓬头垢面和破衣烂衫的躯体上,看出这就是那个几个月前还曾相识的「故人」,实际形象已成活鬼。
当时,我没有敢多看他,也没有和他说话,只是忙着往他手里塞了几角钱,就匆匆地离开了这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一个人再走这一段路回家。实际上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恐怕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再从我的那一间单身宿舍的小天地看,跟我同住过一室的还有三个人。一个就是三十多岁,较为黄瘦的郑家瑞,他年纪比我们大,厂龄也比我们长,好像就当然地可以自居为一室之「长」,有些事得由他说了算。不知道他以前都干过什么工作,反正看着就让人觉得带点市井气,说话横眉立目,别人叫他的外号「碴儿郑」,指他为人好找碴儿。也听说他的前妻是上吊自杀的,没听说是什么原·因,我想总看他这种脸色,起码也会令人心不顺。
这屋里后来又住进的一个人,二十多岁,叫马瑞泉,是郑的亲成。据他自己说,原来干过冀东伪政权的保安队,也参加了张庆余领导的「通州事变」,后来被打散了才回的家。这个人很健壮,性粗野还有点「食亲财黑」,有些地方他是听郑的,但还不如郑的懂得「里外面儿」,因此,他们之间也有些矛盾。郑嗜嫖好赌,经常侈谈自矜他的那些「经验」,也在宿舍屋里招人「推牌九」赌过钱。遇到这事时,我看了生气,也只好躲出去,到别人的屋里去找小伙伴玩。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自己做得正,也讲礼貌。郑有点讲外场,还没有正面欺负过我。郑后来又结婚搬出宿舍以后,又补住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新伙伴,叫李树棠,他矮个子方脸庞,可能是京东一带的人,原来是个理发匠。人还算规矩老实,而他的处事谈吐,自然是另一路人物的习惯了。
在车间、在宿舍,耳熏目染的东西是形形色色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下流情调,淫歌、窑调,有过于如今的黄色歌曲;那时的下流语言之成套化、系列化、韵律化,较之现代小哥儿们创造的下流话,还要深刻和「艺术」得多。但这些究竟不是什么文化,在那个时代也是不齿于正经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