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指出,二十世纪文学作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结晶体,一种是火焰。这是两种归类事实和理念、风格和感情的范畴。卡尔维诺自称是代表创新的结晶派,他的小说风格追求形式创新,追求哲理性、图解性和制作性,强调精确和简洁。不过,尽管卡尔维诺属于后现代主义,加缪属于现代主义,结晶派的这些特征同样可以在加缪的小说中发现,尤其是他的【局外人】。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 1957 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代表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
撰文 | 景凯旋
他追求的不是活得最好,
而是活得最多
没有一部现代小说的文字比【局外人】更简洁的了,想想普鲁斯特繁复细腻的【追忆逝水年华】,想想穆齐尔未完成的【没有个性的人】,与他们相比,加缪的【局外人】就像是一颗精工打磨的结晶体,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小说第一部的开头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开头这段简洁文字表现出小说的冷漠风格。故事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自述展开。默尔索生活在阿尔及尔,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请假前往养老院,几年前他把母亲送往那里,近一年几乎没有来看过她。他不记得母亲的年龄,拒绝看母亲的遗体,在灵柩前抽烟。他似乎对母亲的去世毫不伤心,却很注意观察周围的人群,全书都是通过默尔索对外界的观察,来表现主人公的漠然。
守灵时,来了几个母亲生前的朋友,都是养老院的老人,默默地坐在灵柩旁边,默尔索只是感到困倦不堪。「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天一下子就黑了。」「从开着的门中,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盹。」第一句写女护士进来,接着就写天黑了,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第二句写房门开着,其实是在照应前段女护士进来后的情景,夜晚和鲜花的气味与打了个盹之间,也是句子间的非逻辑跳跃。萨特就曾敏锐地指出,这部小说的每句话都是一座岛屿,一个封闭的「现在」。
这种话语的缩减造成一种疏离的效应,主人公对外界的感受是零碎和隔膜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加缪绝不同于卡尔维诺,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主题已经变得比人物更重要(结晶派的特点) ,不过后者将文学视作接近事物无限多样性的方式,而前者则是将文学视作获取事物实质的方式。也就是说,【局外人】是结晶体和火焰的结合。从表面上看,【局外人】是一部关于罪与罚的故事,实际上却是一部探索荒谬的小说。
加缪在论及文学的性质时曾说过,作品是「在死亡那里获取自己最终的意义。」【局外人】恰恰是以母亲去世时始,以主人公被判死刑时终(符合结晶体的结构原理) 。默尔索就像是一个活在绝对自我中的人,他从母亲葬礼上回来,睡了一觉就去海里游泳,接着与女友玛丽去看了一部喜剧片,然后俩人回到住处做爱。接下来,默尔索自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周末在阳台上观看街道上往来的人群: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卖烟的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去拿了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来。很快,天阴了。我以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渐渐放晴了。不过,刚才飘过一片乌云,像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阴暗了。我待在那儿望天,望了好久。」
总之,母亲去世后的日子没有任何变化,他的生活一切照旧。玛丽想要跟他结婚,他觉得怎么都行,她问他爱不爱她,他认为这句话毫无意义。他说他大概不爱她,但这于结婚无关紧要。邻居莱蒙是个拉皮条的人,默尔索并不拒绝与他交往,还替他写情书,引诱他的阿拉伯女友来遭受羞辱。
默尔索能感觉到言语的无意义,却感觉不到行为的无意义,这让我们想到之前的法国作家塞利纳,主人公知道杀人阴谋后同样一声不吭。不同的是,塞利纳的主人公本身避免了成为杀人犯,而在加缪这里,这种无意义的行为最终衍生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默尔索和玛丽、莱蒙在海滩上玩耍,那个女人的兄弟向他们寻衅,仿佛灼热的阳光使默尔索感到眩晕,他在漠然状态中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荒谬就是这样产生的,正是无意义驱使他开的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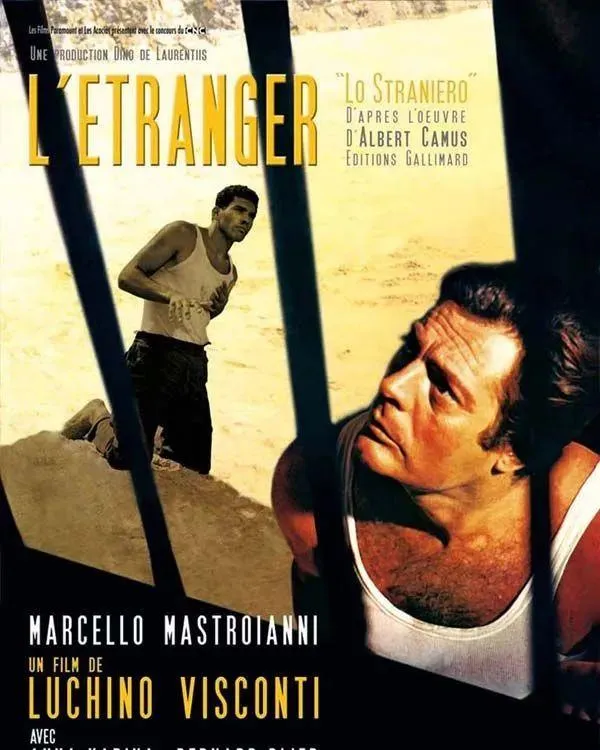
电影【局外人】(1967)海报。
虽然默尔索是叙事者,但由于作者将他放在一个被观察的位置,于是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主人公毫无道德感,麻木不仁,他仿佛只活在「现在」,活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当前化」中。这一点在默尔索跟预审推事的初次会面时体现得最为明显,分手时他想要跟推事握手,「幸亏我及时想起来我杀过一个人。」不过,如果我们认为默尔索是个阿Q式的人物,完全缺乏自我的意识,那就错了。用玛丽的话说,他是个「怪人」。主人公不是缺乏自我,而是无法超越自我,与外部世界建立起联系。
问题在于,对于默尔索来说,这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值不值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小说第二部中,默尔索面临杀人指控,但他从未感到自己有罪,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预审推事试图探讨他杀人的动机,揪住他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以证明他是天生的杀人犯。案件被引向道德审判,并得到众人的赞同。在法庭上,检察官义正辞严地指控道,默尔索「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随随便便地杀人!」
默尔索不明白,母亲的死与杀人有何关系。他跟所有人一样爱自己的母亲,只是不愿像所有人那样被既定的习俗束缚,当众表演很悲痛的样子。但是,事实确实摆在那里,所有证人的证词都对他不利,按照检察官的观点,默尔索没有人性,没有灵魂,他应当因为对母亲的去世表现冷漠而被判极刑,这样才会对社会有警示意义。
在最后时刻,默尔索一再拒绝了神甫主持的忏悔。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孤独的,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想到了死:「但是,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因为,「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主人公在省察自己的一生时,意识到生命的空泛和虚妄,他并不是个没有思想的人,相反,他在观察别人时比所有人都要思考得多,他追求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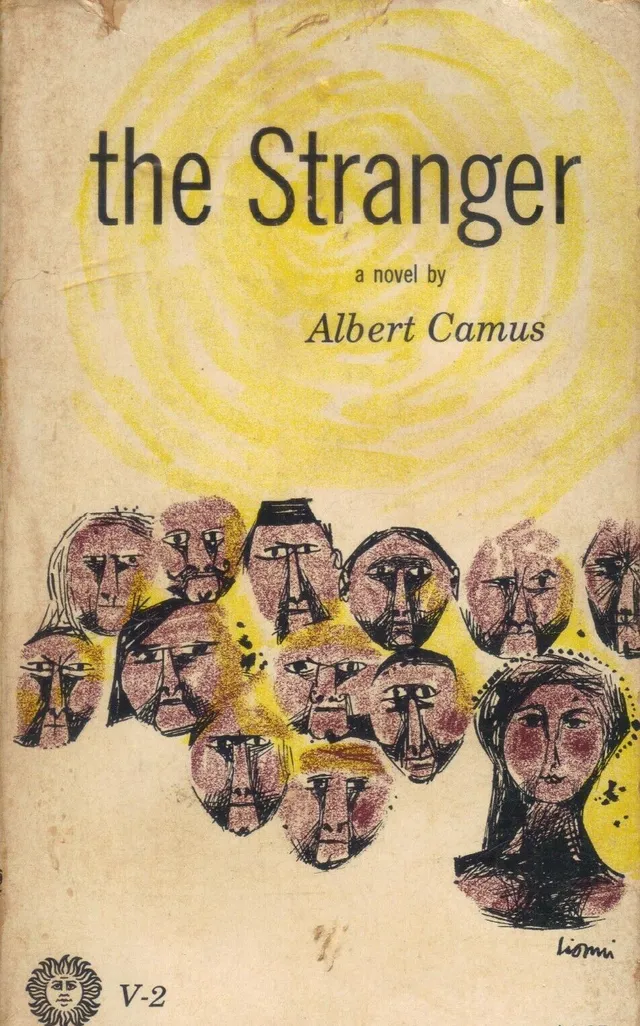
【局外人】外文版封面。
从对荒谬的反抗中获得自由
显然,按照社会的法律,主人公是有罪的,但默尔索绝不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为生活所迫的罪人,能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批判。如果加缪想引起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读者只能将作品看成具有更深的含义才行。
这更深的含义就是加缪的存在哲学。在他看来,人是被偶然掷入这个世界的,孤独感来自生存的荒谬,来自世界的无意义。加缪在其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里指出,人与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荒谬,意识到荒谬世界的人就是荒谬人。因此,默尔索感到自己对何为生命比神甫更有把握。苏姗·桑塔格曾评论道,加缪常常从虚无主义的前提出发,把他的读者带向人道主义的结论,而这结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其前提得出来。「这种从虚无主义深渊向外的非逻辑的一跃」,正是默尔索最后时刻的感受。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满天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音一直传到我的耳畔。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使我的两鬓感到清凉。这沉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静,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他的身上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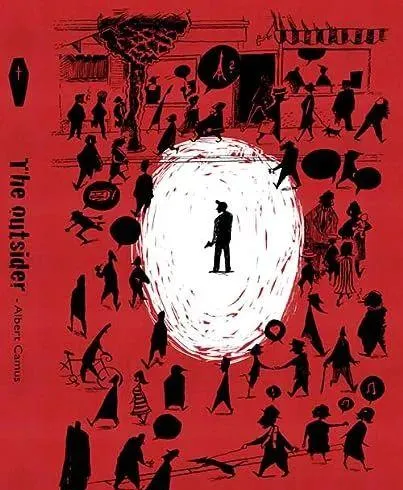
【局外人】外文版封面。
还是让我们回到前面的叙事,看看默尔索为何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吧。默尔索对养老院周围葱绿田野的喜欢,对大伙在海滩岩石上嬉戏的欣喜,对从阳台上望出去万千街景的观赏,以及从监狱窗口看到波涛起伏的大海所感到的幸福,在在表明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正因为如此,加缪才在美国版序言中写道,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加缪所说的「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默尔索拒绝与这个世界和解,选择独自面对死亡,按照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的阐述,荒谬的人只承认「自我决定的道德」。我觉得,这个「自我决定」就是默尔索身上对绝对的激情。世上大多数人都是与世浮沉,每日寄望于虚妄的明天,默尔索意识到这种荒谬,决心要反抗这种荒谬,这使得他在这个平庸的世界显得异常孤独。面对无意义的人生,主人公以荒谬为自由的根据,从对荒谬的反抗中获得自由,「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主人公这最后一句话的态度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镇静地走向巨石。

画作【西西弗】。
随着近代以降上帝的离场,十八世纪的人重新赞颂古希腊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欲图以这位古代英雄来取代上帝,拯救人类。于是我们看到,从近代小说诞生之日起,小说家们就加入了寻找意义的大军,歌德、司汤达、狄更斯、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这些伟大作家塑造了众多反叛的世俗英雄。但是,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意图掌控历史的这种普罗米修斯野心是现代极端思想的根源之一。他们用文学改变社会的理想最终落空了,二十世纪的文学于是产生了某种「反英雄」, 默尔索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投身反抗,但绝不指望反抗的结果,因为荒谬本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存在境况。加缪曾指出:「荒谬,其实就是指出理性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目睹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滥用,这使加缪得出自己的生存观:「荒谬在这一点上使我豁然开朗:不存在什么明天。从此,这就成为我的自由的深刻原因。」对加缪而言,生命的意义不在目的,而在过程,人的历史因而是一部反抗荒谬的历史,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意识到自由。
那些认为加缪揭示了存在本质的读者,对加缪充满了感激之情。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结晶体不是火焰,它不会灼伤人。就像苏姗·桑塔格所说,加缪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他的魅力不在于他的思想,而在于他表现出的道德之美,如果说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加缪唤起的则是爱。爱这个荒诞的世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景凯旋;编辑:张进;校对:陈荻雁。封面为摄影师Henri Prestes作品,有裁剪。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