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網路內容幾乎塑造了絕大多數當代年輕人對性的概念,在這樣一種社會文化下,性的含義到底是什麽?我們如何理解最新浮出水面的有關性權利的探討?尤其是這一討論還涉及影響人們的關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復雜問題——比如性權利、性騷擾、色情文化、校園師生戀情等,使得這一話題更具有很強的當下性與現實意義。
師生戀由於其「雙方同意」的外殼,一直處於校園性騷擾問題中的模糊地帶。師生間是否存在真正的浪漫愛情曾一度引發爭議。但近些年來,人們開始懷疑,在「教與學」這種存在明顯權力差異的關系中,名副其實的「同意」是否可能?另一方面,即便師生之間確實「彼此傾心」,這樣的關系又是否真的毫無問題?
在傳統的「師德師風」規訓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作為老師,究竟應當對學生展現出什麽樣的愛?當我們猶豫學生是否有自主的選擇意識時,往往容易忽略在心智尚未成熟階段,這種「愛的萌芽」鑲嵌在關系內部的不平等與外部作為制度存在的「強制異性戀」結構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性?我們應該如何談論性?怎樣才能讓性真正自由?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整理自【性權利:21世紀的女性主義】中的「教與學的倫理」。篇幅原因,本文為對該書的綜合整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雙方自願的師生間性關系
就沒有問題?
校園性騷擾政策擴大到涵蓋雙方同意的師生關系是婦女解放運動遺產的一部份。然而,這種擴大一開始,一些女權主義者就斥責它是對其原則的深刻背叛。她們認為,否認女學生能夠同意與其教授發生性關系,是將「不行也是行」的強奸犯邏輯倒置成了「行也是不行」的道德化邏輯。女大學生不是成年人嗎?她們沒有權利與自己喜歡的人發生性關系嗎?這樣的政策不是正中重新擡頭的宗教右派的下懷嗎?他們可太熱衷於控制女人的性生活了。
但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這些論點聲量漸弱,對師生間性關系的全面禁止幾乎沒有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反擊。女權主義者越發為被巨大的權力差別所影響的性關系當中的倫理問題而焦慮,這一結果是與此種焦慮並列的。當相對無權的一方同意與有權的一方發生性關系時,這是名副其實的同意嗎?
毫無疑問,有時女學生會同意她們實際上不想發生的性關系,因為她們害怕拒絕的後果——低分數、乏善可陳的推薦信、導師的無視。但仍有許多學生做此舉是出於真正的欲望。有一些教授的求愛與性邀請是非常受歡迎的。堅稱師生之間的權力差別使其不可能存在同意,要麽是把女學生看作孩子,本質上無法同意性行為,要麽是認為她們在教授的耀眼魅力下莫名失去了行為能力。而哪個教授真的那麽好?
但這不是說真心想發生的師生間性關系就沒有問題。
想象一下,一個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自己學生的熱切迷戀,帶她出去約會,與她發生性關系,把她變成女友,就如他此前對許許多多學生做過的那樣。學生同意了,且不是因為害怕。我們真的準備說這種行為毫無問題嗎?但是,如果有什麽問題,而問題又不是沒有同意,那麽問題是什麽?

【性權利:21世紀的女性主義】,[英]埃米婭·斯裏尼瓦桑 著,楊曉瓊 譯,雅眾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1月。
在其對學生性騷擾投訴的正式回應中,簡·蓋洛普訴諸佛洛伊德的移情(transference)概念,病人往往無意識地將與童年時期的重要人物(通常是父母的其中一方)相關的情感投射到分析者身上。在很多情況下,其結果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移情之愛」,孩子奉獻、迷戀和渴望取悅的目標從父母身上轉移到了分析師身上。蓋洛普說,移情「也是我們與真正發揮其影響力的老師的關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份」。換句話說,愛上老師,是教育進展順利的一個標誌。
或許是這樣。我們之中必定有許多人最終能成為教授,是因為有老師或不止一位老師——在高中、大學——激發了我們新的渴望和願望。而我們這些從事教學的人很可能在學生身上辨認出某種類似於移情的東西,不僅是那些被我們激發了相似渴望的學生,還有那些在我們教學權威的行使中感受到對他們獨立性的致命攻擊,從而激發出過分的敵意而非(過分的)崇拜的學生。即便如此,蓋洛普也忽視了佛洛伊德的堅持:分析師是「絕對禁止」與他們的分析者發生戀愛關系或性關系的。

【死亡詩社】電影劇照。
在佛洛伊德看來,如一位讀者所說:「分析師要回應,但不以同樣的方式回應。」也就是說,分析師不能對分析者做出愛意或敵意的回應,也不能把移情作為自己情感或身體滿足的工具。相反,佛洛伊德說,分析師必須把移情關系作為治療過程中的一項工具。他說,技巧熟練的分析師會透過讓被分析者註意到移情的作用來達成這一目的,會「說服」她——我應該讓這個表述回到模糊的狀態——她的移情感受不過是一種被壓抑的情感的投射。
「這樣一來,」佛洛伊德說,「移情就從最強有力的抵抗武器變成了分析治療的最佳工具……這是分析技術中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部份。」
對教授來說,對學生的移情之愛做出回應,又不以同樣的方式做出回應,而是把它為教學過程所用,可以怎麽做呢?大概需要教授「說服」學生,她對於他的欲望是一種投射:她所愛慕的其實完全不是這位教授,而是他所代表的東西。把佛洛伊德的話換成柏拉圖的話來說就是,老師必須將學生對他的情欲能量引到正確的物件上:知識、真理、理智。
作為老師,應當向學生
展現怎樣的「愛」?
此處的差別,學生對教授的迷戀與任何人對任何他人的迷戀之間的差別只是一個程度問題,而非型別問題。師生戀的問題不在於他們之間是不是真正的浪漫愛情。許多教授都跟從前的學生結婚了(這一事實經常被師生戀的辯護者參照,仿佛我們的生活是一場莎士比亞喜劇, 所有的結局都是終成眷屬)。但是,正如佛洛伊德向我們表明的,問題不在於在教與學的語境之下,「真正」的浪漫愛是否可能,而是真正的教學是否可能。
或者,換種說法,問題在於老師作為老師,應當對學生展現出什麽樣的愛?在1999年的文章【擁抱自由:精神與解放】當中,貝爾·虎克斯要求老師自問:「我怎樣才能愛這些陌生人,這些我在教室中看到的他人?」虎克斯所指的並非戀人之間排他的、要求忠誠的、兩人之間的愛,而是某種更有距離、更節制、更對他人與世界敞開的愛。這並不一定是一種低一等的愛。
當我們談論師生之間權力差別的時候,不單單是說老師對學生生活的發展更有影響力,學生對老師命運的影響則相對較小。事實上,如果以此方式來呈現,將招致這樣的反駁:女學生其實掌握著所有權力,因為她們能讓男教授被開除。相反,師生戀的本質特征是深刻的認知上的不對等:老師了解並知道如何做某些事情,學生想要了解並知道如何做這些事情。他們的關系中隱含的承諾是,這種不對等將得到縮減:老師把自己的一些權力賦予學生,幫助她至少在某一方面變得更像他。當老師抓住學生對認知權力的渴望,將其變調為性的渴望,允許自身成為——或者更差勁,把自己塑造成——學生欲望的物件,他作為老師,就辜負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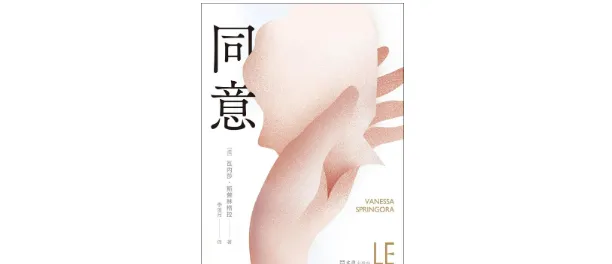
延伸閱讀:【同意】,[法] 瓦內莎·斯普林格拉 著,李溪月 譯,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2023年2月。
【被指控性騷擾的女權主義者】出版後,南加州大學英語教授詹姆士·金凱德(James Kincaid)在【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雜誌的一次討論中為蓋洛普的性騷擾指控辯護——在他看來,這一指控太無「趣」了。金凱德以抄錄他在上學期收到的一封學生來信開頭:
親愛的金凱德教授:
我從不做這樣的事,但室友一直告訴我應該這樣做,她說,如果你想的話,就去告訴他。所以我現在就來告訴你了。我真的很喜歡你的課以及你解釋事情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我讀過這些詩,但我看不出它們有什麽意義,直到你談論它們,它們才顯出意義。這是因為你說話的方式與我在英語系見過的其他老師都不一樣,他們可能比你懂得更多,卻無法表達出來,讓人理解,如果你明白我是什麽意思的話。但是,當你說浪漫主義詩人書寫情感,而不像17世紀的詩人(如蒲柏)那樣不寫情感,我立刻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自己也有很多情感,雖然我算不上是一個詩人,哈哈。但無論如何,我只想說謝謝,希望你繼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金凱德把這張便條解讀為調情,一種邀請,一種誘惑:
那張沒有簽名、發自內心的便條,表達了真實的渴望……我的仰慕者希望我繼續,因為他或她很喜歡,他或她給我寫這封信,也希望我喜歡。我會喜歡,他或她也會喜歡,我們會一起繼續下去,因為喜歡和被喜歡以及不停地保持被人喜歡,對我們雙方來說都很有趣。沒有人觸及終點線;沒有人被賦予權力,也沒有人成為受害者。如果我敏銳的學生和我逾越寫信,把這一切發展成實際的關系,這不是因為我有東西要給予,他或她有東西要索取,或者反過來,而是因為我們喜歡並想要繼續。身體的關系不是更進一步,只是不同維度。
金凱德的專業是解釋以及教他人解釋,假使如他所說,這不是一封來自年輕女學生的「發自內心的」信,那麽他在這裏幹的事情將是對某一類「變態」心理分析闡釋的諷刺。(金凱德堅持認為這個學生的性別是模糊的——「他或她」——但我們知道這是一名年輕女性,即便無法從信的語氣判斷,也能從作者宿舍室友的性別來判斷。金凱德表現得好像這封信以及他的回應與性別無關,是什麽意圖呢?)

【裂縫】電影劇照。
事實上,金凱德對這封信的解讀是一種辜負,是對一種甜美、真摯的情感表達的色情化。這個學生第一次明白了詩歌的意義,她對這個教授肅然起敬,在她所有的教授中,只有這個教授有能力向她展示詩歌的意義。金凱德忽略了這一切,而是把註意力集中在最後一句話上,「希望你繼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把它變成了一個粗俗的含有性意味的雙關。他在學生眼裏很厲害,而她樂在其中,希望繼續下去,別停下,就因為這很有趣。
但他的學生不是這麽說的。她希望他「繼續」,也就是繼續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因為這讓她樂在其中,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且因為這幫助她理解了詩歌的意義:「我的意思是,我讀過這些詩,但我看不出它們有什麽意義,直到你談論它們,它們才顯出意義。」她希望自己擁有理解詩歌的能力,而不僅是看他運用這種能力的樂趣。金凱德堅持他學生的渴望當中存在意淫的部份,正是這種堅持讓他說出那種想象的未來:他和他的學生「逾越寫信,把這一切發展成實際的關系」,「沒有人被賦予權力,也沒有人成為受害者」。
師生戀中的權力差別
作為【愛戀兒童:色情的兒童與維多利亞文化】的作者,金凱德和其學生之間沒有權力上的差別嗎?我想暫且放下(無趣的)制度上的權力問題不談:誰給誰打分,誰給誰寫推薦信,等等。這裏還存在其他的權力差別。
第一是認知上的權力。金凱德知道如何以一種讓閱讀有意義的方式閱讀;學生缺乏這種能力(power), 但希望擁有這種能力。金凱德對這封信的解讀特別令人不安的部份原因是,這個學生在智識上並不成熟。金凱德說她「敏銳」,有一種操縱感,而且很殘忍,給了她一個她想要的東西的幻影——老師本人的精熟技能。事實上,金凱德僅僅是復制了這封信,大概沒有經過她的同意,因為他確信她不是那種會讀【批評探索】的人。但如果她真的讀了這封信呢?看到自己年輕時的誠摯懇切被當作性戰利品,她會作何感想?
第二,金凱德不僅有解釋詩歌的權力,而且有解釋這個學生本人的權力。這是一種形而上的權力:也就是說,這種權力不僅能揭示真相,而且能制造真相。他告訴我們她的信中隱含著性意味,自然應當以性來滿足——而性不過是「把這一切發展成實際的關系」。這個學生相信 他有揭示紙上所寫之事的真相的能力,如果金凱德把他的這種解讀拿給學生本人看會怎麽樣?金凱德是否有權力制造這樣一種真相,即她的信在某種意義上始終包含著性意味?

【男人四十】電影劇照。
金凱德可能會反駁說,她的信就是帶有性意味的,盡管是隱含的。不是說信裏沒有任何欲望的表達。它的開頭就像一封告白信:「我從不做這樣的事……」這名學生說她也有「很多情感」,隨即又自嘲(「哈哈」)。金凱德是特別的,與「其他老師都不一樣」。他暗示,如果他想,他可以與這個學生發生關系——不需要任何脅迫、威脅或提出交換條件,這或許沒錯。或許他無須做更多的事,只要給她讀一讀華茲華斯,誇她「敏銳」,就能把她帶進臥室。那又怎麽樣?我們真的相信金凱德不是故意性化這種交往,面對學生的意願,他只是被動和順從而已嗎?
無論這個學生的渴望始於何處——我是想變得像他,還是想擁有他?——對老師來說,順勢而為,將其引向第二個方向,都太容易了。同樣地,當學生(錯誤地)認為,跟老師睡覺是一種變得像他的手段,或一種她已經跟他一樣了的標誌(他渴望我,那我肯定很有才華)。即使學生的渴望很明顯是想成為像老師一樣的人,老師也不難說服學生,她其實渴望的是他,或者和他睡覺是一種變得像他的方式。(還有比親身體驗更好的理解浪漫主義詩人「情感」的方式嗎?)

【死亡詩社】電影劇照。
無論學生的想法如何,金凱德作為一名教師,重點都應該是將學生的渴望從自己身上引開,並將其引向正確的物件:她的認知賦權。如果這已經是這名學生想要的,那麽金凱德要做的就是保持克制,不要把她真誠地表達出來的學習渴望性化。如果這名學生對於自己的渴望感到矛盾或困惑,金凱德則必須再進一步,劃定邊界,把學生的渴望引向正確的方向。佛洛伊德認為,在精神分析中,這一點應當做得明確幹脆,告訴病人,她體驗到的是一種移情。在教學語境下,采取這一方法可能非常尷尬。但也有一些更微妙的轉移學生能量的辦法,悄然後退,把對自己的註意力引向一個觀念、一篇文本、一種觀看方式。而金凱德甚至都沒有嘗試去這樣做,這使他未能成為他的學生所稱贊的:一個好老師。
老師應當抵制誘惑,不該允許自己成為或把自己塑造成學生欲望的容器。不是說教學可以或應當完全免於自戀的滿足,但享受你所點燃的學生的渴望(即便你已經將其從自己身上引開),和把自己變成渴望的物件,兩者之間還是有差別的。這種自戀是良好教學之敵。
從師生戀看
「強制異性戀」文化
前面我問過,金凱德談及學生時仿佛她可能是任何性別,這是出於什麽意圖?他不想面對的是什麽?最明顯的,也就是他實際描述出來的情況——年長的男教授,年輕的女學生——是最常見的師生戀形式。金凱德不想讓我們看到他如此老套。他大概也不想讓我們去思考,或者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支撐這種老套關系的性別動力學。我的意思不僅是男孩和男人所經歷的社會化使他們自認支配性感,而女孩和女人所經歷的社會化使她們自認從內容感;或者一些男教授混合了應得的性權利與知識分子的自戀,把睡女學生視作遲來的獎賞,在此之前,因為青少年時肌肉或酷比好腦子更受贊賞,他們可能經歷了一整個痛苦的青少年時期;還有最重要的,女性所經歷的社會化使她們以特定的方式解釋自己對所仰慕的男人的情感。
艾德萊恩娜·裏奇將「強制異性戀」制度描述為一種政治結構,它強迫所有的女性,無論性向如何,都要以同父權制相符的方式調整自己與其他女性的關系。它的一種運作方式是默示女性,她們應當如何看待自己欣賞的女人,或者解釋她們對其的感受。合適的方式是嫉妒,而非欣賞。你一定是想成為像她一樣的人,絕不可能是你想擁有她。但如果物件是對她們具有強烈吸重力的男人時,情況則相反:你一定是想要擁有他,不可能是想成為像他一樣的人。

【男人四十】電影劇照。
瑞吉娜·巴雷卡(Regina Barreca)在談到那些最終當了教授的女性時問道:「我們每一個人,是在哪一個時刻意識到,我們是想成為老師,而不是跟老師睡覺?」巴雷卡認為,大多數女性預設將(男)老師在她身上激發出的渴望解釋為對老師的渴望:如果她自己想成為老師,這便是她必須克服的一種解釋。與此同時,男學生與其男教授的關系就像他們所經歷的社會化一樣:想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男女在把老師視為模仿物件或吸引物件的可能性的差異,並不是某種自然的、原始的天性差異所帶來的影響。它是性別化的社會化的結果。
需要明確的是:女教授和她的男學生睡覺,或者女教授和女學生睡覺,或者男教授和男學生睡覺,也是同等的教育的失敗。但是,對雙方同意的師生性關系現象進行倫理上的評估,如果沒有註意到其典型情況是男教授與女學生的性關系,就會錯失某些重點。

【醜聞筆記】電影劇照。
在此類情況下,教授的失敗——也就是大多數師生雙方同意的性關系的實際案例——不僅僅是未能將學生的情愛能量導向正確的物件。在父權制下,女性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被社會化,也就是說,以一種有利於父權制的方式經歷社會化,這是一種對「拒絕利用」這一事實的失敗。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它使教育的好處平等分配給男性和女性這件事變得徹底不可能,從而再生產它賴以存在的動力模式。
性騷擾監管去向何方?
雖然雙方同意的師生性關系並不符合性騷擾的定義,但它們仍可算作性別歧視。因為可以預見,這種關系對女性的教育常常造成損害,且是非常嚴重的損害。而且這的確是基於性別的。根據傳統的對性別歧視的法律理解,「基於性別」的歧視包括對女性和男性區別對待。顯然,只與女學生發生性關系的男教授對待女學生和男學生是不同的。只與男學生發生性關系的男教授,或只與男學生發生性關系的女教授,也是如此。雙性戀給這種對性別歧視的理解帶來了一個問題。這是需要對「基於性別的歧視」提出另一種理解的一個原因。
對凱瑟琳·麥金農、林·法利 (Lin Farley)和其他性騷擾理論的女權主義先驅來說,性別歧視的本質不在於有差別的對待方式,而在於其所采取的對待方式復制了不平等。以對女秘書下手的老板來說,問題不在於老板沒有同時對男下屬下手,而在於他的性挑逗是她不想要的,如麥金農所說,「表達並加強了女性相對男性的社會不平等」。

延伸閱讀:【言詞而已】,[美]凱瑟琳·麥金農 著,王笑紅 譯,三輝圖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把師生性關系表達了什麽的問題先放一邊,要說明這制造了什麽是很容易的。此類關系即便沒有普遍地讓女性的教育脫軌,從而對她們造成傷害,但也是常常如此。那些不再去上課,確信自己不適合學術生活,從大學或研究生院輟學的女性,顯然就是這樣。但這也適用於那些雖然選擇留下,但往往低估自己智識程度的女性,當其他男教授對她們的勞動成果表現出興趣,她們就會產生懷疑,並擔心如果她們成功了,她們的成功會被歸功於某個人或某些其他東西。這些關系有時(通常)是當事人想要的。但因為如此,其中的歧視性就減少了嗎?
第九條(指【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該立法旨在消除教育領域中的性別歧視,確保男女學生在教育和體育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和隨之產生的性騷擾政策是監管工具,至少在官方看來,是為了使大學校園對待女性更加平等、公平胡公正。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借由讓校園在其他方面更不公平胡公正來達成的——許多女權主義者不願意承認這一事實。有時這種不公正的受害者是女性。1984年,第一批針對雙方同意關系的政策出現在美國校園的第二年,法院維持了對路易士安那州立大學研究生凱瑞斯汀·納拉貢 (Kristine Naragon)的處罰,因為她與一名非她所教的大一女生發生了戀愛關系。當時,路易士安那州立大學並未正式禁止這種關系,但在學生家長不斷投訴女同性戀關系後,納拉貢受到了處罰。而同系的一位男教授與一個他負責作業評分的女學生有染,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賢妻】電影劇照。
所以,我們必須追問:在法律上認定師生性關系為性別歧視——因此違反了第九條——能夠讓校園對所有女性、酷兒、移民、工作不穩定的人和有色人種更公平嗎?還是會導致正當法律程式的進一步失效?——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而由於它格外多地針對那些已經處在邊緣的人,因此更加不公平。它是否會無意中加強那些熱衷於以保護女性為幌子控制女性的文化保守派力量? 它是否會被用作壓制學術自由的手段?它是否會被當作一種最終歸謬法——盡管錯得離譜——如果需要的話,校園性騷擾政策就是表明女權主義者已經徹底失心瘋的 明確證據?
性騷擾法律的歷史是一個呼叫法律為性別正義服務的故事。但這段歷史也指出了法律的限制性。這些限制性究竟在哪裏?在這些手伸不到的地方,法律必須停止嘗試引導文化,而要殷切地等候文化——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