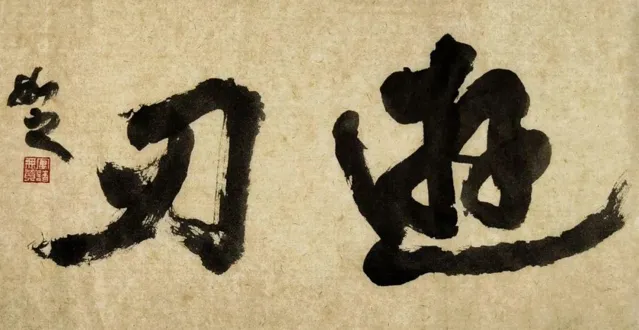
收到【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三十三輯,見刊拙文「間性與整全:【莊子】現象學解讀的一個嘗試」,主要談【養生主】庖丁解牛的遊刃之道,兼及【逍遙遊】的鯤鵬之化、【齊物論】的莊周夢蝶、【人間世】的孔顏心齋、【天地】的黃帝玄珠等等,發此分享,請朋友們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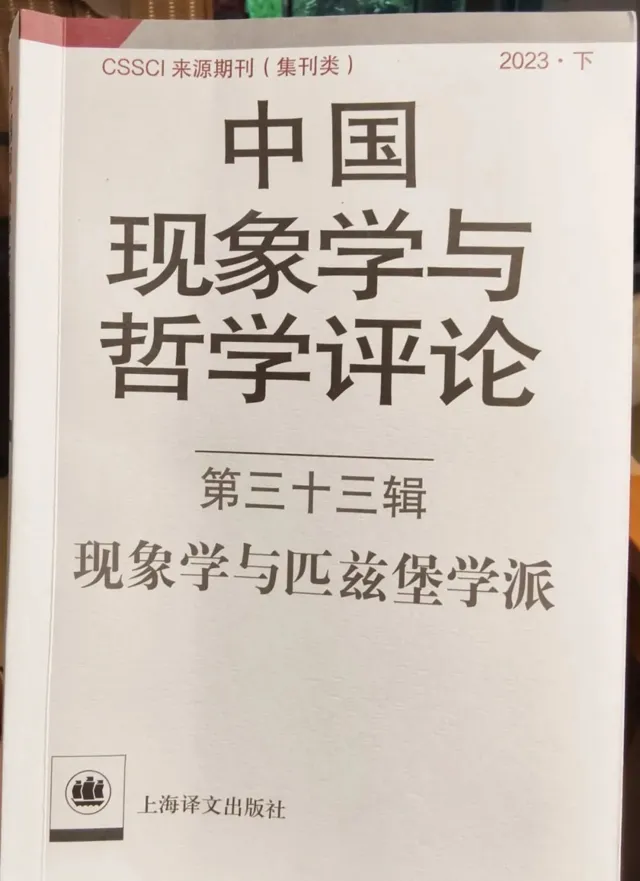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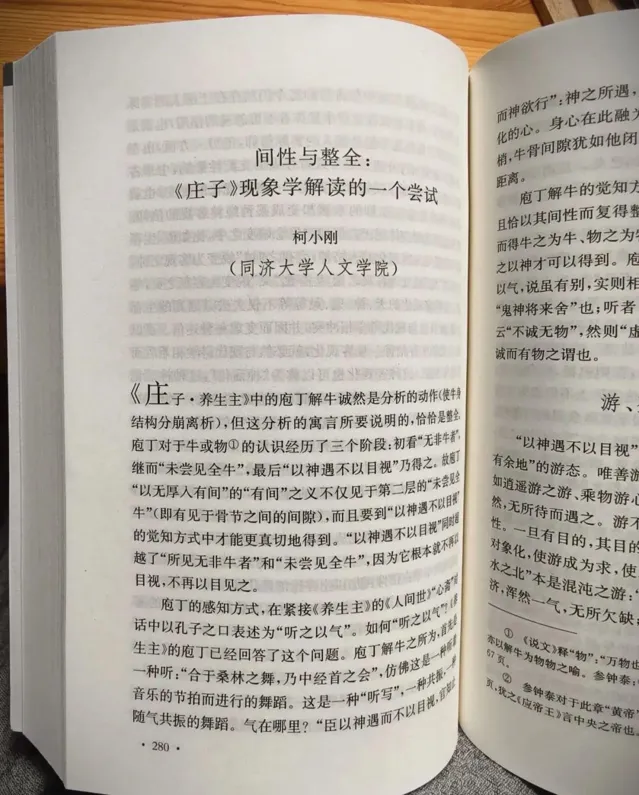
間性與整全:
【莊子】現象學解讀的一個嘗試
柯小剛(無竟寓)
【莊子·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誠然是分析的動作 (使牛身結構分崩離析) ,但這分析的寓言所要說明的,恰恰是整全。庖丁對於牛或物 [ 【說文】釋「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鐘泰亦以解牛為物物之喻。參鐘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頁。] 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初看「無非牛者」,繼而「未嘗見全牛」,最後「以神遇不以目視」乃得之。故庖丁「以無厚入有間」的「有間」之義不僅見於第二層的「未嘗見全牛」 (即有見於骨節之間的間隙) ,而且要到「以神遇不以目視」的覺知方式中才能更真切地得到。「以神遇不以目視」同時超越了「所見無非牛者」和「未嘗見全牛」,因為它根本就不再以目視,不再以目見之。
庖丁的感知方式,在緊接【養生主】的【人間世】「心齋」對話中以孔子之口表述為「聽之以氣」。如何聽之以氣?【養生主】的庖丁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庖丁解牛之所為,首先是一種聽:「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仿佛這是一種聽著音樂的節拍而進行的舞蹈。這是一種「聽寫」,一種共振,一種隨氣共振的舞蹈。氣在哪裏?「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神之所遇,觸處皆氣。這個氣是心氣,這個心是氣化的心。身心在此融為一體,猶如庖丁的刀就是他的神經末梢,牛骨間隙猶如他閉著眼睛所感覺到的左手與右手之間的距離。
庖丁解牛的覺知方式是「以無厚入有間」的間性覺知,而且恰以其間性而復得整全,以及超越「未嘗見全牛」的分析性而得牛之為牛、物之為物的本質。這個整全只有聽之以氣、遇之以神才可以得到。庖丁解牛的遇之以神與孔顏心齋的聽之以氣,說雖有別,實則相通。神者,氣也,氣之「徇耳目內通」而「鬼神將來舍」也;聽者,遇也,「虛以待物」之應物也。【中庸】雲「不誠無物」,然則「虛以待物」之心齋,「以神遇」之解牛,皆誠而有物之謂也。
遊、整全與音樂性
「以神遇不以目視」的間性覺知,帶來「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的遊態。唯善遊者能遇,唯善遇者能遊。遊刃之遊正如逍遙遊之遊、乘物遊心之遊,須在有意無意之間,不期然而然,無所待而遇之。遊不是捕獵,是遇,沒有那麽強烈的目的性。一旦有目的,其目的性就會改變全部活動的性質,使活動物件化,使遊成為求,使遇成為取。如【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本是混沌之遊:「赤」之為離、「水」「北」之為坎,本來相濟,渾然一氣,無所欠缺; [ 參鐘泰對於此章「黃帝」「赤水之北」和「昆侖」的解釋:「‘黃’,中央之色頁,猶之【應帝王】言中央之帝也。‘昆侖’猶混淪,混淪猶渾沌也。‘赤’,離火之色。‘水’,坎也。水而曰赤,則坎離合也。坎離合,是以有‘昆侖之丘’焉。」見鐘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鐘泰卓見,看到了「赤水之北」與「昆侖」同為混沌之義,可惜未能註意「遊於赤水之北」之「遊」與「登於昆侖之丘」的「登」在生命狀態上的區別。混沌雖一,而遊則有之,登則失之。鐘泰以昆侖為混淪、渾沌,說本方以智,見方以智【藥地炮莊】,華夏出版社,2016年,頁236。] 而一當「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則以視覺為中心而物件化其目的,背坎向離 (離卦象南、象視覺) ,於是「遺其玄珠」。遊則水火坎離一氣,玄珠自在昆侖 (昆侖即渾淪) ;登則判分南北陰陽 (如杜甫【望嶽】詩雲「陰陽割昏曉」) ,混沌降而為昆侖,不過足下一山而已矣。且南望之,是背坎向離之象也,故「遺其玄珠」 (反之則將遺其明珠,珠本渾淪之象而妄分明玄,亦坎離判分之效也) 。
玄珠坎象,外陰內陽 (「坎中滿」) ,非以目視可見而以神遇可觸者也。離則反是,外陽內陰 (「離中虛」) ,火耀於外,可見而不可觸者也。故黃帝「使離朱索之而不得」者,以火濟火,愈發強化其視覺中心而遺其觸覺,豈可探珠而得之?「使喫詬索之而不得」者,以名言之物件化機制, [ 成玄英疏以「喫詬」為「言辯」(【南華真經註疏】上冊第237頁),王夫之解「喫詬」為「文言」(【船山全書】,嶽麓書社,2011年,第13冊第221頁)。] 益失其混沌也。其實,玄珠之得,在其不得而得,在遊而不知其得。遊而不知其得,則本亦無所謂失與不失。失與得相待,得則俱得,失則俱失。所以,一當黃帝自覺「遺其玄珠」之時,他實際上不但遺失了玄珠,而且實際上也失去了在「失」的前提下重新獲得的可能性。所謂「使象罔乃得之」者,「象則非無,罔則非有」 [ 方以智【藥地炮莊】,第277頁,此說實出自呂惠卿,見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不使之使,無得之得也。罔者,玄之不可見也;象者,珠之本無可失也。故象罔之義,實即玄珠本身。「使象罔乃得之」者,非外有所得也,乃自復其初之謂也。
珠是整全的象征,實際上就是混沌之遊的整全性。黃帝所失者,實際並非某個可得可失的東西,而是遊本身,或其自身生命狀態的混沌性、整全性。韓詩及魯詩說【漢廣】以漢之遊女遺鄭交甫佩珠,而交甫失之,其義亦可與此相發明。 [ 參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上冊,第51-53頁。] 遊則有珠,求則失之,因為遊即是生命的渾淪狀態,而追求與占有則失其渾淪。【韓詩外傳】說【漢廣】以孔子對話佩璜處子,可能也有以璜為誡的寓意 (半壁曰璜,渾淪之缺也)。[ 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2頁。] 只要仍然處在物件化的「失」之狀態中,「得」就永遠不再可能。如果不明白原先的有珠狀態並不是與「失」相對而言的物件化之「得」,那麽求珠之使只會南轅北轍,愈求愈遠。象罔之所以得之者,如方以智所論,在象罔之為義,「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乃有無之間者也,遊乎非物件化之域者也,故唯象罔能復珠之渾淪。故象罔之得,實非有所得,而是復歸自性之天真無缺而已。遊而有之,遊而遇之,非求而得之也。此義正同庖丁「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也。神遇者,神遊也;目視者,目求之也。象罔之得珠,象罔之解牛也;庖丁之遊刃,庖丁之得珠也。
由是觀之,「聽之以氣」想說的也許就是「聽之以遊」。聽是聽覺,也是聽任。氣是所遊,也是所以遊。【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氣之遊也。【大宗師】「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氣之所以遊也。【在宥】「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雲將,氣之遊也;鴻蒙,氣之所以遊也。鴻蒙,渾沌也,元氣也,氣母也,黃帝之遊於赤水之北而玄珠未失者也(未失則亦無所謂有得);雲將問鴻蒙而復得其所以遊之本,猶黃帝使象罔而復得其玄珠也。庖丁之解牛,亦以「遊刃」之「遊」得之。庖丁解牛是使物解體而後得其整全 (牛喻物也) ,亦猶黃帝之遺其玄珠而使象罔得之,或鴻蒙答雲將之「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而後遊之。失者,整全之失也,解者,整全之解也,而皆以遊復之。解牛完成之時,即牛解體無存之際,而庖丁以此得刀之保全,「善刀而藏之」。解牛之時,刃遊走於牛骨之間,人遊舞於桑林之中 (「合於桑林之舞」) 。所謂解牛,實不見其解也,唯見其遊也,見其舞也。遊舞以解牛,是解物以合物,是解小體而化入大體。小體者,牛也,刀也,物也;大體者,遊也,氣也,道也。「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庖丁之誌在遊在化,在聽之以氣也。在此大化流行的桑林之舞中,所有事物,牛、刀、人、物都被帶上一條道路,一條健動不息的道路,一條載歌載舞的物化之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子罕】) 。
與黃帝使人尋珠相比,庖丁解牛不是要去獲得什麽,而恰恰是要去分解一件事物;顏回請赴衛國之亂也不是要去求取什麽,而是要去分憂解難。在「分解」這一點上,庖丁解牛和顏回赴衛的寓言有著共同的出發點。庖丁解牛的結果是透過分解事物的行動而達到一個更大的整體,孔顏心齋的結果也是透過自我身心剖析的工夫而達道。兩個故事都是透過破解小體以重建大體的寓言。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告子上】) ,其義可與相通也。從其大體則「浮遊乎萬物之祖」 (【莊子·山木】) ,「上下與天地同流」 (【孟子·盡心上】) ,本自固有而自覺其性,無得無失於萬物之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已。故【逍遙遊】之斥鴳、蜩與學鳩雖能飛而不能遊者,以其斤斤於能飛之得也。庖丁「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者,非有所得也,不失而已矣。故庖丁之遊刃舞桑,猶黃帝之遊乎赤水之北而未失其珠也;孔子教顏回之心齋聽氣,猶象罔之復性而復得其珠也。黃帝之珠,孔子之氣,庖丁之牛,三者之要,皆在遊以全性也。遊之關鍵在逍遙 (或作「消搖」) 。解牛是消,消之即解之。遙是心齋,任物之悠然去遠即遙。逍遙之域,北冥南海之間也,牛骨之間也,人間世之間也。唯遊有間,唯間能遊。唯逍之遙之能開啟空間,唯開啟空間而後能遊。所以,無論鯤鵬之變,還是「以無厚入有間」的庖丁解牛,本質上都是一種「心齋」或心的工夫實踐。
實際上,在庖丁解牛寓言裏,骨節之間的間隙總在那裏,並不會發生多大變化;刃之厚薄,即使反復磨刀,也不可能「無厚」到完全沒有厚度。所以,真正能用功的地方,只能是心,或者說是心的無化,正如【人間世】中的孔子對顏回所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或許只有等到【人間世】的「間」,【養生主】的「間」才得到完全的解說;只有等到孔子對顏回說的「心」與「氣」,庖丁解牛的「無厚」與「有間」之義才開始了然。從【人間世】的「氣」來看,【養生主】的「無厚」所說的也許是刃的間化、虛化、氣化。在【人間世】的孔顏對話中,待物者是做心齋工夫的人,所待之物是動亂中的衛國;在【養生主】的庖丁解牛寓言中,待物者是刀,所待之物是牛。衛國總在那裏,要改變的是顏回自己;牛骨之間總在那裏,要改變是是庖丁自身。「以無厚入有間」並不只是在物理空間的意義上盡量減少刀刃的厚度、增加骨節的縫隙,而是要透過「官知止」的時間性躊躇讓出骨節空間的「有間」,透過「神欲行」的時間性蓄勢磨礪出刀刃空間的「無厚」,透過「因其固然」的遊刃使「無厚」與「有間」相配合,使之形成時間與空間的舞蹈,或海德格爾所謂「時間-遊戲-空間」 (Zeit-Spiel-Raum) 。表面上看來,「以無厚入有間」不過是兩種空間的幾何關系 (刀刃厚度與骨節寬度之間的關系) ,實際上卻是兩種時間性之間的音樂關系。這便是為什麽在文惠君看來,庖丁解牛的動作「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庖丁敘說開始之前的「釋刀對曰」是解牛音樂的序曲,解牛完成之際的「提刀而立,為之而四顧,為之躊躇滿誌,善刀而藏之」是音樂的余緒。邵雍和方以智都曾註意此一躊躇。 「躊躇」不是缺乏決斷的猶豫,而是充滿決斷可能性的等待。隨時可以做出某種決斷,但每一個決斷的可能性目前還都只是輕柔的可能性,尚未成為堅硬的決斷。覺知的觸角觸摸到現實的每一處最微細的邊界,充滿可能性的全部空間,但目前還只是「虛以待物」。這便是「躊躇」之為間性的覺知。「躊躇」猶【詩】之「踟躕」,同一雙聲疊韻詞的不同寫法而已。 [ 韓詩即作「搔首躊躇」,參【詩三家義集疏】上冊,第205頁。] 【詩】雲「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詩經·邶風·靜女】) ,亦如庖丁之躊躇,皆「虛以待物」之時間-空間也。等待需要時間,而時間待出空間,所以【養生主】庖丁三年乃不見全牛、十九年若新發於硎,皆「以無厚入有間」之空間工夫的時間前提也;【人間世】顏回數月不茹葷,而孔子誡葉公子高「美成在久」,亦對待之融化於等待、空間之滅跡於時間也。
庖丁解牛的兩個著眼點分別在刀和牛之上。前者是解牛的工具,後者是所解之物。但庖丁在這兩個東西上面所下的工夫,卻恰恰都是對這兩個東西的無化。「無厚」是刀的無化,「有間」是牛的無化。當刀的質礙無化為「無厚」,牛的質礙無化為「有間」,遊刃的舞蹈就可以自由進行。只不過,刀的無化不是象少年胡塞爾那樣把刀磨到沒有 (那樣也無法解牛了) ,而是讓刀成為一種「虛以待物」之氣,讓刀刃和解牛的「神」成為「聽之以氣」的耳朵。同樣,牛的「有間」也不是「唯心地」把牛視為虛無 (那種唯心主義也太廉價,只值一碗雞湯的價格) ,而是經歷了「所見無非牛者」到「未嘗見全牛」到「以神遇不以目視」的過程。如果說牛就是物的隱喻,那麽,這個過程就是「物化」的過程。莊子的「物化」不是現代漢語中所謂人異化為物的意思,而是【人間世】孔顏心齋對話的最後談到的「萬物之化」。【齊物論】莊周夢蝶的最後,也說到「此之謂物化」。牛「物化」為「有間」,刀「無化」為「無厚」,而此二者之所以可能,則因為「以無厚入有間」的「舞化」。在遊刃之舞中,刀與牛、人與物,都渾化在天地之間,逍遙乎鴻蒙之氣,遊而已矣,舞而已矣,這便是珠,這便是道,這便是原初的或復性的整全。
間性覺知與整全渾化
「未嘗見全牛」意味著在下刀解牛之前,已經用眼睛把牛解開了,見到了牛體骨節之間的「有間」。不過,這個「有間」還是視覺的和分析的結果,尚不足以成為遊刃舞蹈的場域。遊刃的舞蹈只有在一個身心整體渾化的「有間」中才能自由發生。這個「有間」必須透過「以神遇不以目視」的基於身心整體觸覺的間性覺知來超越視覺、超越分析,重新回到一種「全牛」的狀態才能達到。這個重新返回的全牛不再是無間的全牛,而是有間的全牛;這個全牛中的有間不只是無化的結果,更是渾化的結果。
僅由目視得的「有間」還只是牛之有間,而非我之有間。只有等到「以神遇不以目視」的重新整全化,才能把牛之有間內化為我的間性覺知,使我進入一個物我渾化、相與舞蹈的時間-遊戲-空間。這是一個大間。我必須首先進入這樣一個大間,並使自己與物共舞,然後,我的刀才有可能遊刃於牛骨之間的小間,使小間成為大間渾化的一個部份,使空間成為時間舞蹈的一個部份。
解牛的困難,無非是空間質礙帶來的困難,而庖丁的解決方式則是透過時間來化解空間的難題。如何用刀是庖丁解牛成功的關鍵,但其用刀之道恰在其不用:全部關於解牛的敘說始於「釋刀」,終於「藏刀」,中間「動刀甚微」「提刀而立」,全無揮運之跡,也就是說,全無空間性的暴力對抗,只有時間性的以柔克剛。在這個意義上,也許無論庖丁解牛的「有間」之「間」,還是【人間世】的「間」,本質上都是時間之間對空間之間的化解。
間是離卦之象。所謂虛明,所謂洞然明覺,都是離卦之象。【易系辭傳】「制器尚象」章所言十二件器物中,離卦及「取諸離」而作的網罟是第一件。 [ 【系辭下傳】:「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為什麽離卦和網罟位居制器尚象之首?也許因為漁獵是人類最初的生活方式?但漁獵何以可能?豈不是因為覺知事物以定位之並漁獵之,正是人類開始從事物中綻出的第一件事?所以,離卦的網罟首先是間性覺知的網罟,使事物顯現並進入「人間」的網罟。故【說卦傳】雲:「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又雲「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在離卦網罟的「間之覺知」中,人方始與物照面,人方始與人相見,人類文明方始在間性中開啟,透出曙光。這個曙光是時間性和整全渾化的,只不過當人透過時間的渾化而看到空間的界畫之後,轉而淡忘時間的生命經驗,過度依賴空間的集置 (Gestell) ;淡忘「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能上能下的「而」,轉而定格於有形之物和無形之道的抽象對立,遺失了形與無形之間、道與器之間的那個間性。離卦之義,實存於此間性之中,存於時間給出空間的運化之中,存於「形而上者謂之道」與「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而上」「而下」之中。
「萬物皆相見」的前提是間性的區分。間性的區分就是能相及、能物化的區分。我與人、我與物、人與人、物與物之間,既相區分,又相影響、映照、疊運、化合,齊而不齊,不齊之齊,是為間性之區分。【齊物論】結尾的「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已經預示了【養生主】間性的開啟,而莊周夢蝶及蝶夢莊周則是二者的相見或間之覺性的層層開啟。「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誌與,不知周也」是一層開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是第二層開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是三層開啟。三層覺醒之間,猶有間焉,是為間之覺知的層層覺醒。
「養生主」之主竟何在乎?在乎間之覺知的整全渾化。「緣督以為經」:督之覺行於經之間,間之緣覺與經之渾化也;「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止而讓出間,神欲行則覺行其間,渾化其間,間之覺知與神之渾化也;「以無厚入有間」:刃之無厚,覺之微也,入乎有間則覺行其間也,「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則渾化其間也;乃至於開篇關於生之有涯與知之無涯的討論,結尾嘎然而止的「指窮於為薪」寓言,皆可循此「間之覺知」開啟一條理解的通道。
【養生主】開篇關於知識與生命、有涯與無涯的討論,就已經預示了「間」的意義。知之無涯與生命之有涯,就是生命的時間之間與知識的空間之間的緊張關系。「以有涯隨無涯」則「殆已」,而「以無厚入有間」則「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貌似一樣的行動,為什麽結果如此相反?因為「以有涯隨無涯」是以有入無,而「以無厚入有間」則是以無入有。「以有涯隨無涯」是「有」疲於奔命的追隨和消逝於「無」,「以無厚入有間」則是「無」遊刃有余的進入和舞蹈於「有」。「以有涯隨無涯」雖是一種出於被動性的艱辛追隨,但野心卻很大,其欲望是以有消無,即以「求知欲」全面地占有知識,消除無知,消除間性。反過來,「以無厚入有間」雖出於主動的進入和遊刃,但卻是無欲之入、無心之遊,是要盡量取消刀刃之有,以便融入有間之無,保持和強化對於間性的自覺。「以有涯隨無涯」是被動驅使的主動欲求,「以無厚入有間」則是主動尋求的被動覺知。「以有涯隨無涯」的被動性是被驅使的抑郁,表現為一種征服的躁狂,故無論主動還是被動,皆非自由;「以無厚入有間」的被動性則是主動培養出來的「虛以待物」的能力,不師心自用而能以物觀物,所以無論其表現為主動還是被動,皆為自由。自由無往不適,不自由進退皆非。自由者自由地被動或者主動,不自由者不自由地主動或者被動。主動不一定自由,被動不一定不自由。自由者自由,不自由者不自由。
如果按庖丁解牛的方式來看知識問題,就不應以有涯之生追逐無涯之知,而是要「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莊子·大宗師】) 。「知之所不知」是內在於知中的不知,猶如內在於生命中的死亡。生命固有一死,否則無所謂生命不生命。生命之有涯不是要去克服的缺陷,反而是要去保養的方面,正如「知之所不知」不是知識的缺陷,而是要去保養的「恬」。保養生命之有涯,並不是「與死亡作鬥爭」以求長生不死,而是適其性、盡其天年而已;同樣,保養「知之所不知」也不是「與無知作鬥爭」以追求全知全能,而是為了以知養恬、以恬養知而已 (參【莊子·繕性】) 。
保養生命之有涯是保養生命的間性,保養「知之所不知」也是保養知識的間性。生命的間性來自生命中固有的死亡,知識的間性來自知識中固有的無知。死亡並不是只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到來的事件 (death) ,而是伴隨生命始終的持續過程 (dying) 。知是知之所知,不知也是知之所不知。正如孔子所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論語·為政】) ,又如「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先進】) ,是真正的知生已經包含知死。內在於生命本身中的持續死亡過程,使生命成為有間的生命;內在於知識本身中的無知,使知識成為有間的知識。這就像太極圖的陰陽魚所示,黑魚因其有白眼而能追白魚之尾,白魚因其有黑眼而能與黑魚遊戲,黑白魚皆因其自身中內在的對方而成為有間之魚、能遊之魚。黑白魚相與遊戲、相反相成,正如「知與恬交相養」的相間渾化 (【莊子·繕性】,恬即無知) ,亦如「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的渾然相間、「兩忘而化」 (【莊子·大宗師】) 。否則,就是【大宗師】裏的子來之妻,「環泣」而「怛化」,或如【則陽】所謂「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庖刀之刃與養生之主
【養生主】為什麽以一個解牛殺生的寓言來講養生的道理?因為【養生主】之義不只在養生,且在養生之主。「主」字字義,在於燈盞器形上的那一點火焰, [ 【說文】:「主,燈中火主也。」] 而此火焰的煥發光亮恰恰意味著燈油物質的逐漸消亡。此義至【養生主】篇尾已揭之無余:「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方以智【養生主總炮】雲:「養生、殺生相反,誰能解之?其惟見全者乎!」 [ 方以智【藥地炮莊】,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第218-219頁。] 見全,則見薪盡之死、火傳之生,其實一也;見 全,則秦失吊老子而見「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莫非一也;見全,則庖丁遊刃於已發皆中節之和,藏刀於未發之中,故十九年解牛數千而未嘗殺也。一非頑一而能自我間之(此「間」讀去聲,猶「離間」之「間」),能自我間之則一而二也,獨而全也。全者,有間之一也;一者,見獨之全也。
何謂「養生主」之「主」?庖丁之「刀」與「刃」的微妙關系可能蘊含了某種提示。「刃」只在「刀」上加了一點,以便指示刃在刀上的部位。然而,這個部位究竟在哪裏呢?自然是在薄的那一邊:厚的一邊是刀背,薄的一邊是刀刃。然而,當我們去到薄的一邊,又在哪裏能發現它呢?從厚的一邊到薄的一邊,從刀背到刀刃,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在這個連續過程中,沒有一處是刀刃。恰恰是到這個連續過程中斷的地方,也就是說,在刀之為刀斷然終止而「無厚」為虛空的地方,才碰到一種叫做刀刃的東西。這個東西有,但只在有快要變成沒有的時候才有。這個東西並非沒有,但它幾乎不比無多一點存在。這個東西存在於有無之間、刀與非刀之間、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生與死之間,知與無知之間,幾乎就是「象罔」之義的一個具體征象。黃帝使象罔乃得玄珠,正如庖丁遊刃乃得解牛。
在庖丁解牛的自述裏,刀似乎只是用來放下 (「釋刀對曰」「提刀而立」) 和收藏 (「善刀而藏之」) 的,而揮舞遊動的只是刃:「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刃當然是無法脫離刀而被獨立揮運的,正如燈焰不能脫離燈台而閃耀,心神不能離開身體而獨明。但這並不意味著二者的區分不可能,也不意味著其區分不重要。「刀」「刃」之別非常微妙,易被忽略,而在庖丁解牛的敘說裏卻很可能是至關重要之點。真正的要點總是容易被讀者忽略的東西,但其實又是特別顯而易見的簡單事實。在庖丁解牛的敘述中,唯一一次說到刀的揮動也只是「動刀甚微」,而且即就此處文本,也有作「動力甚微」的版本, [ 「動刀甚微」,【道藏】成玄英疏本作「動力甚微」,更無動刀之意,與筆者此處的分析更合。更多相關分析,請參拙文【藏刀與藏天下】,見收拙著【道學導論(外篇)】] 刀並不在此出現。刀一旦閃亮登場,刃就會受傷,如「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都是刀的大動作和刃的大災難。庖丁敘此兩者,皆言刀而不言刃,以其揮刀而已,非遊刃也,故不入道;而接下來講到庖丁自己,則是「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則恰恰又是回到刃這個關註點。可以說刀的系列和刃的系列,構成了庖丁解牛敘說的兩個範式。揮刀以傷刃,俗庖之害道也;遊刃所以忘刀,庖丁之技進於道也。
刃誠然屬於刀的一個部份,但卻是刀中最接近非刀的部份,也就是說,是刀中最不屬於刀的部份。刀刃是刀之為刀的本質部份 (無刃不成刀) ,但卻是刀中最遠離刀、差一點就不再是刀的部份。神與形、心與身、養生主與養生、無知之知與有知之知,都是這樣的關系。庖丁解牛要養的與其說是刀,不如說是刃;「養生主」要養的與其說是「生」,不如說是生之「主」。「主」上一點與「刃」上一點,有一種本質的關聯。【說文】:「主,燈中火主也。」燈盞是一個確定的器物,其形如「王」 (最上一橫彎曲如凵,如燈盞盛油之形,下面的「土」是底座) 。但這個確定的器物之形卻不是燈之為燈的本質。燈的本質在於燈盞上面那一點,即燈光之焰。那一點並不是燈盞之形中固有的部份,而是燈形之外的部份。在字形上,「主」上一點也並不與下面的盞形相連。但燈之為燈的本質,卻取決於那個不屬於燈盞之形的光焰。所以,如果說庖丁之刀是養生之生,那麽庖刀之刃就是養生主之主。此「主」非生,卻能生生,猶如火焰非盞而能使燈成為燈。此「主」於庖丁解牛寓言中見諸無厚之刃,於【養生主】末章「指窮於為薪」則見諸不盡之火,而其義早已潛藏於「刃」「主」二字之點中。由此二字之點,可得養生之主;得養生之主,方可進乎文惠君之悟,非僅「得養生」而已矣。「得養生」只是文惠君之得,因為他關心的是技。庖丁本人所言則事關養生之主,是道也,進乎技矣。此間之別,大類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關心「何以利吾國」,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說文惠君即梁惠王,則莊孟之間,同異微矣。
「刃」是「刀」上加一點,但這個點並不是像「雨」字中間的點一樣象形真實存在的雨點,而是指示一個無法象形的東西。刃之所以無法象形,是因為刃幾乎就沒有形,或者說它只是形與未形之間的臨界。所以,「刀」上一點與其說是對「刃」之部位的靜態指示,還不如說是從有到無的動作指示。這個動作便是「無厚」的「無之」過程。較多「有」的一邊是刀背,越來越趨向「無」的一邊是刀刃。刃在薄的一邊,或者說,在更接近「無」的一邊,這便是「刃」中一點的「無厚」之義。只有從此出發,以無厚入有間,才能把【養生主】開頭的有涯無涯和結尾的「指窮於為薪」連線起來,成為一條道路,以及把中間的庖丁解牛、公文軒見右師、澤雉、秦失吊老聃等寓言都連線起來,使之成為一只可解的全牛。
回照【養生主】的開頭,如果按「以無厚入有間」的思路來求知,則首先應該納入的恰恰是無知,讓無知成為首要的知。心是身之刃,故無厚即無心,猶「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知是心之刃,故無知乃有心之無厚。無心之氣、無厚之心、無知之知,乃是自知無知的、時刻朝向無知開放的心靈。如此,則心常有間,心常有閑(閒)。「間」作為能感之氣,虛以待物之氣,乃使覺知成為可能。
無厚之刃是以周圍的空來包裹自身之有,這是坎卦之象 (坎兩陰夾一陽,中有外空) ;有間之節是以周圍的有來撐開自身之無,這是離卦之象 (離兩陽夾一陰,中空外有) 。所以,「以無厚入有間」即以坎入離,以水濟火。水火既濟,則「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而四顧,為之躊躇滿誌,善刀而藏之」;火水未濟,則「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在庖丁的敘述中,上面兩個句子緊緊連線在一起,猶如在【易經】的末尾,既濟未濟兩個卦連在一起, [ 【莊子·養生主】:「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而四顧,為之躊躇滿誌,善刀而藏之。」原文以未濟在前,既濟在後,因為這是庖丁敘述解牛過程的話,必須先難後獲。但「已解」只不過是下一次解牛動作的開始,所以我的參照反以既濟在先,未濟在後,準【易】之序也。實際上,這兩句話由「雖然」帶起,已經是在「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的總結性敘述之後的補充說明,即已經是在既濟之後的未濟開端,所以,參照時的顛倒正是對其本質秩序的回復。] 或如自然的萬物生長之中,以及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水與火從來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相反而相成。而水火坎離之化蘊含著生命的初機,「養生主」之所以養生,於斯可見矣。
反過來,「以有涯隨無涯」則是以火入水,必將自滅心神之火,而無濟於水。知如無涯之水,我生如一炬火光,與其「以有涯隨無涯」,不如「莫若以明」。「莫若以明」就是以無厚之意,觀有間之疏明,以及發生於其中的大化流行,而不是妄圖以我之爝火燭照天地之大。【詩】雲:「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大雅·旱麓】),以明之至也。王船山解之雲:「鳶飛戾天,觀化於天之下也;魚躍於淵,觀化於淵之上也。上下定位,化亙其中而不可為之畛域。故天其函乎!地其興乎!大有之載,‘積中不敗’者,一氣之純乎!故【中庸】曰:‘言其上下察也。’自淵而上,無不在焉;自天而下,無不在焉」(【詩廣傳·論旱麓】)。「上下」者,天地之間也;「在焉」者,在其間也,在其間而川流也,敦化也,萬物之各在其間、各行其道而不相悖也。此天地之大間也,大道也,而解牛、心齋之所共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