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劉夢溪著【東塾紅學三書】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了,「三書」即【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修訂版)、【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增訂版)、【大觀園裏和大觀園外】三種紅學著述。

筆者於2024年8月23日上午10時收到順豐快遞的【東塾紅學三書】,其中【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修訂版)扉頁前襯頁有著者的題贈簽名,題簽時間2024年8月21日。
筆者曾在【名家與紅樓夢研究】一書「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是‘兒童團’時期的營生」一章中做過粗略統計:
自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劉先生先後題贈「淮生先生惠正」「淮生先生指正」「淮生先生教正」「淮生先生存正」的著作大概14部16冊,特分列如下,以見真跡: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
【牡丹亭與紅樓夢——劉夢溪論紅樓夢】,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
【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中國現代學術要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
【現代學人的信仰】,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馬一浮與國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
【陳寅恪的學說】(三卷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
【學術與傳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版;
【七十述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陳寅恪論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中國文化的張力】,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韓譯本),韓惠京轉譯,2019年版;
以上著作的閱讀收獲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方面是對於修訂【劉夢溪紅學學案】的直接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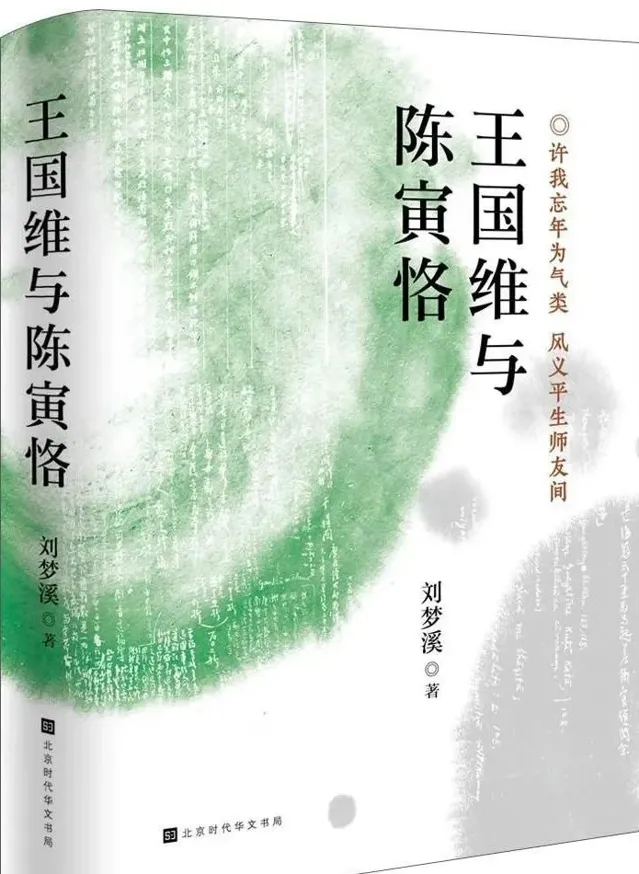
【名家與紅樓夢研究】一書由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未能及時收錄2020年11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劉夢溪著【王國維與陳寅恪】一書,題贈簽名時間即2020年12月27日。
時隔一年略有余,筆者又收到劉夢溪著【八十夢憶】題贈簽名本,該巨冊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1月出版,計606萬字,插圖60幅。筆者原擬通觀【八十夢憶】【七十述學】之後撰述一篇書評,以略酬問學之交誼,然塵務縈心,至今尚未隨願。
前文所列14部簽贈著述中,筆者尤為重視【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此書傳播最為廣遠,影響頗為可觀,堪稱紅學史述類的別出心裁之作。
據商務印書館本「修訂版前記」說:「本書今次是第四版,第一版的出版者是文化藝術出版社,時間在1990年。第二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第三版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每個版次的間隔時間在六至九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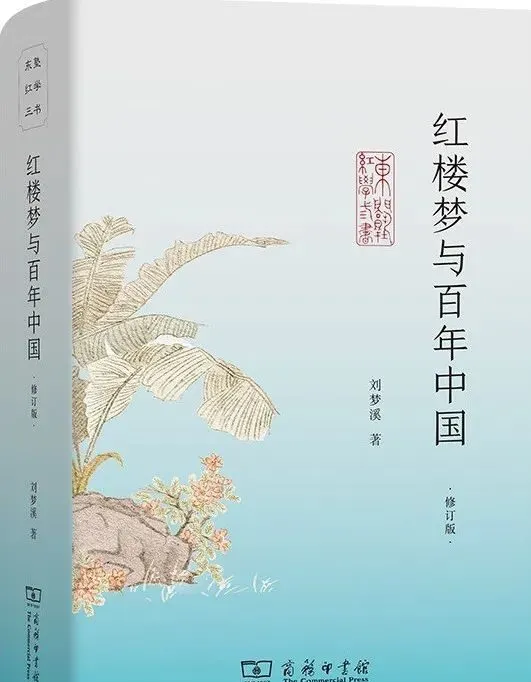
除了上述四個版本之外,韓惠京教授轉譯的韓文譯本正式出版於2019年,書名題為【論證劇場: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紅學智力冒險】。
劉夢溪在 「修訂版前記」中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被轉譯成韓文,是我不曾想到的。這要感謝南韓加圖立大學韓惠京教授的苦心孤詣。當韓文版甫將竣事之際,她來到北京與我晤面。她的譯筆是令人信服的。書名,韓文譯作【論證劇場: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紅學智力冒險】,可謂深得拙著精神旨趣得神來之筆。」
韓惠京教授則在「韓文版譯者後記」中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可謂將與‘紅學’相關內容一網打盡。可以說這本書展示了紅學史的本來面目。我們在這部書中能看到在其他書中很難看到的紅學的真相。……【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對於百年間紅學史的龐大內容按照不同的流派進行了整理,對於圍繞紅學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爭論一網打盡,可以說這本書是一部能讓人有如臨紅學論爭現場的閱讀感受的一部書。」
韓惠京教授的此番話大抵可以說明韓文版書名的旨趣,這一旨趣獲得了原著者的欣然認同。
毋庸置疑,【紅樓夢與百年中國】被轉譯成韓文傳播,自然也是包括筆者在內的一般紅學研究者都不曾想到的,此亦顯見這部紅學史著述實實在在的影響力。
據筆者所知,近幾十年來影響力持續不衰的紅學著述應首推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此外,為數不多的紅學研究暢銷書中【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應屬必選,且堪稱「紅學必讀書」無疑,不僅入門必讀,亦研究必讀。
筆者執教中國礦業大學迄今二十五年矣,這期間給本科生、研究生講授【紅樓夢導讀】【紅樓夢鑒賞】【紅樓夢研究】等課程近二十年,【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則是指定的課外必讀參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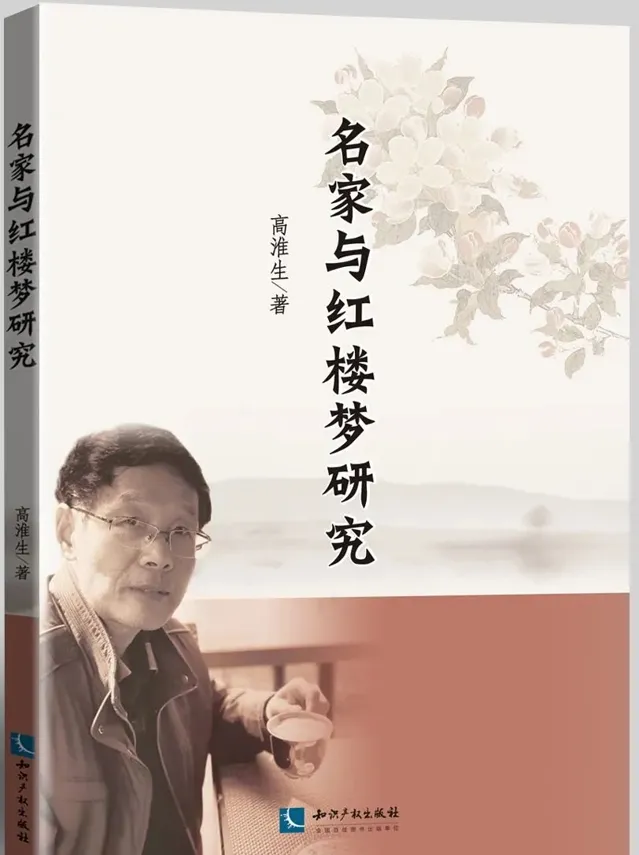
那麽,【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何以成為指定的課外必讀參考書呢?此可參見筆者曾在【名家與紅樓夢研究】一書中記述的一段真切感受:
7月10日午後,看到劉先生發來的韓譯本【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書影以及微信留言:「韓惠京轉譯,815頁,裝幀考究。可惜我看不懂。」筆者回復道:「看不懂無妨,這一成果影響可觀!」劉先生感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筆者回復道:「悠悠歲月,余心有寄何所求!在筆者看來,紅學史著凡數十部,能雅俗共賞者寥寥無幾,先生著【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可謂能領風騷矣!」
由以上感慨可見:【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這一「兒童團」時期的營生畢竟在劉夢溪先生的心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銘印!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雖不曾想到【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竟然譯介海外傳播,卻已有過一段先知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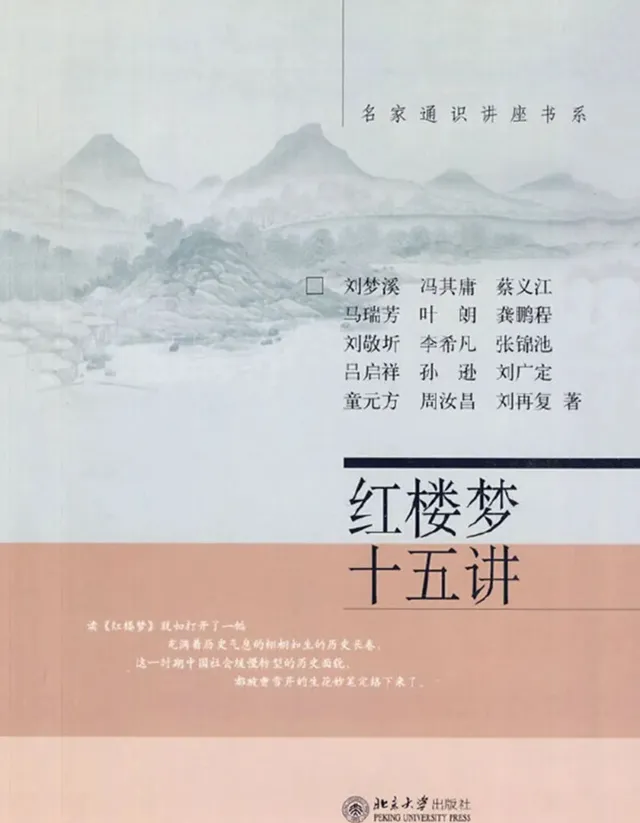
2017年6月24日,筆者曾赴南韓首爾參加由首爾中國文化中心和南韓紅樓夢研究會共同主辦、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承辦的首屆韓中學者紅學研討會即【2017南韓紅樓夢國際學術大會:韓中紅學家對話】,研討會的綜合討論與自由問答階段,韓惠京教授提問道:「請問高淮生教授,您對劉夢溪先生著作【紅樓夢與百年紅學】怎麽評價?」
筆者回答:「【紅樓夢與百年紅學】寫作體例新穎,材料編織巧妙,學術史影響較大。如果說到不足之處,那就是不能像學案史那樣把學人寫得足夠鮮明生動,也不能像通史把事件和時間寫得更加系統全面。」
韓惠京教授比較滿意以上回答,筆者當時並未深究其提問的特別用意。
會議閉幕後,韓惠京教授主動告知筆者,【紅樓夢與百年紅學】韓文譯本不久將出版,所以對【紅樓夢與百年紅學】的評價很關心。
又據韓惠京教授相告:此前已經轉譯出版了劉夢溪先生的【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一書。聽了韓惠京教授的主動告知,筆者竟多了一份期待。
時隔兩年有余,筆者欣慰地收到韓惠京教授2019年8月19日簽名題贈的【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韓文譯題【狂者的誕生——中國狂人文化史】)以及【紅樓夢與百年紅學】(韓文譯題【論證劇場: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紅學智力冒險】)兩種譯本,筆者由此兩種譯本的選題便十分地欽佩韓惠京教授的學術個性和學術精神。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韓文版譯者後記」中所說的一段話:「轉譯的過程如同與紅學旅程中的無數學者一道品嘗其中的苦樂,轉譯完成之後的心情就像從一場心酸的夢中醒來一般,如同在迷夢中徘徊。仿佛答案就在眼前,然而正要抓住時卻瞬間從手中滑落,於是只好再次握緊。雖然花費不少精力,付出不少努力,最後卻讓人感到不過是枉費精力而已。誠如很多紅學家所言,在閱讀【紅樓夢】後所產生的那種虛無感與混亂感,在回顧紅學史時依然縈繞於心。讓人感覺到,不但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反而陷入很深的混亂之中。……這些學者有關紅學論爭的風采讓我對於學者的姿態與風度有了重新審視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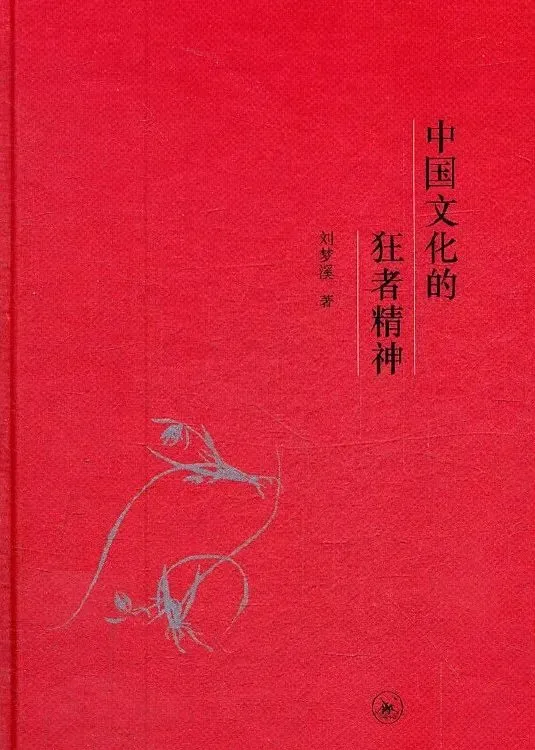
韓惠京教授的譯後感悟很自然地令筆者記起劉夢溪在由【紅學】改名【紅樓夢與百年紅學】的二版題序中說過的一段話:時下的紅學由梁任公先生給定的第四期(即衰落期)向前又跨了一步,似乎進入「鬧學」時期……這回可真的該告別紅學了!
筆者由此認為,【紅樓夢與百年紅學】的確是一部可以給著者、讀者、譯者同樣帶來深切感悟的紅學書,感者自感,悟者自悟,真可謂:各有靈苗各自探!
據筆者所知,紅學百年歷程中海外紅學著述中文譯本常見,而中國內地學者的紅學著述譯介海外者寥寥。韓惠京教授曾告知:這是南韓第一部介紹【紅樓夢】研究史的書。
另據南韓首爾大學崔溶澈教授的女弟子王奇比博士相告:出版【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韓譯本的這家出版社的確非常有名,其對所出版書籍總有很嚴格的要求, 所出版的書籍往往被認為是很有價值的著作。

或問:為什麽高淮生教授在回答韓惠京教授的提問時竟如此從容篤定呢?答案即在2013年2月新華出版社出版的高淮生著【紅學學案】一書中。
【紅學學案】一書第十二章即「劉夢溪的紅學研究:紅樓新論猶可論、紅學史述善通觀」,章下三節分別為「紅學新論:【紅樓夢】與紅學通解」「紅學史論:【紅樓夢】與百年中國」「紅樓探源:【紅樓夢】與文化傳統」,其中「紅學史論」一節對【紅樓夢與百年紅學】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評述。
現摘取幾則如下: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則無論在學術樹義、學術視野、方法論、學術境界等方面明顯地勝過【紅樓夢新論】,這部紅學史著述已經成為當今紅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同時也成為【紅樓夢】教學的主要參考資料。這是他學術轉向過程中形成的成果,即劉夢溪在「傳統與文化」「學術與傳統」「紅學與傳統」等方面的思想沈浸過程中,思想和方法更新了,視野開闊了,思想融通了。
陳寅恪、錢鍾書、余英時的影響是促成其學術思想和方法、態度和立場轉變的直接精神動因,以上三位學人的學術精神和人格精神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通」→「通達」「會通」「融通」「圓通」「通識」。也就是說,他們都是「通人」,所謂「通人」即「主體自覺並得到充分弘揚的人」,劉夢溪「心向往之」地企慕這樣的「通人」。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在紅學史著述中又有著怎樣的突出特點和學術貢獻呢?
現在還不是為紅學史著述規範某一通則的時機,迄今為止的紅學史的撰述仍然處於探索新路的時期,各種寫法都可以嘗試。盡管嚴格按照所謂「時間行程」撰寫通史是紅學史寫作的常規,但並不說明紅學史寫作就只能設定這一「一元論述」的規範,同時拒絕「多元論述」的新規範的嘗試。可以這樣說,【紅學】或【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正是貢獻了紅學史著述的一種新樣本,至於這一新樣本的典範意義如何或是否具備純粹的學術史品質,則有待於時日的驗證。
劉夢溪的【紅學】或【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善用材料,博觀精取,並力圖在材料的梳理中顯其識見,就此而言,稱之為「學術史」足可當之。筆者姑且作這般並不見得恰當的比喻:著者就如同一位編織高手,大量的原始材料經過經緯交織之後而條理化了,這高手的能耐是否如晴雯織補雀金裘一般的巧奪天工,仁智之見常有,姑可立此存照。客觀地說,經過這一番「融會貫通」和「條分縷析」之後,這織品也就仿佛是獨立創作一般。這一「作品」又並不像有些紅學史著述那樣,著者充其量就是個「文抄公」。
〔馬來西亞〕卓鴻澤說:「作者盡量做到‘讓學術歸學術’,擺脫種種學術以外的成見,較之以往的紅學史專著,立論自由、活潑得多。這種‘突破’,不當限於劉先生個人,而應廣被整個大陸紅學界。我覺得這是劉著最可貴之處。」 不僅比較 「客觀公正」了,而且能體現著者的「好學精思」,而深思熟慮的識見往往來自這種「好學精思」。
劉夢溪感慨:「百年紅學的事情,比榮府的家政要復雜得多。只好舉其突出之點,略誌梗概。」 筆者將劉夢溪這一「略誌梗概」的特點歸納為:探源溯流、提要鉤玄;發遑心曲,論見新識。

以上評述是筆者對【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所做的粗略的學術史通觀,由此亦可見彼時「覘文輒見其心」之嘗試過程。
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三版題序中說:「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貴,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龍】又‘知音篇’,劈頭就發為感慨:‘知音其難哉!’學問文章亦復如是,見知於當代,總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陳寅恪寧願相信:‘後世相知或有緣。’文化史上一些典範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統的密碼,由誰來完成這樣的作品,接受群體中誰能成為當時或後世的真正‘知音’,參與其中的個體生命角色固茫然若無所知,歷史也無法預設。不只是知識和學養的問題,對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尤其重要,甚至還需要‘有緣’。」
筆者【紅學學案】「前言」中曾如是說:「【紅學學案】撰述堅守兩個基本‘原則’:一則‘仰視其人格、平視其學術、俯視則不取’的心理原則;二則‘非遇親者而諛之、非遇疏者而略之、非遇強者而屈之、非遇弱者而欺之’的撰述原則。這兩個‘原則’究竟是否可取或縝密呢?當留待時日以檢驗。由第一個原則可知,【紅學學案】撰述只涉及學術事實的述評,不涉及人格價值評價。由第二個原則可知,【紅學學案】撰述‘不惟是非成敗定褒貶,而以學術貢獻論高下;秉持了解之同情,擯棄學派性偏見。’」
筆者至今堅信:彼時「覘文輒見其心」之嘗試過程的確做到了「秉持了解之同情」,至於是不是接受群體中的真正「知音」則不敢自我期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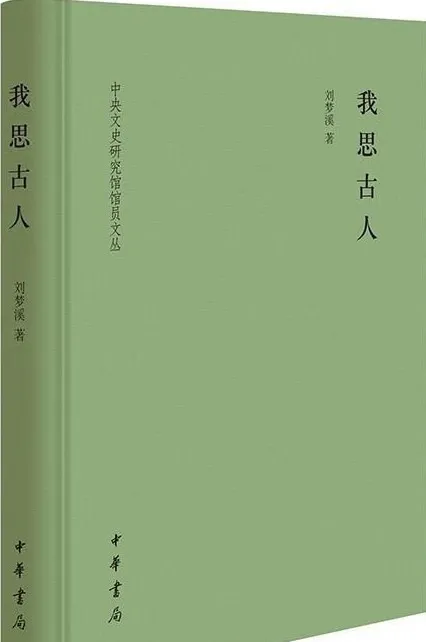
說句題外話:筆者曾促成【
韓惠京:〈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
譯者後記】一文的推介,該文即苗懷明教授主辦的「古代小說網」微信公眾號文章,釋出於2019年7月23日。因為這個學術性公眾號的讀者非常多,國內外的傳播影響力極大,釋出此文的確有助於【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韓文譯本的學術傳播。
【東塾紅學三書】的另外兩種紅學著述【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增訂版)以及【大觀園裏和大觀園外】皆頗見文心,義理辭章亦能相得益彰,亦恰如劉夢溪著【七十述學】自述:「我之為學,不諳異域文字,無家學可承。所長在識見,詞采也不錯,但積寶不足。一定找出有什麽優勢,我想在文本閱讀,不厭其細,反復推求,每有會心。即‘六藝’經典,也能因細詳而得雅趣,明其義理。故陳寅老‘了解之同情’一語,深獲我心。」
略作推求可知,【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增訂版)情辭流韻,別具意趣,以愛情心理學闡釋【紅樓夢】之「兒女真情」可謂別開生面;【大觀園裏和大觀園外】思理綿密,每每會心,其文章選題能見創獲亦多見啟迪。
筆者以為,此紅學二書之閱讀效果亦正如著者【大觀園裏和大觀園外】一文中所願:「帶來閱讀的歡樂,帶來文學的趣味,帶來理性的思考。」當然,因性分不同,偏好各異,讀者的領受自然各見厚薄。
筆者的閱讀感受:【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增訂版)以「閱讀的歡樂」和「文學的趣味」尤為突出,而【大觀園裏和大觀園外】則以「理性的思考」引人入勝。當然,此「二書」均能給人帶來「手不釋卷」的閱讀體驗,亦即「欣悅」的閱讀體驗。
筆者向來認為,做學問也如交朋友,有緣即訂交,無緣則離散,「欣悅」而已!既然「後世相知或有緣」,緣來緣往,各有分定啊!
正如【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修訂版前記」說:「紅學於我,用得上【紅樓夢】十二支曲的‘枉凝眉’中的一句話:‘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遇著了,奈何!其實‘遇’本身也就是緣。緣遇,緣遇,此之謂哉。」
做學問如此,讀書何嘗不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曾口占之四句亦可為「緣遇」佐證,特錄以為據——【庚子即至口占四句以奉夢溪先生解頤】:
丙申之遇沐春風,
疑義相析快哉翁。
尤憶他年擬紅案,
雁書沈影不從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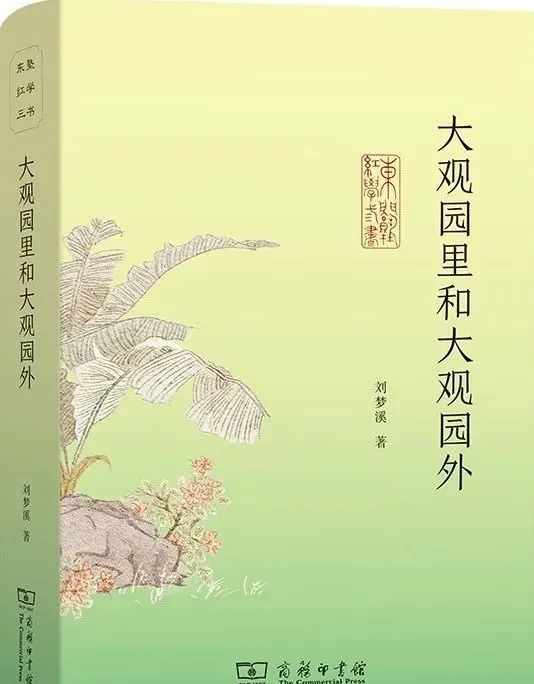
嘻!「丙申之遇」竟成就了「【東塾紅學三書】之評」,豈不「欣悅」哉!
劉勰【文心雕龍﹒序誌】曰:文果載心,余心有寄。【東塾紅學三書】實乃寄心之作,何啻「成一家之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