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公女】
一位男性作家,為什麽要寫一部以女性為主的小說?
在這個故事裏,三位女性生於河南駐馬店的三個不同村莊,父親都格外渴望男孩的誕生,有的成功了,更多的是失敗,母親因此離世或者被迫離家。這三個女孩只能在城鄉之間的縫隙中摸索、忍受、抗爭著長大。
鄭在歡記得這樣的三個女孩。她們背著麥稭走在鄉間的小路上,立在竈台旁刷碗,「在鄉間,從事與年齡不甚匹配勞動的通常是女孩,男孩們大都在玩兒」。鄭在歡母親早逝,後來離開奶奶家,與父親和繼母一同生活,他是幹活的那一個,註意到了同樣在幹活的女孩。
鄭在歡把她們的故事寫成了小說【雪春秋】,書裏,大雪、春藍和秋榮有著少見的主體性,是自己命運的絕對主角,她們受困於環境和自我的局限,又硬著頭皮向前走。
但某種程度上,並非是鄭在歡擅長寫女性,而是寫出這些被忽略的鄉村女性的故事是必然。在【駐馬店傷心故事集】裏,鄭在歡寫下家鄉駐馬店邊緣人的生活,那些人是他的鄉鄰、發小和他自己。
鄭在歡只能寫他能體認的人,「如果記憶就像杯子裏的水,我有十幾年的光陰是放在鄉村裏的,當我去喝水的時候,肯定會嘗到這些經驗」。
或許這也是【雪春秋】獨特的原因,這些女孩曾真實地生長於這片土地中。
以下,是看理想與鄭在歡的對話。
01.
三姐妹
看理想 :為什麽想要寫一個以三位女性為主的故事?
鄭在歡 :我認識這樣的三個女孩。這個題目其實定下來很久了,我會把想寫的、有感覺的東西列一個文件,這三個女孩的故事是我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放到電腦裏的,但是一直都沒有寫。
我最熟的是大雪家的故事,大雪的原型是我的親戚,小時候,我們倆都是幹活的那個。還有一個女孩的原型我只見過幾面,9歲、10歲左右,她就從我們村搬走了。
2020年,我看了彼得·漢德克寫他母親的小說,【無欲的悲歌】。他的寫作讓我找到一種寫女孩的方式。漢德克在他的寫作中是一個自我存在感很強的作家,他要寫他母親,又不能去除自我意識,他選擇像解剖一樣,把母親的生平拆成碎片去寫。
他寫母親的一生,只用了5萬字,但在我看來那5萬字很濃縮,他拒絕講故事,那些資訊全部濃縮在一句一句斷言式的、解剖式的話裏。當時我覺得這種寫法就是從感覺出發,從對人物的認識、論斷出發,我應該也可以這樣寫。
【雪春秋】裏有大量的情節是省略的,因為在人物看來,對她來說不重要的情節不會展開。我會著重去寫事件之後人物的感受,把情節作為對感受的補充。
「堂弟小寶在一邊玩玻璃球,玻璃球滾到腳下,她想像往常一樣給它踢飛,可她懶得動。她打著飽嗝,還是覺得餓,要等很多年以後,她才能知道,這不是餓,是空,心裏空落落的,一頭大象都填不滿。
——【雪春秋】

【母親 Mother】
看理想 :書中的三位女主人公來自三個相似也有不同的家庭,在寫作的時候,怎麽考慮她們各自家庭背景的呢?
鄭在歡 :我想講述她們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她們的家庭結構有代表性。我們這一輩90年前後出生的人,父輩家庭基本上是三種模式,最多的是春藍式的家庭,父母健在,家庭和睦,大家力往一處使,努力掙錢。
也有一些離異的。這種情況在我父輩那個時候少,一旦出現,就會成為很顯眼的存在。那時候的離婚大部份是父親發起的,現在90後離婚基本上已經是由女性發起了。
還有一種是父母一方去世的,像大雪的家庭。這也是我自己的投射,我母親很早就去世了。
看理想 :這三個女孩的家庭,恰好也都各自有三個姐妹。
鄭在歡 :這個也是真的,現實有這種巧合。我一開始只是要寫其中一對三姐妹的故事,在前期準備的時候,又發現了更多的姐妹,那個時候農村要男孩的執念比較深。這不是什麽設定上的巧思。
後來我覺得,這樣寫有一個很好的點,能讓她們把身上的親緣關系抽離出來,組成新的三姐妹。這個故事最大的價值取向就是,不要過度依賴血緣。對這三個女孩來說,家庭對人的傷害和牽制弊大於利。在我們那一代,大多數家庭是因為要生男孩,才生了那麽多女孩,如果第一胎、第二胎就是男孩,會不太有三姐妹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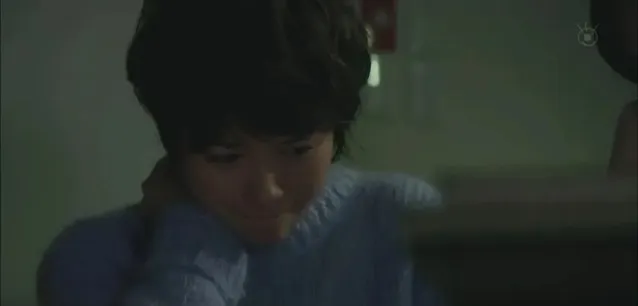
【問題餐廳】
可能也因為我自己的家庭沒那麽好,我關註到的都是不太好的地方。不要那麽依賴血緣,也是我的認識。當然農村裏面讓人羨慕的,比較和睦的家庭也有,但是我不太了解他們為什麽能做得那麽好。托爾斯泰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不幸。不幸的家庭可能不幸的因素比較多,幸福的家庭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好人。
02.
弱勢是一種處境
看理想 :大雪、春藍、秋榮,是三個性格不同的女孩,她們形象的塑造參考了你的個人經歷嗎?
鄭在歡 :是,我會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分散到她們三個人身上。畢竟還是在寫故事,我也沒有經歷過那麽多女孩子的事,沒有那麽多體認,只能設身處地地去想人遇到這種狀況會是什麽樣的感受。
我是奶奶帶大的孩子,從小跟奶奶一起生活,我很喜歡聽農村女性一起聊天,她們敘家常的時候情緒很豐富,從她們豐富的情緒裏,可以感知到她們對什麽介意,對什麽不介意。
我跟書裏的三個女性有一些同病相憐的地方。書裏秋榮羞於讓人家看到在幹活,那就是我。我小時候幹活最大的煩惱不是累,是被人看到。因為跟奶奶生活的時候,我是不幹活的,是淘氣的,跟大家一起瞎玩,但是到我回到繼母身邊,必須得幹活,我又不想讓曾經的玩伴看到我在地裏拔草,這個事在我看來太丟臉了。
包括我在幹活的路上,被大人碰到,他們會說,哎呀,這孩子怎麽那麽小就出來幹活了。我知道他們是好心,但這個好心是對人有傷害和刺激的。
看理想 :如果大人們看到很小的女孩在幹活,也會說這樣的話嗎?
鄭在歡 :他們會說的比較含蓄,比如書裏大雪幹活的時候被人看到,大家就說,哎呀,這孩子真能幹,真賢惠。但大雪聽了也不開心,孩子還是被寵著比較開心。我小時候最想要被大人評價的是,這孩子真淘氣,真不聽話, 而一個孩子被說很聽話,就被剝奪了作為孩子的特性。

【母親 Mother】
看理想 :所以你能看到她們,可能也是因為自己當時的處境是比較弱勢的。
鄭在歡 :肯定是這樣了,因為如果我不幹活,我看到大雪可能根本不會心疼她,或者不會太在乎她,自己跑出去玩了。只有經常在田間地頭幹活的孩子,才會去想她們為什麽會落到如此地步。我是因為嚴厲的繼母,她們是為什麽?
看理想 :書裏的秋榮是一個特別的女孩,她是三個女性中最決絕的一個,知道僅依靠異性無法獲得安穩的生活,一個人的立身之本是會一門技術。她不向父親低頭,與原生家庭決裂。她身上的故事,有一些與你之前在采訪中分享的童年片段重合。秋榮是你投註自我最多的角色嗎?
鄭在歡 :秋榮是虛構性最多的人物。她是我沒見過幾面的女孩,因為母親改嫁很早就搬出去了。我記得她小時候長得很漂亮,眼睛很大,但其實她的面目已經模糊了,我還記得她很有一種很倔強的勁,就這麽多,剩下的是虛構。
我也不一定能做到像秋榮一樣決絕,但是你想塑造一個理想的人的時候,我想象的就是秋榮這樣。她的牽絆最少,一開始就對什麽都絕望了,家庭分崩離析,從小寄人籬下,父親不管,母親走了,跟著嬸子生活。秋榮的生活是一種更徹底的無依無靠,她變得決絕也是合理的。
「誰說的,我當然有想要的東西。
那你想要什麽。
我——。想了好一會兒,似乎也沒有什麽東西特別想要。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沒有。大雪說,比如說你在美甲店工作,你也想要開一家自己的美甲店,那就是特別想要的東西。
對,我想開一家美甲店,自己當老板。」
——【雪春秋】

【問題餐廳】
看理想 :你會最喜歡秋榮這個角色嗎?
鄭在歡 :其實我傾註心血最多的是春藍,她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孩,最沒有故事性。如果不寫她,會很像因為另外兩個女孩家庭殘缺,有故事,所以你才寫。
寫春藍就是嘗試去寫普通人的事,整體來講,她是我最熟的一個人,原型是我堂姐,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就是跟她一起,她比我大一歲,後來去北京,也是她帶我去的。
我十九歲開始寫小說,從來沒有想過要寫她。但因為我們倆太熟了,離得很近,你會感覺到她各種細微的心緒。她有自己的不服和不忿,大體上又是一個順從的人,怎麽把她身上的矛盾性寫出來,我費了很多功夫。
03.
我只寫我能體認的人
看理想 :可能這也是這本書讓很多讀者感到觸動的原因,這些女孩的故事很生動。創作這本書的時候,要如何克服一些可能來自性別視角下的思維慣性?
鄭在歡 :我就跳過去了。我不是克服派的寫作者,在寫作的時候,首先自己得是舒服的,是相信的,是能夠體會到的,我沒有辦法去寫不能體認的東西,只能涉及自己共情的部份。比如我寫春藍懷孕生孩子,會直接寫結果性的感受,這個孩子帶給了她什麽?讓她生二胎,她會怎麽應對?
但是她懷孕過程中孕吐之類的感受,我實在拿不出自己的經驗往上貼,那為什麽要寫呢?這一部份留給真正能體驗到的人去寫就好了。
【雪春秋】裏,女性是我的寫作課題,這三個女孩都是以我的判斷和感受去寫的。雖然不可能完全進入其中,但我有一種寫作者的盲目自信, 我就是寫人而已,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我只寫我能體認的人。
在寫到具體情節的時候,會慢慢地感受到你在寫的是另一個性別,是女性,你平常不會在那個位置上去看世界。波伏娃寫的【第二性】,我一直沒看,但是我覺得這個題目一定包含了很多內容,只有在真的進入這種位置的時候,你才能感受到為什麽是第二。

【東京女子圖鑒】
看理想 :你有看過【厭女】嗎?
鄭在歡 :我是寫完【雪春秋】之後才看的,還沒看完,看的時候確實很有體悟,而且看了一些之後我才讓自己警惕起來,不能亂說話,因為有很多細枝末節的東西,很具體的話題,我沒有經歷過,你亂說,就顯得傲慢了。
我之前出書,他們來采訪,我都是很篤定地去說,我在寫什麽,寫的人是怎樣的。現在【雪春秋】裏雖然寫的都是女性,但我確實不能很篤定地說我寫的這些人,她究竟具體是什麽樣的,我只能分享我認識到、感受到的部份。
「大概是因為屋子裏全是女孩讓她放松了警惕,也可能是距離太近讓她覺得親切,她的話明顯多了起來,這才知道,說話不光是為了解決問題,也可以僅僅是為了開心。」
——【雪春秋】
看理想 :這本書裏也有一些有爭議的地方,比如在小說快要結束的時候,大雪關於婚戀的看法,還有最獨立、自由的秋榮,最後突然決定談戀愛試試。讀者們讀到這裏,會覺得有一些可探討的空間。對於爭議,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鄭在歡 :對,這些地方會被很多評論摘出來說,終究還是暴露出來了作者是個男的。尤其是面臨這個故事,作為講故事的人還是有很多局限的,很多地方不能面面俱到。
我是相信自然成長的,我肯定在成長,但也生活在自己的局限裏。對於小說的一切評論,不管好的壞的,我都沒有任何反駁。如果他們說得好,甚至對我還有啟發,就是小說很美妙的地方,透過簡單的故事,它能延伸出來新的認知,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只是情緒性的批評或者誇贊,一笑了之就好。
04.
找到舒適區
看理想 :你在後記裏寫,這部小說最初的起點是三個場景,裏面有背著麥稭的女孩,為勞作的母親送飯的女孩,刷碗的女孩。你對於這些女性的情感是怎樣的呢?
鄭在歡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很多次都能感受到那種反抗性的、壓抑的力量,也確實是因為這些女性有壓抑才有釋放。
平時我們能寫的沖突沒有那麽多,面對平淡的日常,想要寫出生活的對峙感不容易。但這三個女性是有的,她們身上有力量的積蓄和釋放。

【問題餐廳】
看理想 :寫【雪春秋】的過程會更困難一些嗎?
鄭在歡 :寫作的最大困難是要坐到電腦前,坐下之前是痛苦的,我會畏懼,擔心狀態不好。但寫作的時候不痛苦,寫【雪春秋】恰恰是我最幸福的時候。
它是一個長篇,每天寫一兩千字,跟著前面的往下寫,這變成了我那一年非常規律的日常,後來就沒有那麽規律地寫作過了。2020年寫完後,這三年我總共寫的小說也沒有超過10萬字,沒什麽心情,去年才開始恢復寫作狀態。
寫作過程中沒有困難,因為我不挑戰自己,生命那麽可貴,為什麽要強迫自己寫不熟悉、沒有感受的東西?所以只要是我寫出來的小說都不困難。
包括【雪春秋】裏的性別視角,我能意識到自己在跳過一些東西,但這不是困難,是過程中你會覺察自己身為男性在寫女性的時候,不能完全地代人物講話。有進入不了的地方,只能跳過。 不是說為了突破,非要寫不了解的東西,我不是這樣認知寫作的。
看理想 : 這很有意思,可能很多人都會想說要挑戰自我,跳出自己的舒適區,但是對於你來說這句話不成立。
鄭在歡 :我寫作目的肯定不是挑戰自己,要挑戰自己,我去做運動,去跑步,挑戰身體極限。但寫作、讀小說,恰恰應該是人類最舒服、最自由的狀態,為什麽還要挑戰自己?
一旦我看到一個作家說要突破、挑戰,我會對ta沒有什麽好感。小說不是一個工具性強的東西,我們讀小說,是因為在看故事的時候,能最大程度把自己的偏見和世俗的部份都放掉,沈浸到一個故事裏,相信講故事的人。當然期間你也可以不相信,只是大體上願意跟著走,喜歡它的口吻。

【母親 Mother】
我很喜歡民間故事,每天睡覺都要聽,因為小時候從這裏面受過益。我在鄉下長大,家庭又不幸福,我爸在廣州天橋上賣盜版書,各種型別都有,他會帶回來,也不管是不是適合孩子看,我看的書很雜,但小孩子的想象力會被激發得很徹底,感官全在這個書裏,不會分神,這太幸福了。這個幸福不是挑戰自己得來的。
雖然我十七八歲的時候,也一度想迅速知道人間的道理,後來發現,這個東西不能從小說中得到, 故事都是潛移默化的,它讓你體會時間的作用,你最後可能會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
我寫書也不是要直截了當地講一個故事,或者什麽主題道理。寫【雪春秋】,是因為有三個女孩的原型,她們彌散式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裏,組成了一兩幅畫面,這些畫面和場景會給你豐富的感受,寫小說也是因為這種感受,把它鋪陳開來,沈浸在這個狀態裏。
我最近在改劇本,一旦有甲方的時候,確實會痛苦,因為他們會有要求,而你要滿足要求。所以我一寫劇本就想寫小說,還是寫小說幸福。
看理想 :在現代文學創作中,鄉村是被忽視的部份,鄉村女性更是邊緣中的邊緣,被當作主體寫實在是太少見了。而且從市場的角度,這樣的寫作視角可能不算討巧。為什麽會選擇繼續書寫鄉村被忽視群體的故事?
鄭在歡 :我是要出生在上海和北京,也可以寫燈紅酒綠的故事。因為我有那樣的童年,有那樣的成長經歷,就會生出那樣的感受。
當我懷念過去的時候,我只能懷念農村的那些人。那裏可能有很多不堪,但它是你寄托情感的地方。 如果記憶就像杯子裏的水,我有十幾年的光陰是放在鄉村裏的,當我去喝水的時候,肯定會嘗到這些經驗。
鄉村生活匱乏,都是一些雞零狗碎,人和人的關系赤裸、互相傾軋,甚至還有很多苦難,本來各自的生活已經很累了,為什麽還要看這樣的故事?這是鄉村題材不討巧的地方。

【女人 Woman】
但這可能也是現代人才有的感覺,大家已經不太願意去關註跟自己沒那麽大關系的生活了,都在自己的舒適區裏快樂地蹦迪,我也想,所以只能在鄉間蹦迪。最近我開始寫北京了,因為確實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終於有了生活經驗和感受,才有想分享的內容。
即便鄉村的故事不討巧,沒那麽大的需求,沒那麽多人想看,對於我來講,我只能寫這個。作為寫作者,像我筆下的人物一樣,我也受困於原生環境。
看理想 :你會對書中的角色有一些不一樣的祝福嗎?
鄭在歡 :我祝大家在最大程度上保有自我的同時,能夠舒適地生活,找到自己的舒適區,安全地蹦迪。
可能現在人們的宏大追求已經不多了,就剩下安度余生的舒適感追求了。日常越來越讓人難以舒服,找到一個能釋放自己,容納浮躁的事情,是很難的。當不能去祝福大家有更大成就的時候,祝福大家有更自洽的生活。
❄ ️ 🍃 🍂


采寫:汁兒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小公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