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論】導論
作者 | (英)以賽亞·伯林
轉譯 | 胡傳勝
正文 | 20231字
閱讀時長 | 約8-10分鐘

真實存在為抽象物犧牲;個體的人在大屠殺中成為集體的人的犧牲品。
——本傑明·貢斯當,【論征服的精神】

就理性的支持者而言,忠於決定論的動機之一似乎是擔心決定論是科學方法本身所假定的。因此,斯圖亞特·漢普希爾什訴我們:
在對人的行為的研究中,哲學迷信現在很容易取代作為進步之障礙的傳統宗教迷信。在這個語境中,迷信是指這樣兩種信條的混淆:一種信條是人類不應該被當做自然物那樣對待;另一種信條是人類實際上不是自然物。人們很容易從人不應該像其他自然物那樣被操縱與控制這樣一種道德命題,轉到一種十分不同的、準哲學的命題:他們不能像其他自然物那樣被操縱與控制。在目前的這種輿論環境下,對計劃與社會控制技術的恐懼很容易被尊為一種非決定論哲學。
這段措辭強烈而謹慎的陳述,在我看來顯示了我提到過的那種有影響的、分布很廣的情感特征:如果決定論被拒斥甚或被懷疑,便危及科學與理性。在我看來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盡力去發現量的關聯與解釋並不意味著什麽東西都是可以量化的;稱贊科學是對原因的尋求(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並不等於說每個事物都有原因。我所引證的那段話至少包括三方面令人困惑的因素。
(1) 我們被告知說「一種信條是人類不應該被當作自然物那樣對待;另一種信條是人類實際上不是自然物」,而混淆這兩種信條乃是迷信。但是,除了我的如下信念以外,我還有別的理由要求「不要把人當做自然物那樣對待」嗎?這種信念就是:從某些方面(使人之為人的方面)說,人是與自然物不同的;這個事實是我的道德信念一一我不應該把人當做自然物那樣對待,即僅作為實作我的目的的手段一一的基礎; 正是基於這種差異我才認為隨心所欲地操縱、強制人們和對人們進行洗腦等等是不對的 。如果我被告知說不要把某物當做椅子,這樣做的理由肯定是基於下述事實:所說的那個物體擁有日常的椅子所沒有的特征,或者對於我或別人具有特殊的關系(一種可能被忽視或否認的特質),使得它區別於日常的椅子。除非人被認為擁有某些在自然物(動物、植物、事物)之上或之外的特征(不管這種差異自身被視為自然的還是不自然的),否則,不要把人當做動物或物體那樣看待這條道德要求就是沒有理性基礎的。我的結論是,這遠不是兩種不同命題混淆的問題,如果不至少使其中之一顯得沒有根據,它們之間的這種聯結便不可能被切斷;而且這肯定不會推動漢普希爾所談論的那種行程。
(2)至於警告不要從「人不應該被操縱與控制」的命題轉到「他們不能像其他自然物那樣被操縱與控制」的命題,更合理的說法肯定是假定:我之所以叫你不要這樣做,不是因為人不應該被如此對待,而是因為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容易被這樣對待了。如果我命令你不要控制和操縱人,不是因為我覺得既然你無法獲得成功所以不要白白浪費你的時間與精力,而恰好是因為我擔心你做得太成功,以致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一一而這種自由,要是他們能逃脫太多的控制與操縱,我相信他們是能夠保持的。
(3)「對計劃與社會控制技術的恐俱」那些相信這些力量並非不可抗拒的人可能最痛切地感受到這一點;而人們如果不願被幹涉太多,他們便應該擁有在可能的行動路線間自由選擇的機會,而不僅僅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一一去實作他們被決定了的可預測的選擇(如決定論者相信的那樣)。後一種也許是我們的實際狀況。但是如果我們偏愛前一種狀態——不管它闡述起來多麽困難——這難道是一種迷信,或是「虛假意識」的另一個個案嗎? 只有在決定論是正確的情況下才會如此。但這卻是惡性的迴圈論證。決定論本身也許就是這樣一種虛假信念一一除非接受決定論否則科學便受到危害——所產生的迷信,因此它本身就是誤解科學的本性而產生的「虛假意識」的案例,這難道沒有可能嗎? 任何學說都可能成為迷信,但我自己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說決定論與非決定論之中必定有一種是迷信或將要變成迷信。
現在轉到非哲學作者。那些強調自然科學範疇不適用於人類行為的人的著作,早已使十九至二十世紀唯物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粗糙的解決方案名聲掃地了。因此,現在對這個論題的任何嚴肅討論都必須一開始就考慮過去一十五年裏世界範圍內對這個論題的討論。當 E.H.卡爾認為將歷史事件歸因於個人行為(「傳記偏見」)是幼稚或至少是孩子氣的,認為我們的歷史著作中非人的因素越多便越科學,因此也越成熟與有效時,他就暴露了自己是十八世紀教條唯物主義的忠實——太忠實——信徒。這種學說甚至在孔德及其弟子的時代,或者說在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的時代,也沒有被當做是不容置疑的普列漢諾夫盡管非常天才,但他的歷史哲學得益於十八世紀唯物主義與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地方比得益於黑格爾或馬克思的黑格爾成分的要多。
還是讓我公平地對待卡爾。當他堅持物活論或擬人論——把人的特征賦於無生命的實體——是原始心靈的標誌時,我不想對此加以辯駁。但是將一個謬誤與另一個謬誤相加鮮能得出真理。擬人論是將人的範疇運用於非人類的範疇之謬。但是的確可能存在一個人的範疇能夠運用的區域,這就是人的世界假定惟有在描述與預測非人自然中有效的東西才必然適用於人類,假定我們據以區別人與非人的範疇因而必然是虛幻的——透過將其解釋為我們童年的畸變而予以消除——則是相反的錯誤,顛倒過來的物活論和擬人論。科學方法能夠達成的,必須用科學的方法達成。自然科學中富有成效的統計方法、電腦、任何其他的儀器或方法,只要能用於人類行為的分類、分析、預測與「返測」(retrodict),當然都應該受到歡迎;出於某種教條的理由而禁用這些方法,純粹是蒙昧主義。
不過,從這一點遠遠不能教條性地保證,一種研究主題越是能納入自然科學的範疇,我們就越能接近真理。這種學說,在卡爾那裏,等於說越非人與一般,就越有效,越普通就越成熟;越關註個人、他們的氣質與他們在歷史中的角色,就越虛妄,越遠離客觀的真理與現實。這在我看來與相反的謬誤——歷史可以歸結為大人物的生平與言行——比起來不過是半斤八兩。斷言真理存在於這些極端中間的某個地方,存在於同樣狂熱的孔德與卡萊爾的立場的中間,這可能是迂腐之論,但也有可能更接近真理。正如我們時代的一位傑出哲學家,曾經冷冰冰地指出的,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假定說真理,當其被發現的時候,會是有趣的。當然,真理也不一定就是令人吃驚的和顛覆性的;它可能如此也可能並不如此;我們難以說清。
這不是個詳細檢視卡爾的歷史著述觀的地方,他的那些觀點在我看來散發出理性時代最後的魔法氣息,比理性主義還要理性主義,帶著所有令人羨慕的簡單、明晰,擺脫了這一思想領域甚至在伏爾泰與愛爾維修處於頂峰的燦爛開始時代就具有的懷疑與自我質疑的特質;在此之前,德國人以其特有的鑿通一切的熱情,淪陷了平滑的草地和對稱的花園。卡爾是一個精力充沛和令人愉快的作者,雖然受了點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但基本上是一個過時的實證主義者,處於奧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賓塞與 HG威爾斯的傳統之中;他是聖伯夫所說的un grand simplificateur」(一個大簡化者)從不為自赫爾德和黑格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起就一直折磨著這個學科的那些問題與困難煩心。他對馬克思尊敬有加,卻遠離他的復雜洞見:他是一個走捷徑的大師,是為那些巨大而無法解決的問題提供最後答案的人。
但如果我在這裏無法詳盡地討論卡爾的立場,我至少也能夠試圖回應他對我的觀點的一些最嚴厲的指責。他對我的最嚴重的指責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我相信決定論是錯誤的並且拒絕任何事物都有其原因這條公理,而這條公理,按照卡爾的看法是我們有能力理解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的條件」;第二,我強烈堅持「譴責查理曼、拿破侖、成吉思汗、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屠殺」也就是說,裁定歷史上重要的個人的道德行為,是歷史學家的責任;第三,我相信歷史學中的解釋是一種根據人類意圖所作的解釋,對此,卡爾提出相反的「社會力量」作為替代概念。
對於所有這些指責,我只能再一次重復: 第一 ,我從未否認(也從未想到過)這樣一種邏輯可能性:有一些版本的決定論在原則上(雖然,也許僅僅在原則上)可能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有效理論;我也從不堅持說我已經駁斥了它。我惟一爭辯的是,對決定論的信念是與深嵌在我們普通人與歷史學家的正常言說與思考中的信念不相容的,至少在西方世界如此;因此嚴肅對待決定論必然導致這些核心觀念的根本修改,一種無論是卡爾還是其他的歷史學家在其實踐中都沒有提供明顯例證的劇變。我不知道有支持決定論的最終論據。但這不是我的觀點。我的觀點是,正是決定論支持者的實踐,以及這些支持者在這方面要勉強面對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會使他們付出代價;這恰好表明,這種理論支持在目前無法被嚴肅對待,而不管誰聲稱提供了這種支持。
第二, 我被指控要求歷史學家進行道德說教。我從沒做過這種事。我只是堅持,歷史學家(其他人也一樣)所使用的語言不可避免地滲透著帶有評價性力量的言詞,而讓他們凈化他們的這種語言等於讓他們完成一項異常困難也是自我愚弄的任務。當然,就像任何希望在某個領域建立真理的人一樣,客觀不帶偏見、不動情無疑是歷史學家的美德。但是歷史學家也是人,他沒有義務在更大的程度上比其他人非人性化(dehumanise);他們選樣討論的主題以及他們對註意力與著重點的分配都受他們自己的價值天平的引導,而如果他們想理解人的行為或想與他們的讀者交流他們的看法,他們的這種天平便不應該與人們共享的價值觀相去太遠。
當然,理解他人的動機與觀點並不必然分享這些東西;洞察力並不包含贊同;最有天賦的歷史學家(和小說家)也是最少偏袒的;與題材保持某種距離是需要的。但是,雖然對動機、道德、社會法規以及整個文明的理解並不需要接受甚至同情它們,這種理解也需要以「哪些價值對這些個體或群體是重要的」這一看法為前提,即使這些價值可能被發現是令人厭惡的。而這種理解依賴於一種有關人性和人的需要的觀念,這種觀念進入歷史家自己的倫理、宗教或美學視野中。價值,特別是制約著歷史家搜集事實的那些道德價值,以及他們在其中展示這些事實的眼光,被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傳達出來,而且是不自覺地被傳達出來,正像它們同樣被任何一個試圖理解與描述人類的人傳達出來一樣。我們用於判斷歷史學家著作的標準,原則上並非也不需要不同於那些我們借以判斷其他研究與想像領域的專家的標準。在批評那些處理人類事務的作者的成就時,我們不可能將「事實」與其意義斷然分開。「價值進入事實並成為其組成部份。我們的價值是我們作為人的那些配置的基本成分。"這些話不是我說的。說這些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卡爾自己(讀者對此一定大吃一驚)。我原本是能對這個命題作不同闡述的,但我覺得卡爾的話已經足夠了。我想用他自己的話來反駁他對我的指控。
很明顯,歷史學家沒有必要像卡爾錯誤地認為我希望他們做的那樣,去正式地聲明他們的道德判斷。作為歷史學家他們沒有義務告訴讀者希特勒危害了人類,而巴斯德有益於人類(或者無論他們舉什麽例子)。正常語言的使用本身不可能不透露作者關於什麽是常規什麽是反常、什麽是重要什麽是瑣碎、什麽令人喜歡什麽令人沮喪的想法。在描述已發生的事情時,我可能說成千上萬人被殘酷處死;或者換一種說法,說他們遭受淪陷、犧牲生命、被屠戮;或者簡單地說歐洲的人口減少了,人口的平均壽命降低了,許多人失去了生命。所有這些對已發生的事情的描述沒有一個是完全中性的:它們全都攜帶著道德含義不管他多麽小心地使用純粹描述性的語言,歷史學家之所言遲早會傳達他的態度。超脫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立場。使用中性語言(「希姆萊使好多人窒息而死」)本身便傳達著自己的倫理語氣。
我並不是說關於人類的嚴格的中性語言是無法獲得的。統計學家、情報編輯者、研究部門、某種型別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官方記者、旨在向歷史學家或政治家提供數據的編輯,都可能並被期望接近這種中性語言。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行動並不是自主的,而是被指派向那些以自身工作為目的的人,如歷史學家和活動家,提供素材。研究助理並不要求去選擇和強調人類生活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歷史學家無法避免這點否則,他寫出的東西將會與他、他的社會或別的文化視為中心或邊緣性的東西毫無關系,因而也不再成為歷史。如果歷史就是歷史學家提供的,那麽任何一個歷史學家都不能逃脫的核心問題便是(不管他是否意識到):我們(以及其他社會)是如何到達今天這個境地的。這個核心問題 eo facto(實際上)必然要求對社會、人的性質、人的行為的根源、人的價值與價值尺度有某種特殊的洞見,而這種洞見卻是物理學家生理學家、體質人類學家、語法學家、數量經濟學家或某種型別的心理學家(例如為別人的解釋提供資料的人)能夠避免的。歷史學不是附內容活動它試圖為人的行動與苦難提供盡量完整的描述;稱人類為人就是把我們能夠辨識出的那些價值賦予他們,否則對我們來說他們就不是人。因此,對於什麽重要、在多大程度上重要這些問題,歷史學家(無論他做不做道德說教)沒有辦法不采取某種立場,這就足以使得「價值中立」的史學觀念,即歷史家是 ipsis rebus dictantibus的抄寫者觀念,成為一種幻覺。
這也許就是阿克頓強烈反對克雷頓的理由:並不盡因為克雷頓使用人為的非道德詞匯,而是因為他在使用這些詞匯描述博爾吉亞家族及其行為時,實際上為他們進行了開釋;不管他做得對還是不對,他還是這樣做了;中立也是一種道德態度,而且認識到它的這種本性也是一種道德態度。阿克頓堅信克雷頓是錯的。我們可能要麽同意阿克頓要麽同意克雷頓。但無論我們站在哪一邊,我們都在陳述與傳達(即使我們寧願不直陳)一種道德態度。讓歷史學家描述人的生活,卻又不根據穆勒所說的人的永恒利益來描述他們生活的意義,無論作何理解,都構不成對其生活的描述。要求歷史學家嘗試想像性地進入其他人的經驗卻又禁止他們表現道德理解,這是讓他們只陳述他們所知道的一小部份,而剝奪他們工作的人性含義。事實上這是我對於卡爾那種反對道德說教的壞習慣的道德說教所要說的一切。
毫無疑問,下述觀點仍然是值得討論的:存在著客觀、永恒且普遍的道德與社會價值,不受歷史變遷的影響,任何一個理性之人的心靈只要選擇正視它們便可以接近它們。不過,理解某人自己時代或其他任何時代的人的這種可能性,以及人類不同部份之間交流的可能性,依賴於某些共享價值的存在,而不僅僅依賴於共有一個「事實的」世界。後者是人類交往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條件。那些與外在世界隔離的人被描述為反常的,或者在某種極端的場合,被描述為神經錯亂的。同樣的情況——這正是問題癥結之所在——也適用於那些遠離共享的公共價值世界的人,一個人宣稱他曾經知道好壞之分卻又說自己忘掉了它們,這樣的人是不足為信的,如果他可以信賴,也應該被恰當地認為是精神不健全的。但是這種情況也適合於這樣一種人,他不單不贊成、欣賞或寬容,而且事實上無法理解其他任何人都可能會有的反對意見,例如,對於毫無理由地屠殺任何藍眼睛的人的法令的反對。他也授權以算作心智不全的人的活標本,這樣的人算起來可能不足六人,或者想想大概也就只有愷撒之類。對這樣一種錯亂的標準(而不是描述性)檢驗,所依賴的是什麽給予諸如自然律這樣的學說以可信性,特別是在那些拒絕給它們以任何先驗地位的版本中。對共享價值的接受(至少對其不能再少的最小部份)進入我們對於正常人的理解之中。共享的價值能將關於人類的道德基礎的概念與諸如習俗、傳統、法律風俗、風尚、禮儀的概念區分開來。有了這些價值,所有這些廣泛的社會歷史、民族、地變異數異與變化,便不再被視為奇怪或反常的、極端自我中心不健全或根本不可取的;更不會被認為在哲學上是有問題的。
任何一種高於純粹編年記述、涉及選擇與重點的不平等分配的歷史著述,都不是全然 wertfrei的。那麽是什麽把被正當地譴責為說教的東西與那種似乎無法逃脫的對人類事務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區別開來呢?並不是它的公開性:在不贊成作者觀點的人眼中,僅僅從表面上選擇中立語言可能顯得更具說教性不過是更內在一些而已。在論歷史的不可避免性的文章中,我想我已經討論了偏見與私心的含義。我只能重復說我們只能根據與那些被傳達的,人類共通的核心價值的接近程度來區分主觀的贊賞與客觀的贊賞,也就是說,出於實際的目的,根據與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地點與絕大多數時間內共享的那些價值的接近程度來區分。很明顯這不是絕對和嚴格的標準;存在著變數因此存在著不能忽視的(和明顯的)民族的、地方的、歷史的特殊性,存在著偏見、迷信、文飾以及它們的非理性的影響。但是這個標準不全然是相對和主觀的;否則,人的概念將變得太不確定,面被無法溝通的規範性差異所分裂的人與社會,就會全然無法越過時空與文化距離而溝通。
道德判斷的客觀性似乎依賴於(幾乎是存在於)人類回應的持久程度。這個觀念從原則上說不能被弄得太尖銳和不可更改。它的邊緣仍然是模糊的。道德範疇以及一般的價值範疇遠不像關於物質世界的知覺那樣堅實與難以磨滅,但是它們也不像有的作者在對抗經典的客觀主義教條時常常假定的那樣相對與流動。最小量的、共享的道德基礎,即相互關聯的概念與範疇,對於人類的交往來說是根本性的。不管它們多麽易變,也不管它們在什麽力量的影響下會作多大改變(這些是經驗問題)在道德心理學、歷史學與社會人類學的領域內,這些範疇是什麽,乃是有趣的、重要的和沒有得到充分探討的問題。在我看來,做出再多的要求便超出了可交流的人類知識之外。
第三,我被指控假定歷史學處理人的動機與意圖,面對於這些東西,卡爾希望代之以「社會力量」。對這個責難我表示服罪。我必須再說一遍,任何人只要討論的是人,就註定要考慮動機目的、選擇以及專屬人類的特殊人類經驗,而不是只考慮在有感覺、有生命的人類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尤視非人因素的作用,無視無目的的人類行為後果的影響,無視人常常不能正確理解他們自己的個體行動及其根源這個事實;在解釋事件的發生及如何發生時在非常字面與機械的意義上不作更深的因果性探究——所有這些都是荒謬地幼稚與瑣碎的(不要說蒙昧主義了),我從不主張如此。但是無視動機產生的背景以及動機在行動者面前展開的可能範圍(它們絕大多數從未實作,有些則根本無望實作),無視人類——在我看來他們的世界他們自身以及他們的眼界與價值(幻覺連同其他一切)只能根據他們白身來理解——思考與想像的廣度,就不再存在歷史著述。在形成事件的過程中,這個或那個人的個人影響到底有多大作用,我們也許會對此爭論不息。但是試圖將個人行為歸結為那些非人的「社會力量」的行為(它們是不能進一步分析為馬克思所說的創造歷史的個人的),乃是統計學的「物化」,一種官僚與管理者的「虛假意識」,這些人無視所有不能量化的東西,因此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非人道的。
藥方會引起新的疾病,而不管這些藥方能不能治愈它們正在治療的疾病。對人類說他們是他們很少或無力控制的非人力量的玩物,以此來恐嚇人類,縱然詭稱為了殺死別的虛構之物——超自然力量、全能的個人與看不見的手等等觀念——也不過形成了新的神話而已。這等於是虛構實體,宣傳對事件的不可改變的模式的信念,而對於這些模式,經驗的證據至少是不充分的;這種做法雖然放松了個體的人格責任的重擔,卻在一些人當中產生了非理性的被動性,並在另一些人當中產生了非理性的狂熱的主動性;因為沒有什麽東西比這樣一種確定性更激動人心:星辰都為自己而戰,「歷史」、「社會力量」和「歷史潮流都站在自己一邊,背負著自己向上、向前對這樣一種思考與說話方式進行揭露,是現代經驗主義的大成就。
如果我的文章有什麽論戰鋒芒的話,那就是對諸如此類的形而上學構造物的不信任。談論人卻僅僅根據統計機率而無視人之為人的特殊性一一評價、選擇、不同的生活見解——乃是對科學方法的誇張的使用,一種沒有道理的行為主義,其誤入歧途的程度不亞於訴諸想像性的力量。前者有其地位;它描述、分類、預測,即使並不做出解釋。後者雖然解釋,但是以一種超自然的,我稱之為新物活論的詞匯來解釋。我懷疑卡爾維護這些方法時從不感到於心不安。但是在他對 naivete(天真)、矯矜、民族主義、階級、人格說教的空洞的反駁中,他放任自己駛達另一極端一一非人格的黑夜,人類在其中被分解為抽象力量我對這種力量的激烈反對導致卡爾認為我贊同相反的荒謬極端。他的這種假定,即只能在這些極端中選擇其一,乃是一種基本的謬誤,而他(還有別人)對我的真實的與虛構的觀點的激烈批評,全都源自這個謬誤。
在此我想再一次重復我從未放棄的一些基本觀點:因果律是可以運用於人類歷史的(對不起卡爾,我認為否定這個命題就是心智不健全);歷史並不主要是個人意誌間的「劇烈沖突」知識,特別是那些在科學上已經確證的規則,會使我們更有效率並擴充套件我們的自由,這種自由易於被知識所培育的無知、覺、恐懼與偏見所遮蔽;許多經驗證據表明,自由選擇的疆域遠比過去許多人假定的要狹窄,現在也許還有人錯誤地相信這個疆城很大;歷史的客觀模式,在我看來,甚至是可以辨識的。我必須重復,我惟一關心的是申明,除非這些規律與模式容許某種自由選擇,而且不僅僅是那種其本身完全由前在條件決定的選擇所決定的自由行動,否則,我們就必須重建我們相應的現實觀;這項任務比決定論者認為的要更為艱難。
決定論者的世界,至少在原則上,是可以理解的:在其中,厄尼斯特·內格爾所謂的屬於人類意誌力的作用的一切將仍然是完整的;人的行為將仍然受道德煲貶的影響,而他的新陳代謝(不管怎麽說)則不直接受這種道德褒的影響;人們將繼續按美醜來描述人與事,按有益與有害勇敢與怯懦、高貴與渺小來評價行動。但是康德說,如果支配著外部世界的現象最終支配著存在的一切,那麽道德——在他的意義上——便會被廢止另一方面,在論及道德責任觀念所假定的自由概念時,康德采用了非常激烈的手段來拯救這種觀念。我覺得康德至少顯示了他對至關重要的東西的深刻把握。他的解決是不清楚的,也許是站不住腳的;但是盡管這種解決遭到拒絕問題依然存在。在因果性地決定的系統中,通常意義上的自由選擇與道德責任觀念便不復存在了,至少是沒有用了。行動的觀念也將不得不重新考慮。
我認識到這個事實:有些思想家在解釋諸如責任有罪性自責等概念與嚴格的因果決定相一致時,似乎沒有任何理智上的不安。他們至多把持不同意見者的抵制解釋為將因果性與某種強迫相混淆了。強迫挫傷我的願望,但是當我滿足這些願望時,我肯定是自由的,雖然我的願望本身是因果性地被決定的;如果它們不是如此,如果它們不是我的一般傾向或我的習慣因素或生活方式的結果(它們可以用純粹的因果性詞匯來描述)。或者,如果這些願望不完全出自物理的、社會的或心理的原因那麽,肯定存在著一種打破因果鏈的純粹機會或隨機因素。是(論證繼續)隨機的行為難道不正好是自由、合理性與責任的對立物嗎?而這些選擇項似乎已經窮盡了所有可能性。沒有原因的選擇,這種觀念就像某種從虛無中產生的東西,肯定是無法令人滿意的。但是(我不需要再作論證)這些思想家所容許的惟一候選方案一一因果性的選擇包含著責任、功過等等——同樣是無法接受的。
這個困境在兩千多年裏使思想家們陷入分裂。有些人仍然受其折磨或至少感到困惑,就像早期斯多噶派一樣;其他人則覺得什麽問題也沒有。它有可能,至少部份地,起源於將機械模式運用於人的行動;在一種場合,選擇被理解為因果系列中的紐帶,這種因果系列的典型情形便是機械過程的做功:在另一種場合,即系列中斷的情況下,仍然用高度復雜的機械論來解釋。沒有一種圖景能很好地切合於實際情況。我們似乎需要一個新的模式、一個圖式,把明顯的道德意識從強迫性的傳統討論的構架所提供的普羅克汝斯忒斯之床中拯救出來。打破舊的、阻塞性的類比或(用一個熟悉的詞)不適當的語言遊戲規則的所有努力,至此都是不成功的。這需要至今尚未出現的第一流的哲學想像。懷特的辦法一一將觀點的沖突歸結為價值的不同尺度或道德用法的多樣性一一在我看來並不是出路。我不禁懷疑,他的觀點是更大的理論的一部份,按照這種理論,對決定論或者任何別的世界觀的信念,都是或都依賴於某種大範圍的、關於如何處理思想或經驗之某一領域的實用決定progmatic decision),這種決定的觀念基礎是:哪一套範疇能產生最好的結果。縱然我們接受這個觀點,也難以協調諸如因果必然性、可避免性、自由選擇、責任等等觀念。我並不聲稱我駁倒了決定論的結論:但是我也看不出我們為什麽非得接受這些結論。無論是諸如此類的歷史解釋觀念,還是對科學方法的尊敬,在我看來都不必然蘊含著這些結論。
以上說法概括了我與厄尼斯特·內格爾、莫頓·懷特、E.H卡爾、古典論決定者及其現代弟子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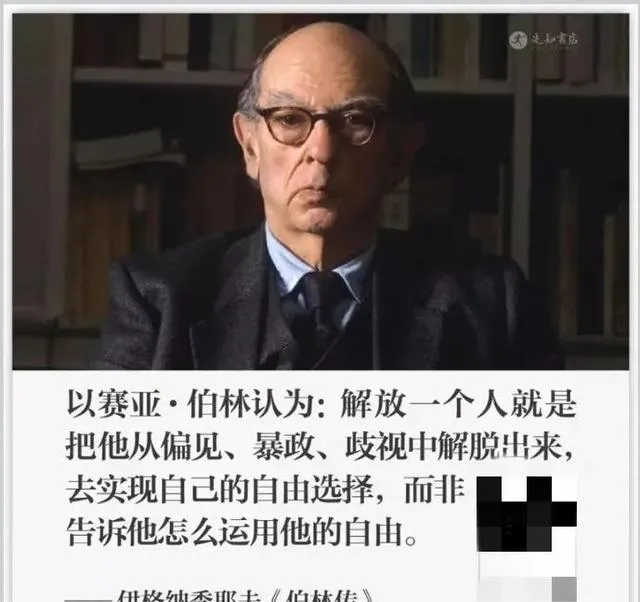
本文節選自:
自由論
/(英)伯林(Berlin,1.)著
胡傳勝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3.12
書名原文:Liberty
ISBN 7-80657-653-3
部份內容由編者整理,註釋從略。
本文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於商業用途。如對本書有興趣,請購買正版書籍。
#自由 3個
#以賽亞·伯林 2個
#【自由論】 2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