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人類學家特雷莎·麥克費爾是一名過敏癥患者,她的父親死於蜜蜂蜇刺引起的嚴重過敏反應。
目前,全世界有數十億人患有某種形式的過敏癥,據估計占全球總人口的30%~40%。
過敏並不一定致命,但會帶來沈重的負擔。多年遭受過敏困擾的人花費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而且時常需要集中精神關註自己的癥狀。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但即使如此,有時也很難忽視過敏帶來的影響。一個吸入花粉的糟糕日子、一塊發紅發癢的皮膚、一場聚會……都有可能帶來麻煩。
究竟什麽是過敏?為什麽我們會過敏?為什麽過敏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嚴重?關於過敏,我們能做些什麽,還不能做到什麽?
顯然,我們的身體對每天接觸到的大量天然和人造過敏原越來越敏感了。在【過敏的真相】一書中,麥克費爾展開了一場對過敏的科學探究之旅,嘗試解開過敏謎團。
以下內容節選自【過敏的真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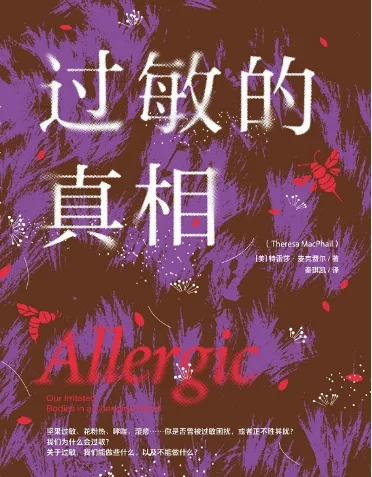
【過敏的真相】,特雷莎·麥克費爾 著,秦琪凱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4月版
如何準確計量過敏狀況的發生率?
過敏從來都不是表面看起來的那樣。它們難以確定,很難診斷,更難衡量。
準確計量過敏狀況的發生率很重要。在醫學研究中,從資助分配到新藥開發,數位驅動著一切。為了開始理解這個問題可能有多嚴重,以及為什麽過敏可能是21世紀的主要慢性疾病,我們必須一頭紮進統計數據的海洋。以下是從一些最新數據中挑選出來的內容,它們凸顯了當今過敏是多麽普遍和廣泛。
•全球估計有2.35億人患有哮喘。
•在全球範圍內,2.4億~5.5億人可能患有食物過敏。
•藥物過敏可能影響到全球10%的人口和20%的住院患者。
•世界上10%~30%的人口患有花粉熱。
•20%~30%的印度人至少患有一種過敏性疾病。
•33%的印度人受到呼吸道過敏的影響。
•1.5億歐洲人被某種形式的慢性過敏困擾著。
•50%的烏幹達人患有過敏癥。
•7.7%的中國兒童受到食物過敏的影響。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數位令人難以置信,但我們每天都能看到這樣的數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在新聞提要中看到表格、圖表、調查結果和百分比,事實和數位每時每刻都在吸引著我們的註意力,淹沒我們,麻痹我們,令我們感到不堪其擾。
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數據、全球科學和Excel電子試算表的時代,曾有人說過:「如果只有一個人死於饑餓,那是一場悲劇;如果數百萬人死於饑餓,那只是統計數位。」如果我們把這個邏輯運用到現代醫療的領域,也許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為什麽我們沒有對這些驚人的比例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只有一個孩子死於花生過敏或嚴重過敏性哮喘發作,那是一場悲劇;如果有數百萬人患有食物過敏或哮喘而沒有死亡,那就只是統計數位了。雖然像這樣的大量數據也許能夠告訴我們全球過敏問題有多嚴重,但它們並不能告訴我們所有人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紀錄片【過敏世界】(2008)劇照。
我們很難想象構成所有數據的要素正是過敏癥患者日復一日共同面對的掙紮。個人的故事,比如我父親的、我的,也許還有你的,往往會被遺忘。重要的細節和背景資訊——數十億過敏癥患者的生活經歷,都從數據集中消失了。
以維羅妮卡為例,她是一個30歲出頭的活潑女人,她的呼吸過敏癥狀非常嚴重,嚴重到她會害怕看見春天到來的跡象。隨著氣溫變暖,綠芽從地下冒出來,白天逐漸變長,樹木發芽——如果維羅妮卡沒有盡早開始服用治療過敏的處方藥,所有這些變化都會給她帶來災難。由於變幻莫測的氣候變遷,她每年越來越像在做一場猜謎遊戲:春天什麽時候會到來?維羅妮卡試圖在春天來臨前的三四個星期預約她的主治醫生。然而,即使她把每件事都安排得恰到好處,她的過敏情況也仍然不可預測。如果這是一個特別嚴重的花粉年——花粉濃度明顯更高或者花粉季比平時更長,即使維羅妮卡服用了抗組織胺的處方藥,她也會受到影響。
一天下午,我們舒舒服服地坐在她的辦公室裏,她向我解釋說:「步行去上班時,我必須確保自己戴上緊貼式太陽鏡。眼睛是我的觸發點。如果忘記戴眼鏡,我看起來就會像哭過或者通宵參加了派對。不管怎麽說,這個樣子都不適合上班。」
每天,維羅妮卡回家後都會淋浴,洗掉頭發上的花粉,花粉濃度可能特別高的日子裏她會避免戶外活動,而且每年有三四個月她會感到身體疲憊。當我問她的丈夫、朋友和家人是否理解時,她點點頭說:「我們全家都有過敏癥,所以他們都懂。每個人都在服用氯雷他定片或鹽酸非索非那定片或鹽酸左西替利嗪片之類的藥物,所有人都在吃藥。」她說,最近每個人的過敏癥似乎都越來越嚴重了。只要她的抗過敏藥一直有效就沒事。但她擔心的是,當最好的處方藥都不再有效時,她會怎麽樣。
情況是否變得更糟了?
當我第一次開始檢視統計數據時,我感到不知所措和困惑。官方數據究竟是基於什麽統計的,為什麽它們經常變化,或許這反映了可能性的範圍之大?顯然,所有的統計數據都是估計得出的。它們是根據較小的、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量計算出來的。但我想了解更多細節——誰在做抽樣調查以及如何做抽樣調查,所以我聯系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試圖找到一些答案。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會跟蹤調查哮喘和食物過敏的發病率,因為這是兩種最致命的過敏性疾病,最有可能導致美國人的死亡。然而,在與工作人員打了幾輪電話和發了幾封電子信件後,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在做了更多的跑腿工作以及對過敏研究人員進行更多的采訪之後,我意識到,要確切地知道有多少人被過敏所困擾,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對於這一每個人都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我們同樣很難給出明確答案:情況是否變得更糟了?
這是我自己被診斷出過敏癥並開始和別人談論他們各自的過敏癥後,最迫切地想知道答案的問題之一。過敏癥專家、醫療保健提供者、醫藥和生物技術公司、不過敏的公民、像維羅妮卡這樣的過敏癥患者(很可能還有你),關心這些問題的讀者,都想知道如今過敏是否比過去更普遍,在可預見的未來,過敏率是否會繼續上升?是否所有的數據都比10年前、20年前或30年前更糟糕?過敏率真的在10年接10年地上升,還是新的公共衛生意識運動和更準確的診斷工具令我們更善於發現和診斷過敏,從而使得數位激增?生活在21世紀的人更容易患過敏或更頻繁地經歷過敏,並且癥狀更嚴重嗎?

紀錄片【過敏世界】(2008)劇照。
我花了5年多的時間研究和撰寫這本書,閱讀了過敏癥的歷史,采訪了過敏癥專家,參觀了研究過敏癥的科學實驗室。我問遇到的每一個人,他們是否認為過敏在普通人群中變得越來越普遍,在癥狀上變得越來越嚴重。幾乎所有人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然而,他們也提醒說,我們剛開始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過敏,目前擁有的數據還沒有達到它可以或應該達到的水平。
在這個領域工作了幾十年的過敏癥專家都告訴我同一件事情:很難準確地評估目前的情況,因為很難獲得關於過敏癥患者數量的可靠數據。一方面,我們有無數患有不同形式過敏性疾病(濕疹、哮喘、花粉熱、食物過敏)的人的個人敘述,以及醫生或過敏癥專家的臨床記錄和診斷。另一方面,我們有經組譯和制表的官方統計數位。如果你深入研究這些流行病學數據,很快你就會發現一些明顯的問題。
首先,什麽是過敏,或者更重要的是,什麽不是過敏,這個定義會影響人們的統計方式,從而影響統計的準確性。疾病類別並不是世界上穩定的實體或「事物」;它們是對疾病典型癥狀和生物體征的集合的描述,甚至一些看似「容易」定義的東西——比如哮喘,也比乍看起來要復雜得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哮喘的正式定義已經變了許多次。流行病學研究並不總是使用相同的疾病標誌物,因此在一項研究中被列入哮喘患者的人在另一項研究中可能不符合哮喘的條件。
在一項薈萃分析中,研究人員發現,122項關於兒童哮喘患病率的研究沒有使用標準化的定義或哮喘癥狀,這使得數據無法組譯或比較。事實上,這122項研究使用了60種不同的哮喘定義。如果將最流行的4種定義套用於同一組數據,那麽可被歸類為「哮喘」兒童的人數的差異將令人震驚。由於使用的定義不同,會有比例高達39%的兒童從患有哮喘變為沒有哮喘。
那麽,這些研究中的孩子到底有沒有哮喘呢?這由誰來決定?是目睹孩子在操場上輕微喘息或睡前呼吸困難的父母?是會記錄家族史,然後用肺活量計來測量小病人肺功能的兒科醫生?還是檢視哮喘保險理賠數據、吸入器處方數量,或者18歲以下兒童的父母自述調查數據的流行病學家?這就是眾多過敏癥患者的流行病學數據如此難以收集、解釋和書寫的原因。
辛辛那堤兒童醫院的內科醫生、哮喘研究人員庫拉納·赫爾希博士擁有數十年的經驗,她向我解釋了過敏性哮喘為何如此難以追蹤。「哮喘是一個垃圾術語,」她說,「它是一種癥狀的名稱,而不是一種疾病。哮喘是異質性的。它由一大堆的癥狀定義,可能由不同的途徑引起。」換句話說,許多不同的醫學狀況都可能導致哮喘反應,而不僅僅是過敏。庫拉納·赫爾希解釋說,這使得具體地測量過敏性哮喘很難,將過敏與哮喘的其他原因(如運動或其他肺部疾病)區分開來也很難。更復雜的是,過敏即使不是患者哮喘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觸發哮喘的環境因素。除非你檢視每一個病人的病史,否則你不可能分辨出誰是「過敏性」哮喘,誰是有過敏誘因的「非過敏性」哮喘。
而且,不僅僅是哮喘的問題。用於編制全球過敏率官方數據的過敏的定義幾乎全部是模糊的、有爭議的、不斷變化的。令人驚訝的是,花粉熱這種醫學上公認的最古老的過敏癥,比人們最初想象的要難定義得多,用於判斷它的癥狀可能差別很大。即使研究是嚴格的,即具有臨床試驗或官方診斷的才能被確診(大多數都沒有),得出的數位也仍然取決於研究人員最初如何定義疾病類別。說得委婉點兒,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困惑和沮喪,往往會導致過敏癥患者的官方數據出現很大的差異。
這裏有一個相關的例子,說明要得到更精確的數位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在流鼻涕、打噴嚏或其他方面受到刺激是多麽困難。過敏性鼻炎患者占世界總人口的10%~40%。在全球範圍內,10%和40%這兩個比例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就像增加或減少整片大陸的人口一樣。這種巨大差異背後的原因包括對花粉熱的定義不同、個人和全國調查中用於評估病情的診斷標準(如流淚或頻繁打噴嚏)不同,以及被測量的受試者群體不同(正在編制的調查數據中社會經濟群體和地理區域的不同)。

紀錄片【過敏世界】(2008)劇照。
首先,並不是所有患花粉熱的人都接受了測試,自我診斷的人並沒有反映在官方數據中。即使患有過敏性鼻炎的人去看醫生,他們也可能不會得到正確的診斷。此外,並不是每個有過敏癥狀的人都知道自己有過敏癥,或者會被認為是過敏癥患者,特別是癥狀輕微或很少接觸過敏原的患者。我父親不知道自己對蜂毒過敏,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呼吸道過敏,我們倆都不會在家族病史中「過敏」旁邊的方框上打鉤,也不會在關於過敏的調查問題上回答「是」。而這通常是我們收集過敏率數據的首要方式——直接詢問人們或調查他們的癥狀。
這是目前過敏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大多數關於過敏的流行病學研究都是基於透過網路或電話調查自述癥狀完成的。我們依靠過敏癥患者準確評估自己的癥狀並如實報告,然後把他們的回復分到正確的類別中並進行統計。這種方法的一個明顯問題是,過敏的癥狀往往與其他疾病的癥狀相似或完全相同,因此可能會令人困惑。自述癥狀充其量只能證明病人可能有潛在的過敏情況。如果沒有醫學診斷,自述癥狀本身不能用作確認真正的過敏反應的依據。
過敏在過去幾十年裏變得更嚴重了
盡管研究人員可能在定義、癥狀和方法上存在分歧,但他們都同意一件事:過敏在過去幾十年裏變得更嚴重了,全世界過敏癥患者的數量可能會繼續快速增長。看看我們從20世紀獲得的數據,有一個共識是,美國的花粉熱發病率在20世紀中期有所上升。數據顯示,哮喘的發病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增加,並在90年代達到頂峰。從那以後,哮喘的發病率一直保持穩定。
就呼吸道過敏性疾病和特應性敏感(皮膚過敏)而言,過去幾十年的患病率可能有所增加,而且其地理差異逐漸縮小。例如,1993—2003年,加納的特應性疾病發病率翻了一番。在食物過敏方面,全球發病率的上升是最顯著的,這一趨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此後發病率一直穩定增長。
史考特·西歇雷爾博士是艾利洛和羅斯林·賈菲食物過敏研究所的主任,也是紐約市西奈山伊坎醫學院兒科過敏癥教授,親眼見證了食物過敏情況的增多。1997年,當他開始在賈菲研究所工作時,他的團隊與「食物過敏和嚴重過敏反應網路」組織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每250名兒童中就有1人報告對花生過敏。到2008年,西歇雷爾的研究表明,這一比例增加了兩倍多,達到1/70。

紀錄片【過敏世界】(2008)劇照。
「一開始,我並不相信2008年的研究。」最初,西歇雷爾認為這個比例反映了研究方法存在問題——直到他看到加拿大、澳洲和英國的類似數據,這些數據都表明大約1%或更多的兒童對花生過敏。如今,西歇雷爾毫不懷疑,過敏的發病率在過去幾十年裏有所增長。「我們也看到食物過敏的情況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來越多。」西歇雷爾說,「食物過敏的嚴重程度可能與20年前沒有什麽不同,但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大問題。」
雖然所有這些數據都是令人信服的,但在過去30年裏,我們所掌握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可能是住院人數。每兩個小時,就有一個嚴重過敏的人被送進急診室。這些數位似乎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過敏性疾病的問題正在擴大。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在過去20年中搜尋了可獲得的數據,根據他們的研究,食物過敏住院人數增加了5.7%(1998—2018年),而死亡率從0.70%下降到0.19%。
在同一時期,腎上腺素自動註射器(Epi Pen)的處方增加了336%。研究人員控制了食物嚴重過敏反應的定義和標準的變化,他們認為,在總體發病率上升的情況下,食物過敏診斷和管理的改善導致了死亡率的下降。在20世紀70—90年代之間的短短20年間,因哮喘住院的人數增加了兩倍,直到今天才趨於穩定。
盡管已開發國家的哮喘發病率增長趨勢一直在放緩,在美國等地哮喘發病率保持不變,但在世界上的不發達地區,哮喘發病率仍在繼續攀升,導致全球總體發病率繼續上升。

紀錄片【過敏世界】(2008)劇照。
這就是為什麽專家預測過敏率將在未來幾十年繼續上升。過敏性疾病在低收入國家的農村地區不那麽普遍,但過敏性敏感處於同一水平(提醒:你可能有敏感性,但不會發生過敏)。換句話說,各地的人都有相同的敏感性,但在貧窮國家的農村地區,活動性癥狀和活動性疾病的病例較少。隨著國家發展程度提高,過敏率往往會上升。為什麽會這樣?
原文作者/特雷莎·麥克費爾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