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向陽/文 1901年,故國值多事之秋。一年前的1900年7月28日夜,鼓吹革命立憲、謀劃成立「中國國會」的湖南人唐才常在漢口舉兵事敗,被張之洞戮首於武昌大朝街紫陽湖畔。與唐才常一同赴難的共11人,唐的首級被高懸漢陽門,以儆效尤。
更早前的1900年3月,義和團謀動於北方,5月殺戮日使館書記杉山彬。此後,燒教堂、殺教民和誅殺無辜,成了義和團的常規套路。清廷在5月份接連舉行了4次禦前會議,定下了「利用拳匪以制洋人」的調門。唐才常們正是以反對清政府引義和團排外為名,發起「勤王」運動,終因計劃泄露而被捕。
漢口事敗後,梁啟超即遠赴澳洲,一路反思變革社會之新途徑。這一年,梁啟超逼近而立之年(時年29歲),也陷入了情緒低谷。彼時,新舊力量交替,中西思想激蕩,革命新黨屍骨日寒,保守舊派茫然無著。一時間,國家如萬馬危臨深淵,喑然不見天日。長歌當哭,梁啟超於這一年始發表了一篇意味深長的文章【過渡時代論】。
「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為何狀也。雖然,為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沖激,為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是不經營慘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
「扁舟一葉放中流」,這一幅「兩頭不到岸」的危險圖景,被學者楊國強的新作【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參照作為標題,作者由此希望帶領讀者重返一百年前晚清和民國初年的歷史現場,讓今人感受劇變時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景轉換:從戛然而止的科舉停擺到轟轟烈烈的變法立憲,從掀天動地的辛亥鼎革到漣漪般一圈圈蕩開的新文化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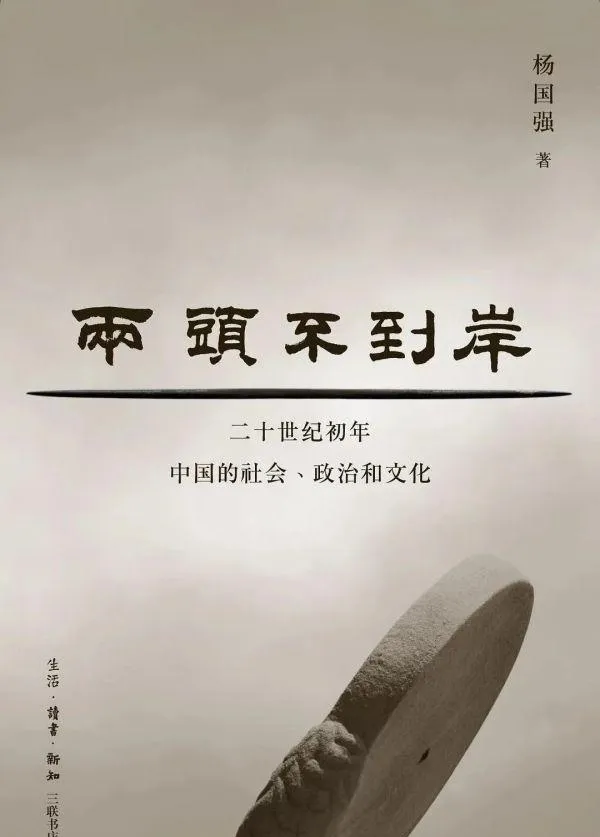
【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
楊國強 |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3年11月
在追求「變」與「不變」「快變」、「速變」和「漸變」、效法西法和保留國粹之間,新舊勢力、古今之爭和中西之辨各種不同派別爭鬥,勢同冰炭。
梁啟超所提出的「過渡時代」裏,充滿了太多的張力和迷思,就像其後來總結自身的「昔日自我」和「今日自我」之間判若兩人的個人思想觀念變遷。時代劇變中的歷史轉輪大切換,造就了一種「速成的、急切的、畢其功於一役的近代中國現代化行程」。
而如何描摹出這個全方面劇變、多層次斷裂而又時刻充滿緊張矛盾張力的「過渡時代」之特征,去除歷史被「毛玻璃化」之後表面的局部美化和種種「濾鏡」,正是當代歷史學者楊國強所追求的——盡可能回到真實、多元賽局、復雜形勢下的「歷史現場」。
楊國強教授歷時五載,爬梳剔抉,鉤沈稽考,試圖一一揭開晚清民國初年大激變時期未經「凈化」的歷史種種駁雜皺褶和時代和個人命運之錯位播弄,透過其間的人物多變和世事紛亂,來印證探究近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曲折嬗變、內在脈絡和始因終果。
士人顛仆,道術為天下裂
1905年,正值光緒三十一年,作為清廷回應朝野有識之士的舉國呼籲,光緒皇帝以「時局多艱、儲才為急」、追慕「東西洋各國富強之效」為名,宣布「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1300余年的科舉制度,由一紙詔書立刻停擺。
科舉的千年轉輪一朝按下永停鍵,傳統士人們上下求索、難辨前路的顛仆命運才剛剛開始。
按照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的說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大夫們)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充當了一種類似粘合劑、連結器和精神燈塔的角色。
對上,士人要「塑造明君」,確保政統合乎道統軌轍,維護社會公義的一致性和恒久性;對下,士人要教化百姓,維持下層社會禮法制度的規範性和正確性,從而確保「上下同心」,以維系一個超穩定社會結構之千年穩定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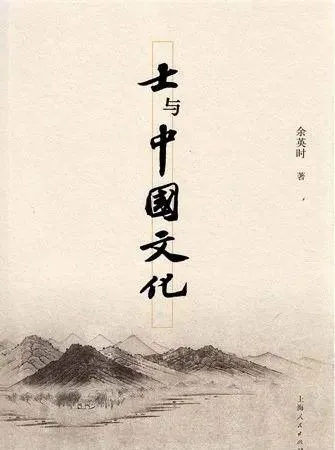
【士與中國文化】
余英時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從最初以章句取進士,到明朝以八股文選取人才,以帶病之身,歷千年演化,雖屢受詬病,仍一路逶迤至晚清,終被洋務運動興起後的各種新式學堂所取代。
新式學堂不僅教育內容與傳統科舉大相徑庭,其批次化的生產人才方式,興實業以救國的教育宗旨,加上新式學生以及隨之不斷催生的新學潮,釀就了一波接一波的東潮西潮,最終導致晚清民國初年的傳統士人大規模分流。
這一波分流和兩宋之際的士人走向民間有大不同。兩宋之際,國運雖然式微,但道統和政統兩者依舊能維持各自的一致性和相互間的和諧關系;晚清民國初年,在道統和政統全部失去其傳統合法性的大背景下,士人群體中每一個個體命運面臨進退失據和無所依傍的境地,知識精英一夜之間淪為難以消納的「高等遊民」,其社會地位變化之懸殊,尤為慘烈。
清末名儒陳漢章的故事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個例。
陳漢章早年師從晚清樸學大師俞樾,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意欲聘其為教授,陳漢章堅決不受,反而要求做京師大學堂的學生。
按照當時的京師大學堂的章程規定,學生從該學堂畢業之後,可以直接欽賜翰林。陳漢章1909年入學,1913年畢業,可畢業前後,正值天下鼎革,「當官的願望最後被辛亥革命徹底打破」,京師大學堂的「翰林獎勵章程」還沒來得及施行便戛然而止,陳漢章當了四年學生之後沒能當成翰林,只能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
相比於陳漢章,魯迅和孔乙己們的命運更糟糕。
「有高等文憑而無光耀功名、有民間聲譽而無官家俸祿、有知識滿懷而無尊貴待遇」,成了那一代知識人的集體命運。孔乙己們脫不下長衫,只能淪落烏鎮,靠賒賬借酒消愁度此殘生;公務員魯迅因民國教育部長欠薪很難領到薪資,只好與女友許廣平相約南下謀生,輾轉廈門廣州兩所大學,最後在上海賣文為生。
魯迅在去世兩年前的1934年5月29日給母親的一封家信中這樣寫道:
「男(指魯迅本人)為生活計,只能漂浮於外,毫無恒產,真所謂做一日,算一日,對於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辦法,京寓離開已久,更無從知道詳情及將來……」。
更早的一封寫於1933年7月11日的家信則訴苦說:
「家中既可沒有問題,甚好,其實以現在生活之艱難,家中歷來之生活法,也還要算是中上,倘還不能相諒,大驚小怪,那真是使人為難了。先既特雇一人,專門伏侍,就這樣試試再看罷。男一切如常,但因平日多講話,毫不客氣,所以懷恨者頗多,現在不大走出外面去,只在寓所看看書,但也仍做文章,因為這是吃飯所必需,無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會遇到危險,真是無法可想。」
顛沛於骯臟城市,流轉於困厄溝壑,士人失途於時代轉換,不僅僅是科舉功名流落無著,更有謀生艱難之外的性命侵辱。
傳統學堂因得獎勵翰林、進士、舉人、拔貢、優貢、歲貢、廩生、增生、附生,獲得科舉功名後陡然身價倍增,可是到了新式學堂時代,知識分子或棄筆從戎,或只能漂浮在大城市謀生,當時甚至有「讀書十年,當兵一時」的童謠,諷刺士人社會地位降低,遠不及一個普通士兵,甚至還會有性命之憂。
1912年3月19日夜,常州中學堂監學陳士辛被逮捕後,第二天即被當地軍政頭目以「侵吞軍餉之罪」先斬後奏;一年後,【愛國報】丁某以「通匪罪」槍斃。此後,教員周剛直被殺,報人胡信之被殺,記者邵飄萍被殺、主編林白水被殺,而當年奉狀元為文曲星的軍閥張宗昌,對付沒有功名的文人,殺心越發兇惡,殺起來更無所顧忌。
士人顛仆於途,道統價值體系歸於潰敗,道術將為天下笑,整個社會秩序進而分崩離析、社會文化由此全方位斷裂。「百變俱起,一變而變」,清末和民國初年一波疊加一波的社會疊變浪潮,由此無限蕩開去,逐漸遠離了原先社會結構演進的本原、主體和出發之初心。
文化斷裂,激進漸成主流
耕讀並重的科舉制度和舊式學堂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新的教育理念、新式學堂所代表的西式教育制度,背後是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
士大夫群體的解體,不只發生在文化價值領域,新舊文化的斷裂延伸至政治領域之後,就是一波接一波的社會震蕩和思想翻攪,從政治結構的內外離散到社會結構崩壞,整個社會變成了「一盤散沙」。
從1894年的甲午喪師之恥,到1898年的戊戌變法,再到1900年庚子之變,晚清10年間,新勢力尚未登場,舊勢力逡巡不去,暴力革命此起彼伏,綿延不絕。
【庚子記事】錄載,1901年辛醜正月初八這一天,禮部尚書啟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以及載勛、毓賢、趙舒翹、英年等滿清六大臣被斬首於菜市口,「護送囚車,彈壓法場,皆是各國洋兵,因數百人」。
而一年前的1900年,清朝滿族大臣立山等五人,因力主和洋人議和,同樣被慈禧太後棄屍於菜市口,方其時,「乃數千義和團護決,今則數百洋兵護決,世界變遷,令人浩嘆」。
從洋人護法場,到義和團護法場,3年前的戊戌政變後的法場,更令人喟嘆,只不過戊戌變法所被斬首者,除楊深秀外,皆「南人」;而辛醜年間洋人列強所殺者(「滿清六大臣」),除了天水尚書趙舒翹外,全是北人。戊戌變法殺的都是少年新進,辛醜列強殺的都是老成舊輔。
無論被殺者是「南人」還是「北人」「漢人」還是「旗人」,「少年新進」還是「老成舊輔」,4年時間,晚清朝野處處殺氣騰騰,戾氣充塞天地。其恐怖血腥,不亞於當年法國大革命那一幕幕暴力屠戮。
到民國初年,孫中山依舊稱當時的中國社會為「舊屋已拆、新屋未成」。滿清大皇帝雖然被推翻,由此衍生出無數個漢族小皇帝,較以前的大皇帝更加「暴虐無道」(孫中山先生語)。
因此,文化斷裂催生的激進主義,成為政治變革主流,社會改良和主張漸變者通通被痛斥為保守主義和頑固不化,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民國初年,政治人物和知識精英們即將面對的社會,只能是楊國強在書中所描述的痛心一幕:
「一種沒有整體性的社會、一種沒有維系力的社會、一種沒有主體的社會、一種沒有規則的社會,對於身在其中的個體來說,便是一種沒有常態的社會和普遍痛苦的社會。」
其中最具悲劇性的代表人物,就是民國政壇的佼佼者立憲派掌旗官宋教仁。宋與唐才常同為湖南人,早年留學日本時結識黃興等革命黨人,在民國政壇中是立憲派的中堅人物。
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帝制後,作為革命一派的南京政府,無疑手中握有更多的道義和主導地位,繼孫中山就任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後,整個國家之內「勢力之莫與敵」的袁世凱,自然就成了南京政府革命派直接且最主要的對手。而如何利用和鉗制這個對手,正是宋教仁等立憲派們在制定【臨時約法】時費盡心力之最多處。
宋教仁代表的立憲派和袁世凱代表的保守派,兩者之間圍繞【臨時約法】展開的微妙深藏的權力爭鬥,在唐德剛先生的【袁氏當國】一書中已經有非常精彩的描寫,在此不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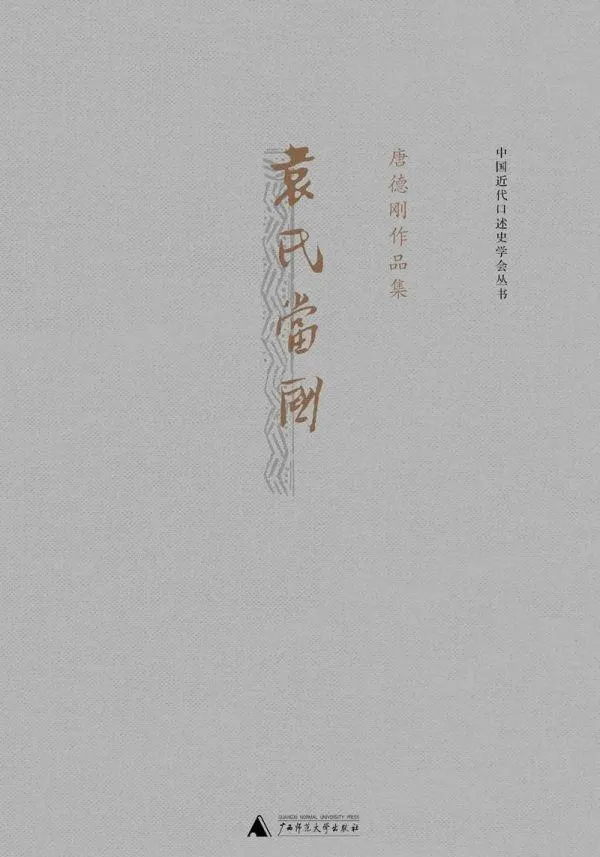
【袁氏當國】
唐德剛 | 著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6月
其中最可感嘆處,是宋教仁們一開始就將袁世凱們釘選為舊勢力代表的「靶心」,這位由清代最後一個總理大臣搖身一變的權力對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只是民國政權的「異己力量」和可怕敵手。
南北議和後,孫中山和袁世凱進行權力交接,【臨時約法】在宋教仁修訂後,政權形式直接從孫中山時期的總統制,變為袁世凱時期的內閣制,在後一個時期,總統袁世凱幾乎只能等同於一枚象征性的橡皮圖章,所有的權力系數被收回到國會手中。
法因人變,以術制道,宋教仁破壞的不僅僅是法律的神聖性,更反映出清末民初政治精英們的局促一面。宋教仁的初心,無非是想用一切權力收歸國會的內閣制,來防範他深信不疑的袁世凱之專制和「野心」,西方的三權分立不僅被拿來全盤照抄,更演變為一種「參議院躍為太上政府」的民國特色——總統權力和內閣總理的權力通通被沒收。
後來有學者稱宋教仁等立憲派的做法,無異於「對人立法」。究其實質,在晚清民國初年以文字左右輿論和鼓蕩人性的那一代政治人物中,梁啟超和宋教仁都屬於「關註革命多於關註憲政」的「革命派」,就像嚴復和章太炎後來批評的那樣,晚清民國時期的革命黨人本質更長於革命,而隔膜於切實的憲政政治理論和實踐。
悲劇的種子早已埋下。1913年3月22日清晨,民國憲政之父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謀殺時的清脆槍聲,不僅扼殺了繈褓中的民國憲政夢想,更預示了暴力一波接著一波延伸之際一代政治人物的群體悲劇: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短短30年間,政治場景魔幻劇變,從守舊的一邊倒,到開新的一邊倒;從「盡去舊法」之後,一個沒有本體與本位的中國如臨深淵,再到新制未立,扶搖飄蕩的「過渡時代」依舊延續,梁啟超稱之為「青黃不接」的時刻,而過渡時代的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復,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究可哀嘆也。
自從梁啟超以「過渡時代」來形容「庚子國變」後的中國社會之劇變,重心俱在「過渡時代」的「兩頭不到岸」。而每一個身處這一「兩頭不到岸」境遇者的心理窘迫和命運遭遇,許多先賢今哲早就作出了預言。
民國知名記者黃遠生譬喻為「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李大釗謂之「如敝舟深泛溟洋」,「猶在惶恐灘中也」;當代史學大家唐德剛和黃仁宇則稱之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定經歷的危險「三峽時刻」。
回望百年前梁啟超這一「知更之鳥」(章士釗語)的預言,唯有這促進社會變革的「希望之湧泉」,激勵一代代後來者接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