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謙語談書風
編輯|謙語談書風

中唐時期是中國佛禪發展最為輝煌鼎盛的時期之一,佛禪之論成為當時士人之間的風尚。 元稹很早就開始接觸佛教。
據何劍平考證,「元稹在十六歲前即接觸佛教是可以斷定的事實」,加之其二姐出家,「次為比丘尼,名真一」, 因而元稹對佛家信仰一直保有親近之心,在他的詩歌裏也出現了一批涉佛詩。

寺院的寓意
中唐時期對佛教的寬容導致佛寺院落建造興盛, 在元稹的涉佛詩中,寺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份,提及寺廟的詩歌有37首。
其中包括大肆渲染描繪寺廟環境與寺院生活的,也有只是在詩歌內簡單提及的。從寺廟扮演的角色來看,具體可做以下劃分:

(一)寺廟作為詩歌活動進行的場所
寺廟作為某一部份詩歌內所記述活動的主要發生場所,是詩歌創作的大背景, 隨著寺廟圖景的徐徐展開,詩中人物的活動也慢慢發生,在某些情況下,寺廟還成為具體描寫的客體,包括其優美的自然景觀和獨特的人文內涵。
如【和友封題開善寺十韻】是元稹在江陵恰逢竇鞏遊江陵,兩人唱和所作, 詩歌細致地描寫了開善寺的環境,用綴珠、紅泥、燈籠、香印等一系列詞來進行寺廟風景書寫……
詩人將寺廟作為一個遊覽風景的勝地與心靈排遣的地點,用傳統文士模山範水的筆法來對寺廟作描寫, 寺廟在這裏是整首詩的客體物件,並富有人生活的氣息。
又如【誚盧戡與予數約遊三寺戡獨沈醉而不行】記錄了詩人的一次遊寺經歷,信馬穿林,四望雲低, 描繪了寺院內外樸素自然的生活:「路幽穿竹遠,野迥望雲低。素帚茅花亂,圓珠稻實齊。」

此詩創作於元和九年,是詩人被貶江陵的第五年,這一年裏,元稹頻繁遊覽寺廟, 參閱經書,【度門寺】【大雲寺二十韻】都是他所創作的詳細展示寺廟禪修的詩歌。
這些詩歌中多工筆描繪寺院內外風景,並化用大量佛家典故,隨處充滿禪意的意象,在這裏寺廟是隔絕了塵世、莊嚴平糊、自然和諧的「桃源」。
還有一類情況是略去對寺廟客體的描寫,詩歌所述活動依然是在寺廟內進行, 但寺廟也只是單純地作為活動的大背景而存在,不加以詳細描寫。

在貞元十二年,尚未入仕的少年元稹前往西明寺尋僧不在, 所見春日西林,蓮池無波等等都是在寺廟中發生的,寺廟是整首詩發生的大背景。
又如元和五年從東台罰俸西歸後,元稹曾與吳端等友人唱和作詩,詩中回憶了自己正式入仕拜左拾遺前優遊林下的少年生活,「閑行曲江岸,便宿慈恩寺」。
在早春時節,不隨京中權貴車塵馬足, 而是獨自賞春,朝遊曲江,暮宿慈恩,與僧同食,日高痛飲。
「冷飲空腹杯,因成日高醉。酒醒聞飯鐘,隨僧受遺施」, 這一系列的活動是在寺廟中進行的,寺廟只是活動發生的大背景。
(二)寺廟與詩歌活動相分離
元稹涉佛詩中的寺廟可能獨立於詩歌主題內容而存在,它的出現只在詩歌中起到點綴的作用。
活動並不在寺廟中發生,寺廟和主體活動沒有太密切的關系,寺廟被模糊去其他特征, 只剩下它最基礎最本質的形象。

如在【思歸樂】中所作:「江陵道塗近,楚俗雲水清。遐想玉泉寺,久聞峴山亭。此去盡綿歷,豈無心賞並。」 這裏的寺院只是作為點綴涉及,在詩中扮演一個特殊的地點,是「遐想」和「久聞」,並不是當下真實所處環境。
在貶江陵途中與友人的寄詩裏,元稹「暇日上山狂逐鹿,淩晨過寺飽看雲」,這裏沒有對寺廟作任何形容描繪,已經濃縮成了「寺」, 只是一種代表,這是詩人料想到了江陵之後官閑事少的生活,有自我開解、自我解嘲之意。

在【酬竇校書二十韻】中提及「竹寺荒唯好,松齋小更憐」, 「竹寺」只是指「栽種修竹」的荒僻寺院,在整首詩歌中依舊如珠綴一般短暫出現。
【飲致用神麴酒三十韻】同樣有「行當遣俗累,便得造禪扃」,指的是在俗世勞形之下, 詩人選擇拜訪禪院,寺院在整篇詩歌中仍然是作為一種點綴而出現。
詩中的人物形象
元稹涉佛詩中詩人本身的形象也十分多樣,展現的是詩人個體生命的某個側面。 透過對詩人自身形象塑造的歸類和分析,剖清佛教與其的幾種聯系,我們能夠更好地看到佛教在元稹生命中所起的作用。
1.訪僧遊寺的善男子
在大多數情況下,元稹在這些涉佛詩中所扮演的是訪僧遊寺的善男子角色, 他熱衷於和佛家相關的人事接觸:與好友相約入永壽寺看牡丹、至西明寺尋僧人、拜訪曾身經百戰的智度禪師、借宿慈恩寺、同僧聽佛理等等。

元稹在這一類詩歌中或闡發對佛理的見解,或表現對佛家生活的向往,均流露出與佛教的親近與融合。
在和竇鞏遊開善寺時,詩人頗為欣羨寺中樸素自然的生活,「便欲忘歸路,方知隱易招」,直到詩人本人也在其中忘了歸路,方才知道歷代名士中為何有那麽多人心願歸隱。
雖然這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陳述招隱的容易, 但從對寺廟那一系列動人的描寫和「忘歸路」已能夠看出,詩人本身已在「易招」之中,動了歸隱的心思。

【思歸樂】中有「遐想玉泉寺,久聞峴山亭。此去盡綿歷,豈無心賞並」, 【玉泉道中作】亦有「遐想雲外寺,峰巒渺相望」之句,都可見元稹對寺院的態度是較為積極乃至熱衷。
另有一首【春曉】,一般被認為是元稹對少年情事的追憶,詩曰: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猧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前兩句用忽明忽暗的光線、半醒半醉的精神狀態,濃郁的花香,醇厚的酒香, 以及小巧的黃鶯,婉轉的鳥鳴,創造了一種香甜朦朧的環境。

這裏的寺是「二十年前」過去故事發生的寺,可以猜想,不管這是不是元稹「自敘」少年時的邂逅, 從詩人的用詞和對環境的渲染,都能看出在這裏並沒有負面的情緒,甚至是以一種珍視、回味、滿懷柔情的筆觸來書寫。
在很多情況下,詩人又是一位希求解脫的困厄人,佛寺是他心靈的皈依和自我精神求助之處。 在仕途不順、蒙冤含怒時,他嘗試從與僧佛的交往中尋找解脫和安慰,在對生活感到迷惘、精神脆弱的時候,佛教能夠給予他一定的救治作用和心靈鼓勵。

詩人尋求解困
【酬樂天勸醉】涉及的大乘佛教經典【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是歷來禪者修習如來禪、明心見性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元稹詩雲「沈機造神境,不必悟楞伽。酡顏返童貌,安用成丹砂」, 正是對白居易【勸酒寄元九】「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鍊丹砂」的回復。
此時的元稹出使東川卻被罰俸西歸, 經敷水驛卻被宦官折辱,回到京城又被貶江陵,精疲力竭之下與白居易寄書長談。

【楞伽經】在這裏所代表的是向佛門所求取的解脫辦法, 後一句「丹砂」指的是向道家尋求的解脫辦法,但這些都不如飲酒快速有效。
這不是元稹詩中第一次出現佛經,結合「不必」二字,可以推想,元稹應該曾向佛教經典痛苦地乞求過寬慰和解脫, 說「不必」,不過是心中巨大的失望苦悶無可排解,而用酩酊一醉來麻痹自我。

元和十年所作的【和樂天贈雲寂僧】同樣透露著無法從塵世煩惱中解脫的消極情緒: 欲離煩惱三千界,不在禪門八萬條。心火自生還自滅,雲師無路與君銷。
詩人深感塵世是痛苦的,而這種痛苦又難以解除,哪怕八萬四千法門也無可解之門路,心中妄念之火升起,便只能靠著內心去消除,別無他法。
元稹這種對俗世痛苦的認識、用自我調節來對抗痛苦的辦法,都具有濃厚的禪宗色彩。 在隨後寄給西京慈恩寺僧人的【寄曇、嵩、寂三上人】中可以看出,詩人依舊受困於人世的痛苦和煩惱,身心俱疲。

到了晚年所作【悟禪三首寄胡杲】,已少用一些激烈極端的字眼, 也不再執著尋求解除煩惱的「對治之法」,反而是「晚歲倦為學,閑心易到禪。病宜多宴坐,貧似少攀緣。自笑無名字,因名自在天」。
在身體病痛和心靈疲倦的侵襲下,詩人流露出和過去的銳利進取不同的情緒, 似乎體現出他參悟妥協的一面。
元稹的涉佛詩中還會展現詩人作為傳統士大夫會友交往、仕進為官的形象。【誚盧戡與予數約遊三寺戡獨沈醉而不行】以戲謔口吻書寫好友盧戡的爽約遊寺;

【梁州夢】中「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遊」展現的是詩人與白居易心神契合、心有靈犀的友誼。
在【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裏,整個活動發生的空間和詩人情感的承載體都聚焦在「開元寺寺壁」上;
【楚歌十首(其七)】有告誡今人莫要因佞佛媚佛而招致社會不穩; 【茅舍】關註了當地百姓的風俗和民生。

涉佛詩蘊含真理
元稹很早便接觸佛教,他在涉佛詩中也展現了自己多樣的思想, 尤其隨著詩人生活閱歷的增加、仕途的深入,他在涉佛詩中流露的思考也在不斷變化。
在元稹早期的涉佛詩作中,佛教常常是以一個能夠警醒世人的形象出現,元稹也多需要借助外物來闡發哲理,經常是「在與僧人廟宇的交往中, 偶然經由僧人或外物勾引思緒,進而感悟生活哲理」這樣一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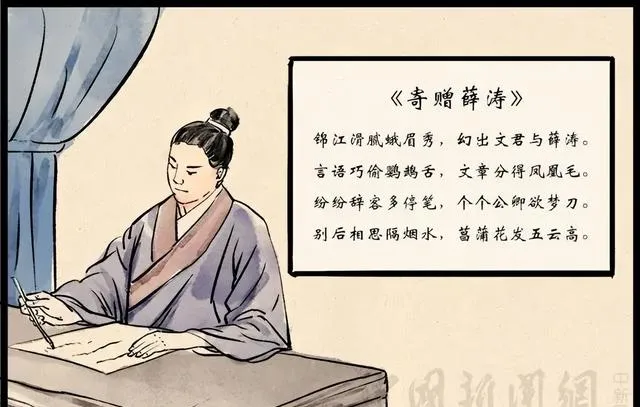
如貞元十二年明經及第寓居長安的少年元稹在與友人交往遊玩時, 入長安永壽寺內遊寺賞花,佛教常常以草木示人佛理。
元稹此詩中也以花的開謝來警示世人人生真理:「繁華有時節,安得保全盛。色見盡浮榮,希君了真性。」
貞元十八年,二十四歲的元稹在長安與白居易一同備考進士科,該年元稹的【杏園】一詩也寫得頗有意思: 「浩浩長安車馬塵,狂風吹送每年春。門前本是虛空界,何事栽花誤世人。」

結語
詩的末句既是戲謔之語,又在戲謔中含有警誡之意。 長安是車馬喧囂之處,更是眾人追逐的紅塵最深處,而杏園有進士登科的含義在其中,是文人的最高理想之一。
詩人一方面極其渴望成為來年「杏園客」之一,另一方面又能站在佛教的角度意識到, 不論是鮮花還是功名,都不過是「虛空界」,皆是空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