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海斌(馨心齋主)

▼新竟陵詩派圖示

「竟陵派」小考
甘海斌
【前言】
筆者也算戎馬一生,未到花甲之年即已退休,過起了閑適的生活。我曾吟詩表達自己退休後的心境:「……心中無罣礙,余歲不堪憂。日食三餐飽,隨時樂自由。」閑人,就有閑心,得閑空,讀閑書,悟閑理,尋閑樂,不亦樂乎!我也喜歡寫點閑詩碎文,悅己悅人。
我出生於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湖北省天門市。這裏曾誕生了名聞世界的茶聖陸羽,也是著名的「狀元之鄉」。所以,我在退休後,先後寫了【茶聖陸羽出天門】【狀元蔣立鏞其人其事】兩篇拙文,發表在報刊和網絡媒體上,受到讀者紛紛點贊,不禁欣喜自慰。
孩提時代,我還得知幾百年前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一個「竟陵派」,讓天門人引以為驕傲。成人後,卻不曾下功夫去了解「竟陵派」所呈現的文采風流,及在璀璨星河之中的興衰浮沈。
但喜愛古體詩詞的雅好興猶未闌,時常發表幾句拙詩在報刊上,並結集為【夢之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此浪得「局長本色是詩人」之虛名。
2020年8月,我加入了由範恒山先生為主帥、北京龍潭詩社社長傅東漁為副將,發起組織的「北京新竟陵詩派」。這是一群生活在北京、古體詩詞愛好者自願結社組成的文學小「沙龍」,非週期性開展詩詞交流酬和,雅賞文化娛樂,頗有衍襲古人儒雅之風韻,玩味高士情調之意味。忝列其中,幸甚至哉。
近幾年來,北京新竟陵詩派在範、傅二人引領下,風生水起,成果頗豐,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竟陵新韻】【盛世詩語】兩部詩集。
但「仰山以崇德,觀水應知源。」新竟陵派若不知鐘譚之如何,談何一脈相傳?弄不清古竟陵派之源流,豈敢言繼承弘揚?故遵恒山兄之囑,余對「竟陵派」作此小考,以饗同道詩友和熱心讀者。
▼新竟陵詩派旗幟

在中國古今文壇上,文學家與文學流派的更叠是極為自然的。既有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那必然是「各領風騷數百年」。
「竟陵派」是明代後期所產生的一個文學流派,名噪天下,影響深遠。因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門市)人鐘惺、譚元春為傑出代表,因此而得名,又稱竟陵體或鐘譚體。
鐘惺,字伯敬,號退谷,又號退庵。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市)皂市鎮人。萬歷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著作有【隱秀軒集】【史懷】等。
他的文學主張與公安派有近似處,也反對擬古,但強調從古人詩中求性靈,在詩文中開眼界,與公安派的「性靈說」有明顯不同。鐘惺在【詩歸序】中說:「真詩者,精神所為也。
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這種藝術審美品格,形成了這一派文學上「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鐘惺工詩能文,自己更以文自負。
他的一些論史之文,能「發左氏、班、馬之未竟,鉤其隱深而出之」(陸雲龍【鐘伯敬先生合集序】);所作諷時小品或題跋等,文筆犀利,語言簡練,極具個性特點,如【夏梅說】【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誌冊子】等;紀遊之作,為人稱道的有【浣花溪記】。
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號鵠灣,別號蓑翁。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市)人。少慧而科場不利,天啟七年(1627) 始舉於鄉,鄉試第一。崇禎十年死於赴考進士途中。歸葬於竟陵黃潭鎮白龍村。
與同裏鐘惺同為「竟陵派」創始人,論文重視性靈,反對摹古,提倡幽深孤峭的風格,所作亦流於僻奧冷澀,有【譚友夏合集】。鐘、譚曾編選【詩歸】(單行稱【古詩歸】、【唐詩歸】)。在序文和評點中宣揚他們的文學觀,風行一時,竟陵派因此而成為影響很大的詩派。
竟陵派與公安派是比肩而生的。是晚明繼公安派之後崛起的一支文學革新流派。「公安派」是明代後期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為代表的詩文流派。公安派的崛起是對風靡文壇的前後七子擬古思潮的矯正。
公安派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文學理論與散文創作方面,但在詩歌創作上公安派也有新的特色。針對擬古派的文學主張,公安派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他們的核心主張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他們要求文學作品充分表現出作者的個性、感情。認為一切優秀作品都是率性而發,「從自己胸臆流出」的,只有「出自性靈者」,才算是「真詩」(袁宏道【敘小修詩】江盈科【敝篋集序】)。
公安派認為,古代的格律、格調則完全不必拘泥,「信腕信口,皆成律度」(袁宏道【雪濤閣集序】),只要能寫出真性情,真面目,律度、法則也就自在其中了。
在文學發展觀上他們針對擬古派盲目崇古的觀點,指出文學是隨時代發展而進步的,每個時代的文學各有特色,「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敘小修詩】),完全不必厚古薄今。他們認為「古未必高,今何必卑」,假如「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
因此,文學創作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不能一味因襲、摹擬,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擬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在文學風格方面,他們「尚今尚俗」,強調文辭、語言合一,以為「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袁宏道【論文】上)
文學語言應「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袁宏道【與馮琢庵師】)。因此,他們倡導一種通俗明快、活潑暢達的語言風格,這對於糾正擬古派模仿古言古句的風氣,開創新言風格有一定的作用。
▼鐘惺著作【隱秀軒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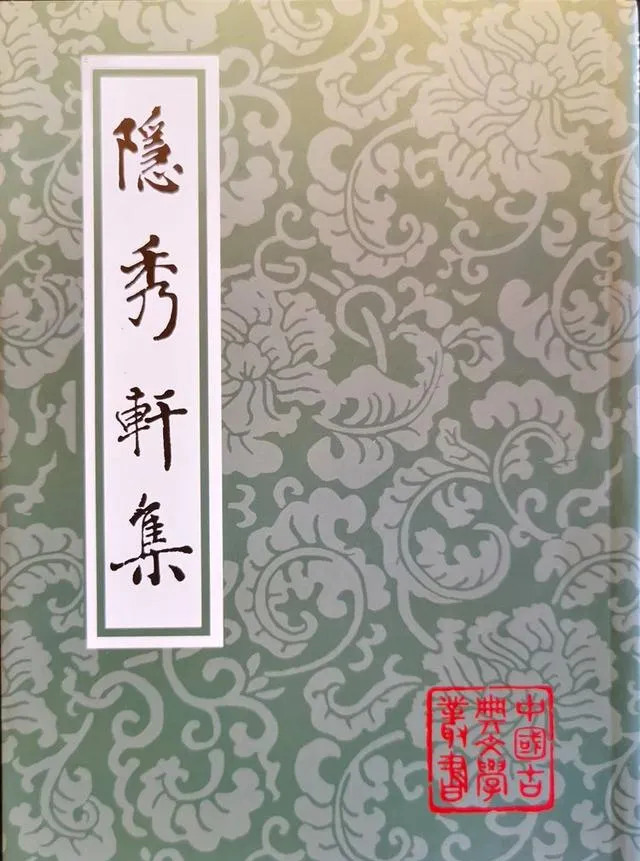
竟陵派的產生是在公安派鋒芒消退的情況下趁勢而起的。竟陵派文學主張:為矯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制濫造,流為俚易膚淺的弊病,鐘惺、譚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絕俗的「孤懷孤詣」和「幽情單緒」,認為只有處於空曠孤迥、荒寒獨處的境地,透過孤行靜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寫出表現作者性靈的真詩。
同時主張作詩為文,要以古人為歸,讀書學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達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認為公安派作品俚俗、浮淺,因而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但所主張和宣揚的「性靈」與公安派不盡相同。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
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是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語句之深奧。由此形成了竟陵派的創作特點:雕琢字句,意境幽遠,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
竟陵派後來超越公安派,盛極一時,但褒貶不一,毀譽參半。在明後期對反擬古之風有促進之功,對晚明及清早期小品文的大量產生有巨大影響。然而,因為他們作品題材狹窄,語言艱澀,又束縛了創作的發展。所以逐漸走向沒落。
值得指出的,由於竟陵派的出現是為矯正公安派的俚俗粗淺之弊,所以很容易讓人造成竟陵派與公安派對立的誤解。其實,兩派的相同之處還是占多數的。二者的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對反對前後七子所采取的路徑不同,出發點與目的還是一致的。
竟陵派的追隨者有蔡復一、張澤、華淑等。這些人大都堅守竟陵衍生澀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語,自稱「空靈」,使竟陵派文風走向極端。當時受竟陵派影響而較有成就的是劉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為竟陵體語言風格代表作之一。
竟陵派的學古乃至復古,不得不玩索於一字一句之間,將詩文創作引入狹窄的天地。他們評詩,只著眼於一字一句之得失,流連於煩瑣纖仄之工穩。
他們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澀詭譎,專在怪字險韻上花樣翻新,與公安派通俗曉暢的詩文大相徑庭。因而,竟陵派的文學主張,正迎合了那些因處於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沈的封建文人之文學傾向。
明代中葉後,詩壇掀起了一場以復古面目出現的革新活動。以李夢陽、何景明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徐禎卿等人的文學群體,稱「前七子」。
他們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目的是掃蕩台閣體的無聊文風,力圖恢復文學自身的獨立地位。但由於他們的創作理論落後,缺乏創新,有泥古不化的傾向。
至嘉靖、隆慶時期,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在內的文學群體,稱「後七子」。
他們一方面繼承了「前七子」關於重視文學自身價值的觀點,另一方面,他們在復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遠。其成員間的文學主張和創作風格差異較大,並不是一個主張和創作實踐完全統一的文學流派。
「唐宋」、「公安」兩派曾先後給予抵制和抨擊。 在整個晚明文學的思想理論方面影響最大的實際是李贄。竟陵派追隨公安派,而公安派的文學觀主要是從李贄的思想學說中發展而來的,所以它的基點不在於詩文的語言技巧,而在於個性解放的精神。「性靈」原不是新鮮的辭語,南北朝時就頗為習用。
如庾信稱「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趙國公集序】),顏之推稱「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顏氏家訓】),其意義大致與「性情」相近。明代中後期,六朝文風重新受到重視,「性靈」一詞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詩文評論中又頻繁使用起來。
袁中郎進一步在這裏面加入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和具體的藝術要求,使之成為影響一代人的文學口號。首先,袁中郎的「性靈說」是出於李贄的「童心說」,它和「理」,和「聞見知識」——即社會既存的行為準則、思維習慣處於對立的地位。
標舉「性靈」,也是同流行的擬古詩風的強烈對抗。總之,竟陵派的理論,在強調真情,反對宋人「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等基本方面承續了李夢陽以來的文學觀點,但他們並不主張著力摹仿古人的「格調」、「法度」,在這一點上與前後七子都不同。
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有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襲;每個時代的語言也在不斷變化,「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所以作家套用自己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真實的思想感情,而不必談什麽「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鐘惺散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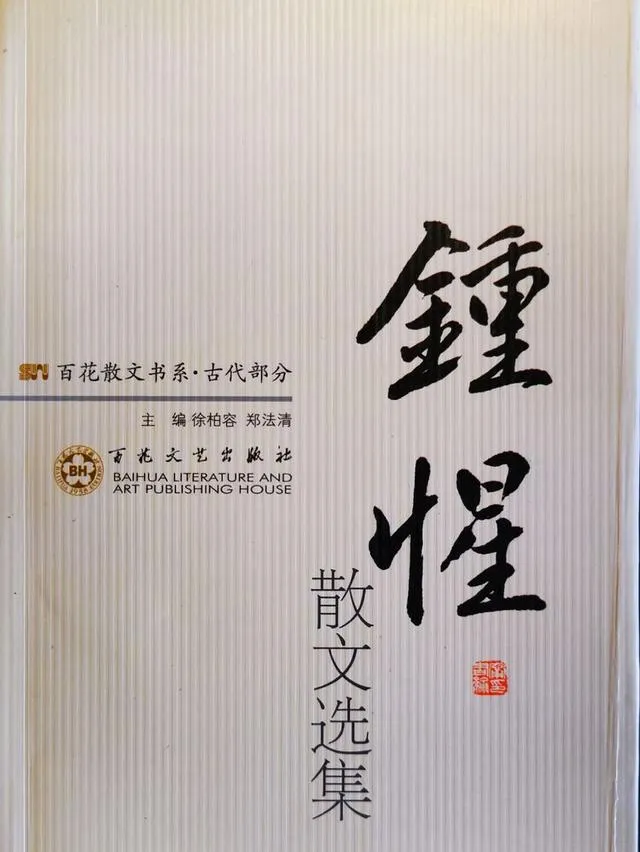
因為前後七子大力提倡復古,文壇上的宗派勢力和剽襲之風,已經成為自由地抒發性靈的新文學的極大阻礙。自由派文人所批判的物件,主要是在後七子宗派主義作風下形成的以擬古為復古,「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
一唱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袁宏道【雪濤閣集序】)的詩壇風氣。特別是對後七子詩派末流的粗濫而毫無性情的假古董,攻擊尤烈。袁中郎常斥責這一類作者為「鈍賊」,甚至刻薄地罵為「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
竟陵派在理論上接受了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口號,同時從各方面加以修正。他們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奇」(鐘惺【問山亭詩序】),即反對步趨人後,主張標異立新。那麽,從公安派那裏來,竟陵派又向何處「變」呢?
他們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於俚俗、淺露、輕率,便提出以一種「深幽孤峭」的風格來匡正。鐘惺【詩歸序】談如何求「古人真詩」有雲:「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
他們也主張「向古人學習以成其「厚」(譚元春【詩歸序】說他和鐘惺曾「約為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但這又不像「前後七子」那樣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調」,而是以自己的精神為主體去求古人精神之所在。所以他們解說古詩,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性靈說的核心是強調詩歌創作要直接抒發詩人的心靈,表現真情實感,認為詩歌的本質即是表達感情的,是人之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說好詩應當「情真而語直」(【陶孝若枕中囈引】),「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序小修詩】)。
性靈的本意是指人的心靈。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說: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於自然界的「無識之物」,即在於人是「性靈所鐘」,有人的靈性。【【文心雕龍】·序誌】中所說「歲月飄忽,性靈不居」,亦是指人的心靈。
【原道】篇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說文章乃是人的心靈的外在物質表現。其後鐘嶸在【詩品】中突出詩歌「吟詠情性」的特點,強調「直尋」,抒寫詩人「即目」、「所見」,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贊揚阮籍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等,和後來性靈說的主張是接近的。
▼鐘惺著述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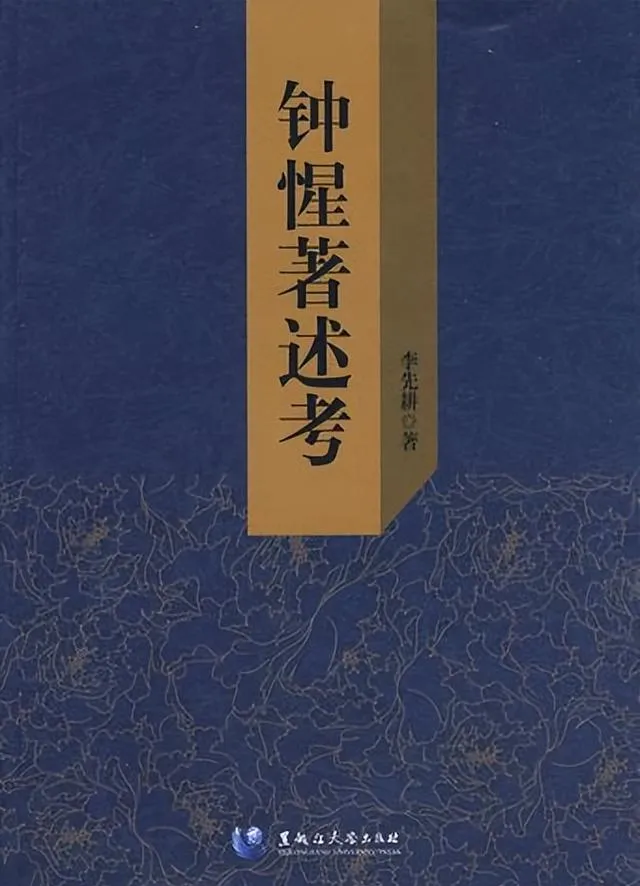
性靈說雖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但是作為明清時期廣泛流行的一種詩歌主張,它主要是當時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文藝思想鬥爭的產物。因此它和歷史上的有關論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時期詩歌理論批評中的性靈說的主要特點如下:
一是 性靈說是在李贄童心說的直接啟發下產生的,是當時反理學鬥爭在文學理論上的具體表現。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封建專制制度走向沒落,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學術思想界展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和鬥爭。
李贄在著名的【童心說】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學的最大特點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對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張文學要寫「童心」,即「真心」,是未受過虛偽理學浸染的「赤子之心」,認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體現。
文學要寫「童心」,實質就是要表現「真情」,反對描寫受儒家禮義束縛的「偽情」。這就為性靈說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二是 性靈說的提出,也是針對當時文藝上反對復古模擬的風氣而發的。明代前、後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給文藝創作帶來了嚴重的束縛,使詩文普遍陷入了模擬蹈襲的死胡同。
李贄在【童心說】中就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的問題,認為只要寫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這是對復古主義文藝思想的有力的抨擊。公安派正是進一步發揮了李贄這個思想,提出了一個「變」字,指出每個時代文學都有自己的特點,必須具有獨創性,才是好作品。
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所提出的「窮新極變」的原則和前、後七子的蹈襲擬古,從創作原則說,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變」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靈說的理論基礎上的。
因為詩文都是性靈的表現,而性靈是人所自有,不同時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樣,所以評論文學作品的標準,不能以時代論優劣,而應以能否寫出真性靈為依據。
三是 性靈說從真實、直率地表達感情的要求出發,在詩歌藝術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暢之美,反對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對以學問為詩。公安派強調詩歌的「真」、「趣」、「淡」,認為這是「真性靈」的體現。
他們提倡質樸,反對鉛華:「夫質猶面也,以為不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減,樸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園存稿引】)主張文學語言要接近口語:「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袁宏道【敘梅子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

竟陵派又發展了重「真詩」 、重「性靈」的主張。鐘惺【宿烏龍潭】詩:「淵靜息群有,孤月無聲入。冥漠抱天光,吾見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潛,中宵萬象濕。損益難致思,徒然勤風日。
籲嗟靈昧前,欽哉久行立。」詩所描繪的是一幅萬籟俱寂、孤月獨照、寒影默然的宿地圖景,一切都給人以幽寂、淒涼與峻寒的感覺,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幽情單緒」、「寄情孤詣」的創作境界吧。
難怪錢謙益說:竟陵派詩風「以淒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其所謂幽深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鐘提學惺】)。
竟陵派提倡學古要學古人的精神。應該說,竟陵派提倡學古要學古人的精神,以開導今人心竅,積儲文學底蘊,這與單純在形式上蹈襲古風的做法有著天壤之別,客觀上對糾正明中期復古派擬古流弊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
再者他們也較為敏銳地看到了公安派末流俚俗膚淺的創作弊病,企圖另辟蹊徑,絕出流俗,也不能不說具有一定的膽識。
但是,竟陵派並未真正找準文學發展的路子,他們偏執地將「幽情單緒」、「孤行靜寄」這種超世絕俗的境界當作文學的全部內蘊,將創作引上奇僻險怪、孤峭幽寒之路,縮小了文學表現的視野,也減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種直面人生與坦露自我的勇氣,顯示出晚明文學思潮中激進活躍精神的衰落。
在重視自我精神的表現上,竟陵派與公安派又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審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這背後,又有著人生態度的不同。
公安派詩人雖然也有退縮的一面,但他們敢於懷疑和否定傳統價值標準,敏銳地感受到社會壓迫的痛苦,畢竟還是具有抗爭意義的;他們喜好用淺露而富於色彩和動感的語言來表述對各種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現內心的喜怒哀樂,顯示著開放的、個性張揚的心態;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詩境,則表現著內斂的心態。
錢謙益說他們的詩「以淒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列朝詩集小傳】),是相當準確的。他們的詩偏重心理感覺,境界小,主觀性強,喜歡寫寂寞荒寒乃至陰森的景象,語言又生澀拗折,常破壞常規的語法、音節,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氣息不暢。
▼譚元春文集

如譚元春的【觀裂帛湖】:「荇藻蘊水天,湖以潭為質。龍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為,喁喁如魚濕。波眼各自吹,肯同眾流急?註目不暫舍,神膚凝為一。森哉發元化,吾見真宰滴。」
這詩就不大好懂。大致是寫湖水寒冽,環境幽僻,四周發出奇異的聲響,好像潛藏著各種怪物。久久註視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於是在森然的氛圍中感受到造物者無形的運作。
鐘、譚的詩類似於此很多,他們對活躍的世俗生活沒有什麽興趣,所關註的是虛渺出世的「精神」。他們標榜「孤行」、「孤情」、「孤詣」(譚元春【詩歸序】),卻又局促不安,無法達到陶淵明式的寧靜淡遠。
這是自我意識較強但個性無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轉向內傾的結果,由此造成他們詩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覺狀態。
在文學觀念上,竟陵派受公安派的影響較深。鐘惺以為,詩家當「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詩歸序】)。譚元春則表示:「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
【詩歸序】這些主張都是竟陵派重視作家個人情性流露的體現,可以說是公安派文學論調的延續。盡管如此,竟陵派和公安派的文學趣味還是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首先,公安派雖然並不反對文學復古,他們只是不滿於仿古蹈襲的做法,但主要還是著眼於作家自己的創造,以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與丘長孺】)。
而竟陵派則著重向古人學習,鐘、譚二人就曾合作編選【詩歸】,以作詩而言,他們提倡在學古中「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詩歸序】,達到一種所謂「靈」而「厚」的創作境界。
其次,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談」的口號下,不免存有淺俗率直的弊病,對此竟陵派提出以「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的創作要求。
來反對「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所為,即在總體上追求一種幽深奇僻、孤往獨來的文學審美情趣,同公安派淺率輕直的風格相對立。這樣的文學趣味在竟陵派作品中比比皆是。
▼皂市鐘惺墓

竟陵派的文學理論在文學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它實際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新的社會思潮在文學領域中的直接反映。
李贄反對以儒經典家規範現實社會與人生,袁宏道等反對以前代的文學典範約制當代人的發揮,而提倡一種具有時代性、個人性、真實性,能夠表現內在生活情感與欲望的文學,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著對舊的精神傳統的摒棄。
竟陵派在文學領域的遐邇聞名,讓天門較之同等城市變得特殊而儒雅,那樣高朗的精神起點使後人的瞻望成為一種境界。詩是哲學,是智者的言說。
有詩的旗幟,竟陵風才在天門這片熱土上緩緩吹拂。一種采自鄉野大地的人間情味,常常在春花秋月中紛披而至,那一股清新的氣息,悠然拂過人們的發梢,穿過千百年的寂靜,帶走了幾絲蟬意。
天門精彩的文化亮點堪稱「竟陵派」。日月為證:在這塊土壤上,有那麽一群人,他們曾經用筆寫出心靈而且使之成為風尚。中國的縣級市裏,能夠在古代文學中書上一筆的流派不多。這是天門人引以自豪的。
所以,今日天門城區有鐘惺大道、元春街,東湖有隱秀軒、元春榭,皂市的鐘惺墓、黃潭的譚元春墓都得到了修繕。竟陵派使天門成為詩歌茂密生長的沃土。詩歌如雨,雨如詩歌,在竟陵派的故土上行吟誦讀,該是溫潤如唇的感受吧?!
2024年元月9日於京華馨心齋
▼鐘惺傳略

▼黃潭譚元春墓
▼天門東湖隱秀軒、元春榭

▼新竟陵詩派印

▼新竟陵詩派詩詞合集【竟陵新韻】【盛世詩語】

▼作者近照

感謝各位關註瀏覽!歡迎大家賜教點評!
責編:黃素梅【白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