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索阿說「我將宇宙隨身攜帶在口袋裏」。書籍,也如浩瀚宇宙,讓我們窺得萬千生命,汲取無盡力量。
423世界讀書日期間,今日頭條推出獨家影片策劃——【我將書本隨身攜帶】,用鏡頭跟隨梁鴻、劉亮程、蔣方舟、程永新四位嘉賓,記錄下他們「隨身攜帶的書籍」,閱讀、創作及日常生活。
在中國文學界,蔣方舟過去 35 年的人生接近於【楚門的世界】。
【楚門的世界】是由澳洲導演彼得·威爾1998年執導的電影。故事中,楚門的一切都由電視台以真人秀的形式播出,什麽是真實,什麽是虛構,楚門的生活沒有邊界。這樣的模糊感也是蔣方舟的色調,9 歲出版散文集【開啟天窗】後,她就以天才少女作家的身份在註視中長大。
「在公眾面前生活了 20 多年的時間,你公共的講話和你內心非常私密的那一部份已經分不清楚了。」蔣方舟在【我將書本隨身攜帶】微紀錄片裏表達。「彼得·漢德克說‘我僅憑我不為人知的那部份活著’,我好像我沒有什麽不為人知的部份,我從小到大每件事要麽被我講述過,要麽被我寫作過,要麽被公眾所知。」
閱讀與寫作構築了蔣方舟的世界。去年 9 月,她出版了新書【主人公】。她追溯了二十位作家的命運故事和精神世界,在前言中,她這樣寫道:「書改變不了人生,它只會逐漸揭露生活的本質:受苦與掙紮永不停息。文學不會幫你減輕痛苦,但它能豐富你與受苦談判的語言。這一點點的主觀能動性,就是我們不服從地活著的證據。」
01 「做一名並不清貧的女學生」
蔣方舟出生於 1989 年,在 90 年代教育界推崇的「神童敘述」下,她被認為是寫作天才。9 歲寫成的散文集被湖南教委定為素質教育推薦讀本並改編為了漫畫書,剛念初中,她便在【新京報】【南方都市報】上開專欄。
質疑與褒獎共同伴隨著她的成長。12 歲時,她出版了一本書,那本書被評為了 2000 年十大垃圾書第四。吃早飯時,她看到一整版的報紙都在批評自己,她沒有惱怒,而是很開心地和母親說:「媽,你看我紅了。」後來蔣方舟意識到,外界的報道和自身的生長是撕裂的。她有一些微小的怨恨,但並不因為自己,她只是覺得抱歉:「僅僅是因為家裏有一個人寫作,他們(家人)就要被別人不公平地評價,我覺得我剝奪了他們的人生。」
不過這些並沒有影響蔣方舟的選擇,她必然、也必須會成為一名作家。2012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她進入【新周刊】成為副主編,她終於脫離學生的身份,開啟自由寫作的生涯。當時二十歲出頭,她希望能一直維持在那個狀態,做一名並不清貧的女學生。「所謂女學生,就是永遠在一個學習的過程中,沒有被那種特別功利和世俗的東西所左右,不斷地在偵錯自己的作品和時代的適配度。」

幾年時間裏,蔣方舟出版了幾本小說和隨筆,也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創作母題。「這確實是一個摸索的過程,我現在還是一個在成長期的作家。」
蔣方舟的生活與大部份人想象中的都不一樣。她沒有太多朋友,也沒看過一場演唱會,張愛玲的作品貫穿了她整個閱讀史,以至在日常中,她都不太喜歡那種特別深厚的感情。每天上午十點,她會帶一個番茄鐘到咖啡館寫作,一周六天,每半個小時,休息五分鐘。她不想隔絕那種嘈雜的環境,甚至在嘈雜中,她反而感覺穩定舒適。「我的寫作類別到底是什麽,這種東西靠想象是想不成的。所以到咖啡廳時我需要旁邊的人,我聽到他們在聊日常的事情,反而建立起我跟這個世界的勾連,而不是讓我僅僅停留在我的環境當中。」

02 「文學提供一種目光」
蔣方舟很快到了 30 歲,也很快超過了 30 歲。
再看 11 歲時的筆記,蔣方舟自己都恍惚:小時候都在想什麽呀?我太奇怪了。她寫要錢首先要不擇手段,因為不會寫「擇」,她用「折」來替代。

「年輕的時候很容易把人生理解視為那種大鳴大放的高光時刻,但是過了 30 歲之後,你就真的發現生活變成了一個沒有那麽光鮮亮麗,但是更為堅固的東西。」相比於年輕的狀態,蔣方舟反而更願意以中年人自居。雖然還沒到四十,但她已經提前作好準備——她發現,假如內心有一件很堅定的事,那麽中年恰好是最適合付諸實踐的年紀。
「這可能是寫作給我帶來的,任何的自欺欺人都沒有辦法進入到寫作當中。」在蔣方舟看來,寫作是一個不斷向內剖析自己的過程,因此一切都要在誠實的基礎上進行,「對自己誠實,對自己的年齡誠實,對自己的衰老誠實,對自己對孤獨的恐懼誠實,對死亡的恐懼誠實。」
文學構建了蔣方舟的價值觀,也拓展了她生命的寬度與厚度。在【主人公】一書中,與她相伴的是卡夫卡、阿赫瑪托娃、馬奎斯和伍爾夫。「文學不提供正能量,不提供‘腹有詩書氣自華’的美容美發,它只能提供一種目光。」
蔣方舟在文學上最喜歡的一個故事由契科夫所寫:有個士兵長得不好看,也不受女性歡迎,有一天在一個舞會上,他無意間走錯了房間,一個女人沖出來,在士兵臉上留下了一個吻。這是士兵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女人親吻。他茶飯不思,終於決定和朋友講述這個吻,他以為故事會被敘述得很長,結果不到一分鐘就講完了。
蔣方舟認為,這個故事恰好揭示了生活與文學的關系:「我們在生活中就跟那個士兵一樣,經歷了很多不可被遺忘的瞬間,可只有當契科夫描述這個吻的時候,它才有當時窗外丁香花的味道,有圓舞曲的音樂,有女人裙擺窸窸窣窣的聲音,這個吻才變得如一個世紀那麽漫長、那麽重要。」
最近,蔣方舟開始了新的長篇創作,題材聚焦在母女關系的議題。主人公在十八歲以前和蔣方舟有相同的人生,不過之後她沒有繼續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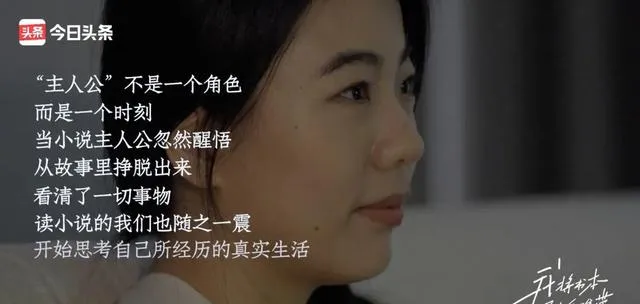
這是蔣方舟的平行世界,也是文學給予她的另一種可能:既然現實是確定的,那麽虛構便是無限的。「‘主人公’不是一個角色,而是一個時刻。當小說主人公忽然醒悟,從故事裏掙脫出來,看清了一切事物,讀小說的我們也會隨之一震,並開始思考自己所經歷的真實生活。」

上 今日頭條
搜尋 「我將書本隨身攜帶」 或 「以書之名」
來了解他們「隨身攜帶的書籍」,閱讀、創作及日常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