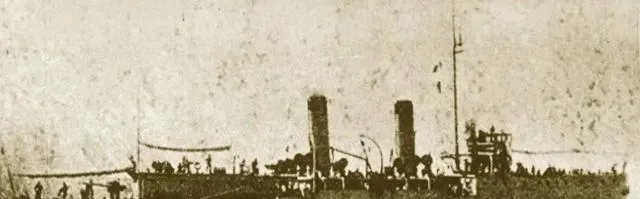
1926年3月20日在廣州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撲朔迷離。它的許多疑團至今尚未解開。本文擬探討這一事件發生前後的真實過程,以進一步揭開中山艦事件之謎。
一、「三·二〇」之前蔣介石的心理狀態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曾多次談到有關經過,但是,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6月28日,他在孫中山紀念周上演說稱,」若要三月二十日這事情完全明白的時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記和給各位同誌答復質問的信,才可以公開出來。那時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於天下了。」現在,該是對這樁公案徹底清理的時候了。下面,就我們所能見到的蔣介石這一時期的部份日記及有關信件、資料,對它進行一次考察。
根據日記、信件等資料,自1926年1月起,蔣介石和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以及汪精衛之間的矛盾急劇尖銳。先是表現在北伐問題上,後又表現在黃埔軍校和王懋功第二師的經費增減問題上。
1925年末,蔣介石從汕頭啟程回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張立即北伐。12月28日日記雲,「預定明年8月克復武漢」。1926年1月4日,他在國民政府春酌中發表演說,」從敵人內部情形看去,崩潰一天快似一天。本黨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將軍閥一概打倒,直到北京」。兩天後,他在向大會所作的軍事報告中又聲稱,「再用些精神,積極整頓,本黨的力量就不難統一中國」,「我們的政府已經確實有了力量來向外發展了」。季山嘉反對蔣介石立即北伐的主張。他在黃埔軍校會議上以及在和蔣介石的個別談話中,都明確表示過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從顧問團寫給蘇聯駐華使館的報告中可以知其梗概。該報告認為:「國民黨中央缺乏團結和穩定。它的成員中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成份,經常搖擺不定」;又說,「軍隊缺乏完善的政治組織,將領們個人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在有利的情況下,他們中的部份人可能反叛政府,並且在國民黨右翼的政治口號下,聯合人口中的不滿成份。另一方面,國民革命軍何時才能對北軍保持技術上的優勢還很難說。當然,革命軍的失敗將給予廣州內部的反革命以良機」。檔未署名,但季山嘉身為顧問團團長,報告顯然代表了他的意見。據此可知,季山嘉和顧問們認為,由於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北伐應該從緩。然而,蔣介石容不得反對意見,二人的裂痕由此肇端。
但是,這一時期,蔣介石與季山嘉之間的關系還未徹底破裂。1月中旬,奉、直軍閥在華北夾攻馮玉祥的國民軍。為此,季山嘉提出兩項建議:1.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國民軍;2.蔣介石親赴北方練兵。其地點,據說是在海參崴。對這兩項建議,汪精衛贊成,蔣介石最初也同意。1月20日日記雲:「往訪季山嘉將軍,商運兵往天律援助事。」28日日記又雲:「往訪季山嘉顧問,研究北方軍事、政治進行。余實決心在北方覓得一革命根據,其發展效力必大於南方十倍也。」然而,蔣介石很快就改變了態度。2月6日,軍事委員會決議黃埔軍校經費30萬,王懋功第二師經費12萬元。7日,軍校經費減至27萬元,王懋功第二師的經費則增至15萬元。此事引起蔣介石的疑忌,懷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當日,蔣介石和季山嘉進行了一次談話。從有關資料看,季山嘉擔心中國革命重蹈土耳其的復轍,對國民革命軍軍官的素質表示不滿,對蔣介石也有委婉的批評。蔣介石「意頗郁郁」,抱怨蘇俄顧問「傾信不專」,在日記中說:「往訪季山嘉顧問,談政局與軍隊組織,語多規諷,而其疑懼我之心,亦昭然若揭」,季山嘉覺察到了蔣介石的不滿,曾於事後立即向汪精衛表示:「我等俄國同誌,若非十二分信服蔣校長,則我等斷不致不遠萬裏而來,既來之後,除了幫助蔣校長,再無別種希望。」又稱:「至於其他一切商榷,我等既意存幫助,則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正由十二分信服,故如此直言不隱。若蔣校長以為照此即是傾信不專,則無異禁我等不可直言矣」。季山嘉的這一態度,柔中有剛,一方面表示「信服」蔣校長,「幫助」蔣校長,另一方面又毫不妥協地聲明,在有不同意見時應該「直言不隱」。汪精衛隨即於8日致函蔣介石,將季山嘉的上述表態源源本本地告訴了他。蔣介石的直接反應是,決定辭去一切軍職。8日,蔣介石表示不就軍事總監一職;9日,呈請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職務,並草擬通電稿;11日日記提出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積極進行,沖破難關」,一條是「消極下去,減輕責任,以為下野地步」,並雲:「蘇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懷,然亦何為而然?」13日,日記中突然有了準備赴俄的記載,「如求進步,必須積極,否則往莫斯科一遊,觀察蘇聯情況,以資借鏡」。
在蔣介石與季山嘉的矛盾中,汪精衛支持季山嘉。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蔣介石提出北伐問題,汪精衛曾表示同意,並開始準備經費,但不久轉而贊同季山嘉的意見。二人未就北伐問題作出任何決定。2月8日,汪精衛在向蔣介石轉述季山嘉態度的信函中,又盛贊季山嘉「說話時,一種光明誠慤之態度,令銘十分感動」,要蔣介石創造條件,使季山嘉等能夠「暢所欲言,了無忌諱,了無隔閡」。對於蔣介石的辭職,汪精衛則一再挽留,2月9日函雲:「廣州衛戍司令職,弟實不宜辭,是否因經費無著?此層銘昨夜曾想及,故今晨致弟一電,請開預算單」。12日再致一函雲:「以後弟無論辭何職,乞先明以告我。如因兄糊塗,致弟辦事困難,則兄必不吝改過」。14日,汪精衛並親訪蔣介石,從上午一直談到晚上,勸他打消辭意。但是,蔣介石毫不動心。19日,蔣介石向汪精衛正式提出」赴俄休養」一事。當日日記雲:「余決意赴俄休養,研究革命政理,以近來環境惡劣,有加無已,而各方懷疑漸集,積怨叢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個人意向亦難確定,再安樂非可與共,劬勞訖可小休。綜此數因,不得不離粵遠遊也。」同日,季山嘉到蔣介石寓所存取,談話中,蔣介石透露了「赴俄」的意圖,並且觀察季山嘉的反應,於日記中寫下了「狀似不安」四字。大約在此期間,蔣介石擬派邵子力赴北京,請鮑羅廷回粵。隨後又致電鮑羅廷,要求撤換季山嘉。
2月24日,國民政府成立兩廣統一委員會,任命汪精衛、蔣介石、譚延闿、朱培德,李濟深、白崇禧為委員,將廣西軍隊改編為第八軍、第九軍,以李宗仁、黃紹竑為軍長。此事進一步引起蔣介石的疑忌,他認為廣東有六個軍,照次序,廣西軍隊應為第七、第八軍。但是,現在卻將第七軍的建制空下來,必然是季山嘉企圖動員王懋功背叛自己,然後任命他為第七軍軍長。於是,蔣介石於26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王懋功扣留,任命自己的親信劉峙為第二師師長。當日日記雲:「此人(指王——筆者)狡悍惡劣,唯利是視,「其用心險惡不可問,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決心驅除之」。次日,將王押送赴滬。
王懋功政治上接近汪精衛,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蔣介石驅王之後,覺得心頭一塊石頭落了地。當日在日記中得意地寫道:「凡事應認明其原因與要點。要點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一月以來,心境時刻戰兢,至此稍獲安定,然而險危極矣。」他找到汪精衛,聲言季山嘉「專橫矛盾,如不免除,不惟黨國有害,且必牽動中俄邦交。」又稱:「如不準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俄。」下午,季山嘉在和汪精衛議事時,表示將辭去顧問職務。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此稱:「不知其尚有何作用也?」
盡管蔣介石在驅除王懋功問題上取得了勝利,但仍然疑慮重重,覺得自己處於極為危險的境地。3月5日日記雲:「單槍片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環境也。」3月7日,劉峙、鄧演達二人告訴蔣介石,有人以油印傳單分送各處,企圖掀「反蔣」運動,這更增加了蔣介石的危險感,覺得有人在陷害他,企圖把他搞掉,3月10日日記雲:「近日反蔣運動傳單不一,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亦漸明顯,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誌益豎矣。」這時,蔣介石和季山嘉的矛盾更形尖銳,以致於公然「反臉」。12日,季山嘉和他討論北伐問題,他居然「力辟其謬妄」。蔣介石曾同意季山嘉由海路運兵往天津的計劃,此時卻認為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計」,與孫中山的「北伐」之誌完全「相反」。對於季山嘉勸他往北方練兵的建議,更認為自心懷叵測,是有意設法使他離開廣東,「以失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赴俄休養」本來是蔣介石自己提出的,而當汪精衛為了緩解他和季山嘉的矛盾,同意這一要求,催其「速行」時,蔣介石卻又恐懼起來。3月14日,蔣介石和汪精衛談話後,在日記中寫道:「頃聆季新言,有諷余離粵意,其受饞已深,無法自解,可奈何!」。3月15日日記雲:「憂患疑懼已極,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觀色,竟困於垓心[下],天下事不可為矣!」。這一時期,他和秘書陳立夫的赴俄護照也得到批準,就使他更加惶惶然了。
正是在這種狀態下,右派乘虛而入,利用蔣介石多疑的心理,制造謠言和事端,以進一步挑起蔣介石和汪精衛、季山嘉以及共產黨人之間的矛盾。

二、中山艦調動經過
要揭開中山艦事件之謎,還必須查清中山艦調動經過。
根據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員黎時雍的報告,事件的開始是這件的:「18日午後6時半,孔主任因外洋定安火輪被匪搶劫,飭趙科長速派巡艦一只,運衛兵16名前往保護。職奉令後,時因本校無船可開,即由電話請駐省辦事處派船以應急需,其電話系由王股員學臣接。」孔主任,系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叡。趙科長,系黃埔軍校管理科科長趙錦雯。定安輪是由上海開到廣州的商輪,因船員與匪串通,在海上被劫,停泊於黃埔上遊。根據黎時雍的上述報告,可知當時調艦的目的在於保護商輪,最初並沒有打算向李之龍管轄的海軍局要艦,更沒有指定中山艦開動,所求者不過「巡艦」(巡邏艇)一只,衛兵16名而已。只是由於黃埔軍校「無船可開」,才由黎時雍自作主張,向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請求「速派船來,以應急需」。
駐省辦事處接電話的是交通股股員王學臣。他事後的陳述是:「3月18日午後6時30分,接駐校交道股黎股員時雍電話雲:因本晚由上海開來定安商輪已被土匪搶劫,現泊黃埔魚珠上遊。奉孔主任諭,派衛兵16名,巡艦一只,前往該輪附近保護,以免再被土匪搶劫。職因此時接電話聽不明了,系奉何人之諭,但有飭趙科長限本晚調巡洋艦一二艘以備巡查之用。職當即報告歐陽股長······想情系教育長之諭,故此請歐陽股長向海軍局交涉。歐陽股長,系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根據上述報告可知,向海軍局要艦的是王學臣,所謂鄧演達」教育長之諭」則是因為電話聽不清,「想情」之故。至於艦只規模,也因「想情」之故,由「巡艦」而上升為「巡洋艦一二艘」了。
歐陽鐘得到王學臣的報告後,即親赴海軍局交涉。當時,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因公外出,由作戰科科長鄒毅面允即派艦只一二艘前往黃埔,聽候差遣。此後,據歐陽鐘自稱,他「於是即返辦事處」。而據海軍局的【值日官日記】則稱:「因李代局長電話不通,無從請示辦法,故即著傳令帶同該員面見李代局長,面商一切」。又據李之龍夫人報告:當夜,有三人到李之龍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龍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聲稱:「奉蔣校長命令,有緊急之事,派戰鬥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同時又交下作戰科鄒科長一函,中稱:已通知寶壁艦預備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兩艦可派,請由此兩艦決定一艘。李之龍歸來閱信後,即去對門和自由艦艦長謝崇堅商量,因自由艦新從海南回省,機件稍失真壞,李之龍決定派中山艦前往,當即下令給該艦代理艦長章臣桐。同夜10時余,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秘書季方接到歐陽鐘電話,據稱:向海軍局交涉之兵艦,本晚可先來一艘(即寶壁艦),約夜12時到埔,請囑各步哨不要誤會。季方當即詢問因何事故調艦,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稱:系由本校黎股員時雍電話囑咐,請保護商輪之用。
19日晨6時,寶壁艦出口。7時,中山艦出口,同日晨,海軍局參謀廳作戰科科長鄒毅要求歐陽鐘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鐘照辦。此函現存,內稱:「頃接黎股員電話雲:奉教育長諭,轉奉校長命,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兵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周迅速派兵艦兩艘為要。」中山艦於上午9時開抵黃埔後,代理艦長章臣桐即到軍校報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黃珍吾代見。章出示李之龍命令,略稱:派中山艦火急開往黃埔,歸蔣校長調遣。該艦長來校,乃為請示任務。並稱:若無十分重要事情,則給其回省,另換一小艦來候用。黃珍吾當即報告鄧演達,鄧謂並無調艦來黃埔之事,但他「公事頗忙」,命黃轉知該艦長聽候命令。
當時,以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聯使團正在廣州考察。中山艦停泊黃埔期間,海軍局作戰科鄒科長告訴李之龍,因俄國考查團要參觀中山艦,俄顧問詢問中山艦在省河否?李之龍即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告以俄國考查團參觀,可否調中山艦返省,得到蔣介石同意,然後李之龍便電調中山艦回省。
中山艦的調動經過大體如上。這一經過至少可以說明以下幾點:
1、中山艦駛往黃埔並非李之龍「矯令」,它與汪精衛、季山嘉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份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
2、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調艦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
3、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歐陽鐘,他明明去了李之龍家裏,卻在事後隱匿有關情節;他在海軍局和李之龍夫人面前聲稱「奉蔣校長命令」調艦,而在給作為校長辦公廳秘書的季方的電話裏,卻只能如實陳述;在給海軍局的公函裏,他清楚地寫著要求「迅速派兵艦兩艘」,而在事後所寫的報告和供詞中,又謊稱只是「請其速派巡艦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詞,因此,歐陽鐘是中山艦事件的一個重要幹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黃人,1925年5月任軍校代理輜重隊長,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後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他是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了解了他的這一身份,將有助於揭開中山艦事件之謎。

三、蔣介石的最初反應和「三·二O」之後的日記
據蔣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誌」在和蔣介石見面時曾問:「你今天黃埔去不去?」蔣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別之後,到九點、十點時,「那同誌」又打電話來問:「黃埔什麽時候去?」如此一連問過三次。蔣介石覺得有點「稀奇」了:「為什麽那同誌,今天總是急急的來問我去不去呢?」便答復道:「我今天去不去還不一定。」蔣介石所說的「有一同誌」,他當時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實際上指的是汪精衛。到下午一點鐘的時候,蔣介石又接到李之龍的電話,請求將中山艦調回省城。預備給俄國參觀團參觀。蔣介石當即表示:「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麽呢?」此後,蔣介石愈益感到事情蹊蹺:「為什麽既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而他要開回來為什麽又要來問我?」「中山艦到了黃埔,因為我不在黃埔,在省裏,他就開回來省城。這究竟是什麽一回事。」當日,蔣介石有這樣一段日記:「上午,準備回汕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發沖冠。下午五時,行至半途,自忖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否則國魂銷盡矣。終夜議事。四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布陷我也。」蔣介石的這一段日記提出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他在判斷所謂「擺布陷我’的陰謀之後,最初的反應是離開廣州退到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所在地汕頭。已經行至半途了,才決定返回,對中山艦采取鎮壓措施。蔣介石的這一段記載,證以陳肇英、陳立夫、王柏齡等人的回憶,當是事實。陳肇英時任虎門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憶說:3月19日,蔣介石專使密邀陳肇英、徐桴(第一軍經理處處長)、歐陽格三人籌商對策。「當時蔣校長顧慮共產黨在黃埔軍校內,擁有相當勢力,且駐省城滇軍朱培德部,又有共黨朱德統率之大隊兵力,且獲有海軍的支持,頗非易與,主張先退潮、汕,徐圖規復。我則主張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並請命令可靠海軍,集中廣九車站待變,以防萬一。初時蔣校長頗為躊躇,且已購妥開往汕頭之日輪‘廬山丸’艙位。迨車抵長堤附近,蔣校長考慮至再後,終覺放棄行動,後果殊難把握,亟命原車馳回東山官邸,重行商討,終於采納我的建議,布置反擊」。陳立夫則稱:「汪先生謀害蔣先生」,「蔣先生發覺了這個陰謀,很灰心,要辭職,要出亡」。19日那天,竟直檢了行李,帶他坐了汽車到天字碼頭,預備乘船走上海。在車上,他勸蔣先生幹,「有兵在手上為什麽不幹?」又稱:「昔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以成帝業。當機立斷,時不可失。退讓與妥協,必貽後悔」。汽車到了碼頭,「蔣先生幡然下決心,重復回到家中發動三月二十日之變。」陳肇英和陳立夫的回憶在回汕頭或去上海上雖有差異,但在蔣介石一度準備離開廣州這一點上卻和蔣介石的日記完全一致。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確實相信有一個「擺布」、「陷害」他的陰謀,否則,他是不必在自己的親信面前演出這一場戲的。
關於此,還可以在蔣介石「三·二〇」之後的日記和其他資料中得到證明。
20日晨,根據蔣介石命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城戒嚴;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余人;占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與此同時,蘇俄顧問也受到監視,衛隊槍械被繳。21日,汪精衛致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請病假,聲稱「甫一起坐,則眩暈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請假療治」,所有各項職務均請暫時派人署理。當日傍晚。蔣介石去探視汪精衛,日記雲:「傍晚訪季新兄病。觀其怒氣勃然,感情沖動,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勢力之惡劣,使人無道義之可言也」。
22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汪精衛寓所召集臨時特別會議。會議上,汪精衛對蔣介石擅自行動表示了不滿,會議決定:「工作上意見不同之蘇俄同誌暫行離去」;「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李之龍受特種嫌疑,應即查辦」。會後,汪精衛即隱居不知去向。25日,蔣介石日記雲:「4時後回省,與子文兄商議覓精衛行蹤不可得。後得其致靜江兄一書,謂余疑他、厭他,是以不再負政治之責任。彼之心跡可以知矣。為人不可有虧心事也」。此後數日內,蔣介石日記充斥了對汪精衛的指責。
3月26日日記雲:「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精衛如果避而不出,則其陷害之計,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記雲:「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繼以利用教育長陷害又不成,毀壞余之名節,離間各軍感情,鼓動空氣,謂余欲滅某黨,欲叛政府。嗚呼!抹煞余之事業,余所不計,而其抹煞總理人格,消滅總理系統,叛黨賣國,一至於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記雲:「接精衛兄函,似有急急出來之意,乃知其尚欲為某派所利用,不惜斷送黨國也。嗚呼!是何居心歟!」
蔣介石的這些日記表明,他當時確實認為,「擺布」、「陷害」他的陰謀的核心人物是汪精衛。4月20日,蔣介石在演說中聲稱:「有人說,季山嘉陰謀,預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黃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艦上,強逼我去海參崴的話,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過有這樣一回事就是了」。話雖然說得有點遊移,但卻道出了他的心病。
汪精衛於政治委員會臨時特別會議之後隱居不出,據陳璧君說,一是為了「療病」,一是為了讓蔣介石「反省一切」。但蔣介石除了裝模作樣地給軍事委員會寫過一個呈子,自請處分外,並無什麽象樣的「反省」行為。其間,汪精衛讀到了蔣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蔣介石毫不掩飾地表露了他對汪精衛的疑忌,於是汪精衛決定出國。3月31日汪精衛致函蔣介石,內稱:「今弟既厭銘,不願與共事,銘當引去。銘之引去,出於自願,非強迫也」。蔣介石於4月9日復函雲:「譬有人欲去弟以為快者,或有陷弟以為得計者,而兄將如之何?」又稱:「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無負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實證之,其果弟為人間乎?抑兄早為人間乎?其果弟疑兄而厭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厭弟乎?」這封信也說明了蔣介石當時認為,汪精衛受人離間,懷疑並厭棄自己,和其日記是一致的。
此外,還可以考察一下蔣介石這一時期的精神狀態。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見蔣介石,質問他究竟想幹什麽,派軍隊到處戒嚴,並且包圍罷工委員會,是不是發了瘋,還是想投降帝國主義?據記載,蔣介石「竟象小孩子般伏在寫字台上哭了」。陽翰笙也回憶說,當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黃埔開會,見蔣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黃」,作報告時講到「情況復雜,本校長處境困難時,竟然哭起來了」。鄧演達也因為蔣介石「神色沮喪」,甚至關照季方:「要當心校長,怕他自殺」。這種精神狀態,從蔣介石認為自己處於被「擺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許易於理解。
盡管蔣介石內心對汪精衛恨之入骨,但是,汪精衛當時是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公認的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蔣介石這時還不具備徹底倒汪的條件。於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眾面前透露某些情節,以說明有人企圖陷害他;另一方面,卻又不能全盤托出他的懷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們在他死後看日記者,蓋為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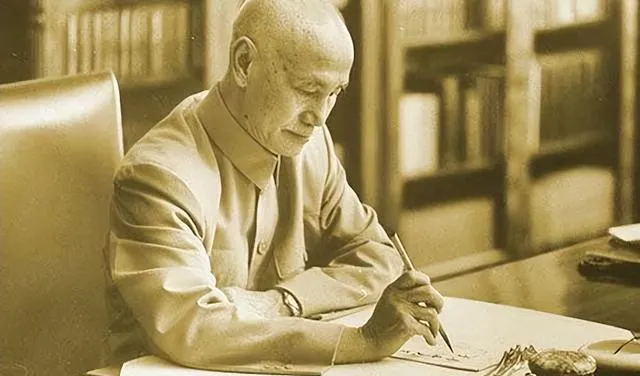
四、西山會議派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把戲」
據陳公博說,鄒魯在1930年曾告訴他:當時,西山會議派謀劃「拆散廣州的局面」,「使共產黨和蔣分家」,鄒魯等「在外邊想方法」,伍朝樞「在裏頭想辦法」,於是,由伍朝樞出面,「玩」了下面這樣一個「小把戲」:有一天,伍朝樞請俄國領事吃飯,跟著第二天便請蔣介石的左右吃飯。席間,伍朝樞裝著不經意的樣子說:昨夜我請俄國領事食飯,他告訴我蔣先生將於最近期內往莫斯科,你們知道蔣先生打算什麽時候起程呢?事後,蔣介石迅速得到了報告,他懷疑「共產黨要幹他」,或者汪精衛要「趕他」,曾經兩次向汪精衛試探,表示於統一東江南路之後,極端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暫休息。一可以和俄國當局接頭,二可以多得些軍事知識。在第二次試探時,得到汪精衛的同意。自此,蔣介石即自信判斷不錯。他更提出第三步試探,希望陳璧君和曾仲鳴陪他出國。陳璧君是個好事之徒,天天催蔣介石動身。碰巧俄國有一條船來,並且請蔣介石參觀,聽說當日蔣介石要拉汪精衛同去,而汪因已參觀過,沒有答應,於是蔣便以為這條船是預備在他參觀時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決定反共反汪。「這是三月二十日之變的真相」。
這段記載說明了伍朝樞在挑起蔣介石疑懼心理過程中的作用。應該說,陳公博沒有捏造鄒魯談話的必要。但是,我們還必須結合其他材料加以驗證。
1、這一段話的核心是蔣介石懷疑共產黨和汪精衛要「幹他」或「趕他」,以自請「赴俄休養」作試探,得到汪精衛同意,便進一步增強了他的懷疑。此點和前引蔣介石日記大體一致。
2、陳孚木在【國民黨三大秘案】一文中說:其時,伍朝樞知道有一艘裝載軍械送給黃埔軍校的俄國商船,不久會到廣州,便編造「故事」說:「蘇聯從蔣介石與俄顧問季山嘉的不和諧,判定蔣是反革命分子,已得汪精衛的同意,不日以運贈軍械為名,派遣一只商船來廣州,即將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受訓。」「他把這‘故事’作為很機要秘密的訊息,通傳給在上海西山會議派中央的許崇智、鄒魯等幾個廣東人,很快便傳到蔣介石在滬的親密朋友如戴季陶、張靜江、陳果夫等幾個人耳朵裏了」。陳孚木的這一段記載認定伍朝樞是編造謠言的主要人物,謠言的核心情節是利用俄船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陳並將這一謠言通傳給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凡此種種,均可與鄒魯對陳公博所述相印證。陳孚木當時是【廣州民國日報】的總編輯,和國民黨上層人物廣有聯系。他看過中山艦事件制造者歐陽格1927年寫的有關回憶稿,所述自然具有相當的可靠性。
3、1926年4月1日,柳亞子致柳無忌函雲:「反動派陷害共產派是確實的,李之龍是一個共產派的軍人(屬於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而蔣部下很有孫文主義學會的人在那裏搗鬼,他們制造一個假命令,叫李把中山艦開到黃埔去,一方面對蔣說。李要請你到莫斯科去了,蔣大怒,即下令捕李」。柳亞子所述的核心情節是,有人造謠,以李之龍將劫蔣「去莫斯科」,煽動蔣介石反共,此點和鄒魯,陳孚木所述基本一致。柳亞子是國民黨元老,各方面交遊頗廣,他的這一段話不會沒有來歷。回函中,柳亞子又說:「在兩星期前,沈玄廬(定一)告訴陳望道。廣州不出十日,必有大變,所以反動派的陰謀是和上海通氣的」。沈定一是西山會議派的重要人物,當時在上海, 如果他不了解伍朝樞「玩的小把戲」,是不會作出「廣州不出十日,必有大變」的判斷的。6月4日,陳獨秀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裏也說:「先生要知道當時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國大會,和廣東孫會互相策應,聲勢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們已得意揚言,廣州即有大變發生。先生試想他們要做什麽?」這些材料,都可以反證陳孚木所述:伍朝樞曾將他編造的故事,通傳給在上海的兩山會議派中央。
4、鄧演達曾告訴季方,蔣介石之所以「倉皇失措」,是因為「得到密報」:「共產黨利用其海軍局長李之龍的關系,將中山艦露械升火,與黃埔鄧演達聯合行動,圖謀不軌」。此說雖未提到伍朝樞,但在指出蔣介石「得到密報」這一點上,仍有可資參證之處。
從1926年1月起,西山會議派的鄒魯等人就在廣州和香港散布謠言。第一次說李濟深陰謀倒蔣,廣州並行現以四軍名義指蔣為吳佩孚第二,想做大軍閥的傳單;第二次說第一軍要繳四軍的械;第三次說,二、三、四、五各軍與海軍聯合倒蔣;第四次說,蔣介石對俄械分配於各軍不滿,將驅逐俄顧問全體回國;第五次說,蔣介石倒汪。如此等等。很顯然,散布這些謠言的目的在於制造廣東國民政府內部的不和,煽起蔣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事實上,它們也確實起了作用。這一點,前引蔣介石日記已有充分的證明。蔣介石之所以在那樣一個特定時刻對中山艦采取鎮壓措施,應該說,西山會議派和伍朝樞的謠言起了重要作用。
當然,鄒魯把中山艦事件完全說成是西山會議派和伍朝樞的「功勞」也並不全面。其中還有柳亞子、陳獨秀所指出的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作用。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發端於1925年6月的中山學會,其核心人物為王柏齡、賀衷寒、潘佑強。這一組織成立後,即與西山會議派相勾結,陰謀反對國共合作。其間的聯絡人就是時任國府委員,兼任廣州市市政委員會委員長的伍朝樞。李之龍說:「這種組織(指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筆者)在廣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對抗青年軍人聯合會,其後經伍朝樞、吳鐵城之介紹,遂與西山會議派結合,遂受其利用而擴大為倒汪、排共、仇俄之陰謀。他們在廣州發難,領過了上海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數萬元之運動費,陳肇英領了一萬五千元,歐陽格領了五千元」。中山艦事件發生前,廣州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異常活躍。王柏齡很早就到處散布汪精衛反蔣。2月22日,蔣介石日記中有王柏齡進讒的記載。3月17日早晨,王柏齡在黃埔軍校內又散布說:「共產黨在制造叛亂,陰謀策動海軍局武裝政變」。王柏齡並在他的部隊內,對連以上軍官訓話,要他們「枕戈待旦」,消滅共產黨的陰謀。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上午議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以佛入地獄耶!」顯然,蔣介石的這段日記和王柏齡的謠言之間有著某種聯系。正是在這一狀況下,作為孫文主義學會成員之一的歐陽鐘出面假傳蔣介石命令,誘使李之龍出動艦只,以便和王柏齡的謠言相印證。他的活動是整個陰謀的組成部份。關於此點,如果我們將幾個有關回憶錄綜合起來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陳孚木寫道:「那時伍朝樞所說的俄國商船已經到達,起卸軍械之後,停在黃埔江面。一連幾天,沒有什麽動靜。於是,王柏齡便與歐陽格商量,決定「設計誘使中山艦異動」。章臣桐寫道:「在三月十八那一天,歐陽格打電話給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副官歐陽鐘(歐陽格之侄),叫他用辦事處的名義向海軍局要一只得力兵艦開往黃埔,說是校長要的。所謂得力的兵艦,即暗指中山艦而言。」在章臣桐接到李之龍命令,上艦升火試笛之後,「歐陽格就在蔣的面前報告說:‘中山艦已出動,正在開往黃埔,聽說共產黨要搶黃埔的軍火’」。自由艦艦長謝崇堅也有類似回憶。他說;「三月十八日歐陽格偵知中山艦上發生混亂,戒備不嚴,有機可乘,密令歐陽鐘偽稱接到校本部電話,通知海軍局立派一艘得力軍艦,駛往黃埔聽用。據說十九日上午中山艦在東堤起錨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立即向蔣介石控告,說海軍李之龍異動,已出動中山艦要逮捕校長,奪取軍火」。這就很清楚了: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之後,一面唆使歐陽鐘矯令,一面向蔣介石謊報,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多年以後,王柏齡曾得意地說:「中山艦雲者,煙幕也,非真歷史也,而其收功之總樞,我敢說,是孫文主義學會」。這不啻是自我招供。

五、偶然中的必然
就蔣介石誤信伍朝樞、歐陽格等人的謠言來說,「三·二〇」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鬥爭和蔣介石的思想狀況來說,又有其必然性。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發展。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左派的勝利。會議代表228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168人,中派65人,右派僅占45人。吳玉章任大會秘書長,實際上主持會議。會議透過的宣言進一步闡明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堅持了「一大」的革命精神。會議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中,共產黨員占7人,國民黨左派占15人。在隨後建立的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中,都由共產黨員擔任領導工作。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中大約已有一千余名共產黨員。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一軍三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九個團的黨代表中,七個是共產黨員。此外,中國共產黨在廣東的群眾基礎也大為加強。當時,有組織的工人隊伍約十余萬,農會會員約60余萬,其中工人武裝糾察隊二千余人,農民自衛軍三萬余人。
蘇俄顧問團這一時期也加強了自己的地位和影響。顧問團向蘇俄駐華使館報告說:「總參謀部是軍事委員會的專門組織。羅加喬夫,我們的軍事指揮者(團長助理)實際上擔當總參謀長」;又說:「我們的顧問事實上是所有這些部門的頭頭,只不過在職務上被稱為這些部門首領的顧問。[1925年]12月末,我們的顧問甚至占有海軍局長(斯米諾夫)和空軍局長(列米)的官方位置」。該報告又稱:「現存的國民黨是我們建立起來的。它的計劃、章程、工作都是在我們的政治指導下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標準制訂的,只不過使它適合中國國情罷了。直到最近,黨和政府一直得到我們的政治指導者的周密的指導,到目前為止,還不曾有過這樣的情況,當我們提出一項建議時,不為政府所接受和實行」。
汪精衛也表現為前所未有的左傾。據張國燾回憶:他「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前夕,莫斯科來了一個很長的報告,內容為反對帝國主義,汪精衛還沒有讀完就說內容很好,可作大會宣言的資料。在會議召開期間,汪精衛多次強調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在歷次戰役中,熱血流在一起,凝結成一塊,早已不分彼此,既能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為同一目的而生存下去。在選舉中央委員以前,他預擬了一份名單和中共商量,其中左派以及和汪有關系的人占多數。1926年2月1日,他在中執會常委會會議上,提議任命周恩來為第一軍副黨代表,李富春為第二軍副黨代表,朱克靖為第三軍副黨代表。5日,又提議請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2月22日,他在紀念蘇俄紅軍成立八周年聯歡會上,繼季山嘉之後發表演說,聲稱:「吾人對於如師如友而助我的俄同誌,真不知如何表示其感激之情,惟有鐫之中心而已」。對於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之間的沖突,他也鮮明地左袒,曾命令王懋功「嚴厲制止」孫文主義學會的遊行。3月初旬,他又召集兩會會員訓話,激烈地批判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共傾向,曾稱,「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殺共產黨,中國革命未成,又欲殺共產黨乎?」
國民黨右派不能容忍共產黨力量的發展和蘇俄顧問影響的增強,不能容忍汪精衛的左傾。西山會議派稱:「現在的國民政府,名義上是本黨統治的,事實上是被共產黨利用的。」又稱:「俄人鮑羅廷操縱一切」,「軍政大權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蔣介石雖然因依靠蘇俄供應軍械而仍然主張聯俄,對共產黨也時而表現出願意合作的姿態,但在內心裏,卻早已滋生出強烈的不滿。3月8日日記雲:「上午與季新兄商決大方針。余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雲:「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份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4月9日,蔣介石在復汪精衛函中也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余地。」這一切都說明了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制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