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豐

作者簡介
周豐
藝術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審美心理學、神經美學。
摘 要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雖新,但「新文科」本身的理念卻有著悠久的傳統,仍為「人文」之慣性。神經美學作為一種跨學科研究,興起時是「新理科」的,但在發展過程中卻轉化成為典型的「新文科」實踐。神經美學以「自然」作為視野和方法,考察藝術審美感知在「物理、生理與心理」三個層面的特異性,其悠久的藝術心理學傳統,成為神經美學得以對藝術理論進行拓展與深化的學科立場。「動作想象」是審美體驗的核心能力,情感與認識均是透過動作想象來完成的,在「有意味的形式」之中,「意味」與「形式」之間並不是一種線性關系,而是一種並置的同構關系。神經美學之所以能夠由一種方法之「用」,實作理論之「體」的建構,正是因為契合了對藝術本質的闡釋。
關鍵詞: 神經美學;藝術理論;藝術心理學;動作想象
「新文科」雖然是一個新概念,但其實踐的理念卻有著悠久的傳統。「新文科」之核心首先是「文科」。「文科」是「人文科學」(Humanitas)的簡稱,而「人文」強調的是人的自由、人的價值。「整個西方的人文傳統自始至終貫穿著‘自由’的理念,一些與‘人文’相關的詞組就是由‘自由’的詞根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文科(liberalart)等。」[1] 「science」(科學)所對應的拉丁文「scientia」的含義較為廣泛,一般指「知識」,包含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個方面。[1] 可以說,人文科學之歸旨是一種「自由的知識」,這個自由的尺度是人,是人對自由的追求,也是人的根本。
在文藝復興時期所強調的人文主義(humanism)之中,這一理念則更為突出,人文主義的核心理念為:以擺脫宗教對人的桎梏為出發點,關懷人的生存、肯定理性和科學對於消除愚昧和促進人自身發展的價值、認同人對現世而非來世幸福的追求。因此,人文主義包含科學和人文兩方面,無論是人文還是科學,都要以人為本,促進人自身價值的發展與實作。人文主義並不僅僅包含人文科學,而是涵蓋了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或者說,人文主義回到了「人文」的「自由」指稱,只要是促進人的發展,「破除」人類認識「桎梏」的,都屬於人文主義範疇。
顯然,「新文科」之「新」也是指向人之「自由」的,與「新」相對的「舊」妨礙了人的「自由」。「新文科更根本的使命在於回應新歷史條件下‘人’的觀念的變化,因為人文學科是關於‘人’的學問。新文科之所以成為一個迫切的時代課題,源於舊文科關於‘人’的理解出現了問題。」[2]「舊文科」對人的理解不再全然符合當下人的價值,「舊」與當下時代的人發生了錯位,「舊」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桎梏」,那麽,便需要「新」的視野與方法去打破這種「桎梏」。因此,新文科其實仍屬於「人文」之慣性的沖擊力。
神經美學作為興起於20世紀末的跨學科研究,可以說是「新文科」的一次典型實踐。雖然神經美學原本興起於科學,但仍屬於「人文主義」範疇,是以科學之方法破除人類認識之「桎梏」。因此,「跨學科」的本質是以問題為中心對人類認識「桎梏」的突破。「‘新文科’作為當今時代文科教育的融合創新發展,它首先意味著一種跨學科的深度交叉和融合,尤其是文科與新科技革命的融合。」[3]然而,文科與科技革命如何相融?作為一次文科與科技融合的典型實踐,我們能夠在神經美學中見出科學技術之於人文科學相融的前提和方法。並且,基於藝術理論研究的立場我們能夠看到,發端於自然科學的神經美學研究是怎樣走向了「新文科」又如何實作對藝術理論研究從「用」之方法走向「體」之理論的建構。
一、「自然」作為神經美學的方法與視野
興起於20世紀末的神經美學首先發跡於心理學、腦科學、神經科學、電腦科學等學科,後來又有哲學、人類學、藝術學等學科的加入。因此,神經美學的研究者也大多來自自然科學,帶著各自的學科背景在審視著同一個問題:人類如何感知藝術與美。研究者的不同學科背景意味著,各自的視野、方法甚至是對「藝術與美」的認識也是有差異的。然而,基於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問題以及科學的研究框架,神經美學研究興起至今呈現出明顯的科學傾向。可以說,神經美學的興起首先是「新理科」的,它並不是以人文科學的視角和視野在討論藝術,正如它的研究目的所表明的:「審美的神經生物學基礎」。那麽,今天,我們以人文科學的視角來看,它又如何成為新文科?作為從「用」的方法拓新開始的神經美學,將如何推動藝術理論「體」的建構。
即使從自然科學來看,神經美學也是一次跨學科實踐。柏拉圖曾慨嘆「美是難的」,因此,「美」的問題,無疑是各個時代人們一直關註的問題,無論是人文還是自然科學。「神經美學」這一概念的提出者薩米爾·澤基就認為:「在科學對藝術仍是知之甚少的情況下,一個科學家要去討論藝術是冒險甚至是危險的,……但這並不能成為就此望而卻步的借口。」[4]然而,冒險正是人文精神的體現,在神經美學領域裏這種精神的體現並不是孤立的。另一位神經美學家羅拔·索爾索則對審美的神經生理加工層面的缺失而感慨:「於我而言,有一些欣喜亦有一些震驚,竟然幾乎沒有一個藝術研究者註意到這一基本而又重要的‘觀看’層次。」[5]顯然,「美」作為人類的一個難題已經被「視作一個科學的概念,被提升為科學界關註的主流課題」[6]。當然,這些觀念也是時代之技術發展所賦予的,只是,對於自然科學而言,科學將如何「審美」,「藝術」又將如何呈現?
在神經美學的研究視閾中,「自然科學」不僅僅是一個學科的傳統或集合概念,而是將「自然」作為視野和方法對「人」進行再認識。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一直強調人的「類存在」,以「類存在」來確立人的特性與本質,繼而確立勞動的特性和美的特性,可以說,這些都是基於「自然」的視角。他甚至將自然視為「人的無機的身體」[7]。「人」的類屬概念本就是基於「自然」的視域而確立的神經美學將「人」作為自然的人,意味著「人」不再是自然的中心,而是物之一種,是一種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舍棄,然而,這種「舍棄」並不違背人的內容。即便是從神經生理層面來看,神經美學一直以來所要尋找的,仍是審美感知發生的「特異性」,只是,這個特異性首先是建立在人與物的同質性的基礎之上的,即在自然的視野中看待人。因此,就其方法和視野來看,神經美學研究依然包含於傳統藝術哲學的方法路徑。
但與傳統藝術理論所強調的經驗層面的審美愉悅不同的是,神經美學的實驗實證「承認審美愉悅感的物質性」[8]13。神經美學是從藝術審美感知的最外層效果「愉悅感」出發,一層層地剖析它的發生由來:審美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活動和人類的一種特殊能力,它是如何發生的。審美活動是主體與客體的互動活動,而主體的人是身心一體的,即存在心理、生理和物理三個層面。因此,主客體的互動活動意味著審美主體也具有物質性,審美愉悅的物質性包含主體與客體兩個方面,物不再是單一的物件,而是主客體統一的物質場。
因此,藝術審美感知發生的「特異性」也基於物理、生理與心理三個層面:「‘外部的’物理刺激,繼而引起‘內部的’心理回應。藝術與思維是建立在這個共同基礎之上的整體。」[5]21顯然,在神經美學看來,藝術的審美是一個由物質而精神的過程,正如加比奧·斯塔爾所指出的,神經美學之關鍵在於:「如何在物質層(神經元和神經網絡)、藝術經驗層和藝術作品層三者的鴻溝之間架構起一座橋梁。」[8]25神經美學的這種「以同求異」的原則正是其方法的具體表現,以「自然」為視野和以審美為視點就決定了神經美學研究的自下而上路徑。[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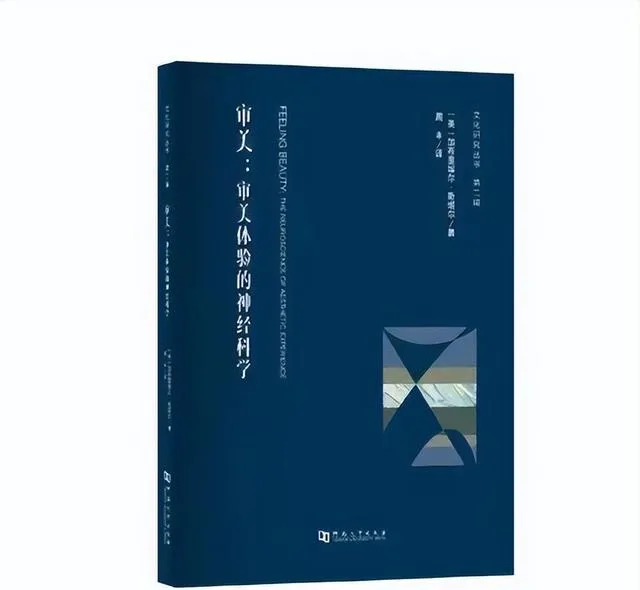
加比奧·斯塔爾: 【審美:審美體驗的神經科學】,周豐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21年
神經美學的兩個支撐性方法—量表法和腦成像技術,都是時代技術的發展而賦予的。量表法能夠多維度將個體對某個物件的態度數據化。例如,神經美學實驗中常用的黎克特量表以及PANAS情緒量表,PANAS是一種高度穩定且內部一致的情緒測量方法,能夠確定實驗中被試是否受到自身情緒的影響。而腦成像技術能夠在對大腦非損傷的情況下呈現出個體在執行某個任務時其大腦相應的活躍狀態。腦成像技術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人類的感覺系統與大腦處理資訊方式的認識。傳統對腦的創傷性研究無法真正做到對一個正常的健康人的觀察。審美發生於正常人的大腦裏,因此,研究審美時的大腦,必須以健康人為研究物件,審美也不可能從動物或死亡的腦那裏看到什麽。在研究審美時,也不允許將一個健康人的大腦解剖來觀察,但腦成像技術完全克服了這一點,它允許研究者們在不破壞人腦的同時,能夠窺探到大腦的內部。其中運用最為廣泛的有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技術(PET),核磁共振成像技術(MRI),以及腦電波誘發電位技術(ERP)等,所有這些技術都已被用於包括藝術、人臉與幾何圖式在內的視覺刺激的知覺實驗。可以說,腦成像技術是神經美學得以興起的決定性技術。
然而,方法是伴隨著問題的解決而發展完善的,這也是科學之方法對「藝術」之物件的適應。黎克特量表早在1932年就已經誕生,這也是心理學研究的常用方法,而在神經美學中,審美發生的量表判定卻是多維度的。例如,在維塞爾等人的實驗中就先後用了三種不同的量表[10]:首先,在進入fMRI掃描之前,會給予被試PANAS情緒量表,以確定被試當前的情緒是否會對實驗造成額外的影響;其次,在fMRI掃描階段,被試在面對藝術作品時,對作品進行美的程度的判斷,以確定該作品是否為美,以便納入後期的數據分析;最後,在fMRI實驗之後,給予被試一個作品內容所表現情感的量表判定,以確定作品的情緒主題分類,並作出皮爾遜相關系數分析,確保每個被試對其所呈現物件實驗的有效性。然而,這種多維度的量表運用其實是以「審美」的「操作性界定」為中心的,美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在實驗中怎樣的操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而然」的審美?這就需要對審美進行「操作性界定」,這也是實驗的關鍵與核心。黎克特量表對實驗的適應與發展便是對審美之特性的一次貼合。
「美的操作性界定」便是以實證科學的方法對「美或藝術」之內涵的重新規定。神經美學研究的基本手段是「實驗」,實驗意味著控制與操作。那麽,「美或藝術」就必須被轉換為一種過程,神經美學不是要靜態地去分析一件藝術作品的形式因素,而是在藝術感知之中去剖析形式所引發的效果,這也是「審美」或「審美體驗」作為實驗之物件的必然。首先,神經美學實驗的研究材料多為藝術作品,藝術是「公認的審美」,因此,在取材層面藝術作品便是最可控的選材。其次,在一些實驗中,更是以藝術家的創作過程為實驗物件,探求藝術創作過程中藝術家的腦區活躍特點。[11]這些現成的藝術實踐都指向實驗的操作性與可控性。
文藝復興時期也出現過科學與人文的交融。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們能夠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世界,繼而產生與原有認識相沖突的觀念。神經美學,作為一種科學實驗所引發的觀念突破,亦是此種路徑,技術的變革引發科學發現之突破。科學的發現必然會推動觀念的更新,包括人的知識經驗和思維方式。文藝復興時期,「以達·芬奇為代表的‘高級技術工程師’透過量化思維消除藝術經驗的大約性知識特征,以數學為基礎重構藝術知識體系,並使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經驗在實驗確證的過程中被凝練,昇華為具備邏輯性與因果律的理論文本形式;藝術經驗中大約性的、口傳心授的知識傳承形態被精確性知識和原理所取代。」[12]因此可以說,今天的神經美學對藝術理論研究的影響與文藝復興時期科學之於人文之影響類似。神經美學首先在觀念上將審美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統一起來,統一了身心一體的人及其審美,再以科學之實證,一定程度上量化了審美發生之過程,將審美發生的現象在神經生理層面呈現了出來。科學的理念與方法進一步推動了人們對藝術感知的認識,對藝術感知的「知其所以然」,便能夠反過來促進藝術創作以及藝術教育的方法與理論更新。
在傳統的藝術理論中,關於審美的認識十分豐富。我們將審美歸結為「理念的感性顯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物件化」,將審美的發生歸結為審美能力的發生,例如,「直覺」「情感」「理智」,等等;那麽,問題就在於,「理念的感性顯現」「直覺」「情感」與「理智」這些概念如何從形而上的邏輯演繹與身心一體之身體相銜接,審美作為一種能力以及審美作為一種活動的發生如何從物理與生理層面的身體實作精神層面的體驗。今天,如果我們對藝術的討論仍然停留於形而上的概念演繹而無法落實到藝術感知所發生的身體層面,那麽,也就無法真正回答藝術的審美問題,甚至會陷入一種概念的平移或替換的遊戲。即便是「理式、完美與不可企及的感覺或藝術的摹仿—也無法脫離世界的創造或物質性」[8]92。
可見,神經美學所「用」的方法本就包含於「人文」之傳統,在人文科學的語境中也有端倪。【亞美利加百科全書】的「美學」條目早就指出了美學的兩種基本研究方法:先驗法和經驗法。可以說,這兩種方法在德納之前及之後一直存在,只是表現不同罷了。在神經美學以「審美」為物件的實證化過程中,作為「用」的方法也是與「審美」的內涵相適應的,同時,實驗實證對審美的馴化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審美」已經具備了有待被人文科學轉化的新的內涵。這便是神經美學「體」的建構基礎。那麽,這種科學的內涵如何轉換至藝術理論?它能夠為藝術理論研究的新文科建設做些什麽?
二、藝術心理學:神經美學的藝術學立場
神經美學實驗的材料本就是藝術作品,而神經美學的目的則在於探求「審美的神經生物學基礎」。在此,這個「神經生物學基礎」包含了兩個層面:「其一,審美活動的神經生理基礎;其二,審美活動在神經生物學層面所遵循的規律」[9],也就是基於神經生物學層面的審美理論。然而,神經生理層面其實並不是突兀、孤立的,而是與先前的心理層面相銜接的。藝術審美的心理層面研究本就有一個十分成熟的學科:藝術心理學。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指出:「把文藝的創造和欣賞當作心理的事實去研究,從事實中歸納出一些可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它的物件是文藝的創造和欣賞。」[13]雖然我們常說的是「文藝」心理學,但很多時候其對應的英文則是「thepsychologyofart」[14]。並且,文學也是現代藝術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15]如果僅就藝術範疇來看,那麽藝術心理學便是以心理學的方法考察藝術的創作與欣賞之規律的學科。而就神經美學的定義來看:「神經美學是關於藝術作品的創造與體驗的神經基礎的科學研究」[16];「神經美學……是科學地研究藝術作品感知的神經層面」[17]。神經美學更是直指藝術感知的神經層面。顯然,神經美學是對藝術心理學的進一步延伸,將藝術的審美感知落實到人的生理與實體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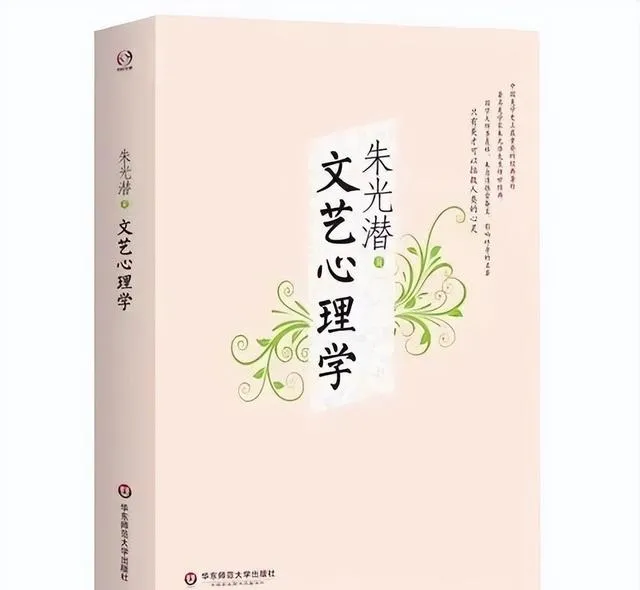
朱光潛 :【文藝心理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那麽,這種落實如何可能?即便將心理層面連線到了生理和實體層面,但並不足以表明它就是以藝術理論為基礎的生發。在此,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神經美學的「以同求異」原則也是與藝術之存在相一致的。藝術物的存在與其他物品無異,藝術的審美感知也是一般感知的一部份。這些都是「同」的部份。我們從索爾索關於藝術感知的三個階段來看:首先,光將藝術作品轉換為光訊號進入我們的視網膜,視網膜再將其轉換為神經電化學訊號成為藝術感知在神經網絡中的基礎。其次,神經電化學訊號進入視覺皮層被解析為某種基本形式。最後,訊號經視皮層進入大腦的其他區域,各區域之間並列加工輸出給意識層面的「我」,表現為審美愉悅。在這樣一個更為完整的審美感知過程之中,藝術之特質便是從物而精神、由物而藝術體驗的轉變中浮現出來的。
從神經美學的審美感知腦區的發現來看,預設模式網絡、內側眶額葉皮層A1區、映像神經元系統、獎賞系統等,這些也並不是審美感知僅有的,在其他感知活動中也有涉及,只是,這些腦區能夠從功能上判定審美感知的功能指向,例如,預設模式網絡與自我的建構相關,內側眶額葉皮層和映像神經元系統與意義(價值或認識)的生成有關,獎賞系統則關乎著我們的審美愉悅。其實,腦區的劃分在腦科學研究中本就是基於功能的劃分,我們也只能從功能上對審美體驗的內容與特性進行界定。值得註意的是,這種審美體驗功能的指向能夠表明,審美確實具有這樣一種內涵,我們便能夠基於此進一步認識這些功能在審美體驗中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就藝術創作來看,審美體驗的過程可以簡化為「物—心—物」模型,我們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到心中的構想再到物化的藝術作品,可以說首尾都是物的形態,即便是我們的構想過程也是基於物質性的腦。那麽,審美究竟特異在哪裏,藝術究竟如何與其他存在區別開來?顯然,即使從神經美學的腦區研究來看,也很難從大腦的「物」的區域來區別美與非美。因此,如果從「物」的層面難以區分,那麽,我們不妨從「物的執行」的層面來看審美感知的發生,來看藝術之為藝術、美之為美的原因:審美感知之特異的生成就在於這個感知的過程。藝術之特異性與藝術物質形式之生成都在與其相伴隨的審美感知過程之中。「審美體驗的探討是解決藝術之為藝術的內在結構的根本性問題,是研究藝術的審美特征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將有助於對‘藝術是什麽’和藝術與非藝術的根本界限這一系列當代美學核心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18]
就藝術學理論的學科使命來看,「藝術審美一定是基於藝術形式的審美活動物件,一定是和邏輯的審美的推演有很大的區別。藝術學理論在把握藝術的根本性質上牢牢抓住對於藝術審美形態內涵。」[19]關於藝術之本質的問題,基利夫·貝爾曾指出:「藝術作品的本質內容,即將藝術作品與其他物件區分開來的那種內容,……有意味的形式。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種獨特的方式組合起來的線條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關系激發了我們的審美情感,……它就是所有視覺藝術作品所具有的那種共性,……‘有意味的形式’是所有打動我的視覺藝術作品所具有的唯一的共同而獨特的內容,……藝術家的工作就是把這些形式安排和組合起來,以此來打動我們。我將這些打動人的組合和安排稱為‘有意味的形式’。」[20]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就是藝術的本質內容,就是事物之所以使我們感到其為美的「共同而獨特的內容」。然而,「有意味」是指什麽?「形式」又是怎樣一種形式?「有意味的形式」確實道出了藝術之為藝術的特性,藝術與非藝術形式的區別在於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而非藝術的形式不具有這種意味。但是問題在於,「有意味的形式」並不應停留於一種物質存在,而應落實到其感知的過程。形式的「意味」是如何被賦予的?我們又是如何見出這種「意味」的?僅從貝爾所論來看,形式之「意味」是經藝術家的「安排」與「組合」而得來的,而我們對「意味」的見出也只是「激發」和「打動」。但是,這並不能真正解釋藝術的根本內容。「有意味」本身並沒有指出藝術的形式是怎樣的一種形式,「有意味」僅僅是對形式的形容,他可以說是「美的形式」,但如此這般對美的特性以「美的形式」來描述可能等於什麽都沒說,「有意味」和「美」只是同一層面的概念平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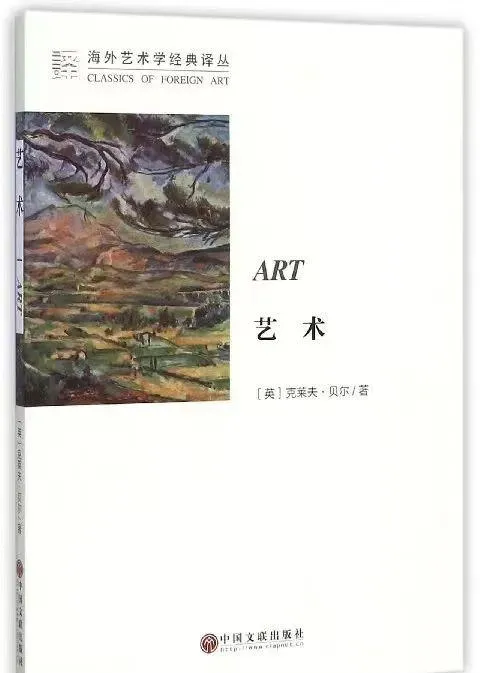
基利夫·貝爾 :【藝術】,馬鐘元,周金環譯,中國文聯出版社2020年
顯然的是,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藝術欣賞,藝術之本質都是在這個過程中被賦予的。或許,對於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並不能僅是靜態地就其內容或形式去考察。同一個事物可以是藝術也可以不是,即使是今天的相機拍出來的照片,它和實物可謂是極其一致的,但仍可為藝術。因此,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或特許以另辟蹊徑,從我們對藝術的感知方式與對非藝術的感知方式的區別來看。羅拔·索爾索甚至認為:「若要徹底認識藝術,你所要做的僅僅是去發現思維的本質。」[5]16
我們都說「藝術源於自然」,那麽,源於自然到底意味著什麽?神經美學之目的是要考察審美體驗的神經生物學基礎,而這個考察的物件正是審美體驗的發生過程。審美感知所遵循的規律是在發生的過程中被考察的,因此,藝術源於自然不僅是「形」的自然,更是藝術生發之過程的自然,生發過程的自然則意味著藝術也在遵循自然規律。加之,我們的生理基礎,我們的視覺結構對光訊號的接收與轉換方式、我們的大腦神經元的並列關聯以及腦區模組的並列加工路徑等,這些都決定了我們對資訊的感知與加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也都是藝術遵從的法則,藝術的審美感知也脫不開這個大的語境。這也是神經美學的「自然」之道的一部份,藝術欣賞正是透過對「形」的把握來感知「形」的生成。然而,問題就在於,我們必須得回到「形」的生成,才能感受到「形」的形成過程中所伴隨的情感。
三、動作想象:「形式」與「意味」的同構
「形」的生成的核心是藝術之「意味」的生成。基利夫·貝爾提出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那麽,什麽是「意味」,藝術家如何在「安排」和「組合」的過程中賦予形式以「打動」我們的「意味」?在貝爾的語境中,「意味」可以說是一種藝術形式從審美主體之中「激發」出來的「審美情感」。因此,藝術創作可以被視為審美情感被賦予藝術形式的過程,而藝術欣賞則是形式的審美情感啟用。那麽,「情感」與藝術形式又是怎樣的關系?
如前所述,神經美學語境中的「形式」不再是靜態的結果,而是被落實到了「形」之「生成」的過程之中,「形」之生成的過程即「情感」被賦予的過程。在此,神經美學首先討論的是這種方式與日常情感流露之方式的差異,基於日常情感與審美情感的效果差異,去進一步尋找二者生成方式之差異。在與日常情感表露方式的參照中見出藝術情感生成的特性,而這也正是藝術之為藝術在感知層面上的特性。
首先在效果層面,藝術情感之凝結與日常情感的表達具有顯著的差異。「藝術的情感體驗也特許以有不同的維度和不同的傾向:這不再是我們對情緒的行為傾向(盡管當你生氣時,你也會拍案而起),而是一種享受這些情緒的傾向,我們會以一種全然不同於對待日常情緒(尤其是消極情緒如悲傷或恐懼)的方式來享受它們。」[8]35日常情感的表達是一種即時性的動作表情方式,喜、怒、哀、樂都以表情的方式釋放出來,有什麽樣的情緒就會有什麽樣的表情與之對應,這些都是即時性的「動作表情」,此表情為廣義的表情,可以說軀體表情,動作表情也是動物的普遍存在。[21]其次,在神經生理層面視覺藝術的情感反應,「無論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都表現出了左半球單側性,然而,當面對其他行為時,大腦的右半球在處理消極情緒時會更為活躍,而左半球對積極情緒更為活躍。積極的情緒會在中線偏左部的基底前腦和眶額葉皮層表現出高度的活躍,而消極情緒則會在中線偏右部表現出高度的活躍。」[23]
與日常情感的「動作表情」所不同的是,藝術情感的表達方式是以「動作想象」進行的。斯塔爾認為:「動作想象實際上是模仿與審美體驗的核心能力。」[8]70動作想象並非以機體動作表情宣泄情緒,而是以一種想象或形象化的方式流露情感。動作想象具有非即時性特點,它能夠打破時空,將此時此地的情感表露於彼時彼地。[21]而動作想象與動作表情之差異的顯著表現就在於:「身體反應(我們可能會視之為與情緒相關的本能反應,如大汗淋漓、瑟瑟發抖、面紅耳赤等)卻會隨著形象的生動性而減弱,你愈是有生動的形象體驗,那麽你的情感反應就愈會傾向於精神化,而不是身體化。」[8]81身體化的動作表情與精神性的動作想象之關系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常見。例如,當一位舞者在舞蹈的時候,如果他總是哭泣,那他必然無法進行舞蹈的表演而產生中斷。還有,當一個演員在進行喜劇表演的時候,如果他自己笑得合不攏嘴,那麽他的表演也就難以使得大家發笑,因為他的這一情緒已經以動作表情的方式流失了。再者,歌手在演唱的時候,他自己若是泣不成聲,他肯定也就唱不下去了。霍達曾經在她的【穆斯林的葬禮】的後記中表示:「我和主人公一起生活。每天從早到晚,又夜以繼日。我為他們的歡樂而歡樂,為他們的痛苦而痛苦。我的稿紙常常被眼淚打濕,有時甚至不得不停下來痛哭一場。」[23]魯迅也有類似的觀點:「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作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24]因此,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如果情緒以動作表情的方式釋放過於強烈,很大程度上也就幹擾了情緒的精神化,而趨向於身體化,即造成創作的中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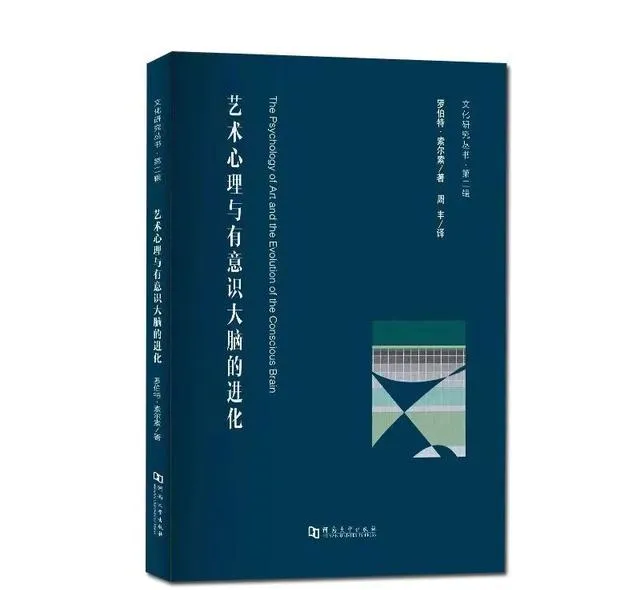
羅拔·索爾索:【藝術心理與有意識大腦的前進演化】,周豐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
因此可以說,藝術創作中情感在物化的同時也是精神化的。我們可以說是先有「胸中之竹」再有「手中之竹」,然而,創作的真正展開則是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呈現過程。線條與色塊絕不是隨機的組合,而是伴隨著創作者情感的流露的形式化,這種形式化在其筆墨的疾緩、濃淡、粗細中蘊含著一種「力」的存在,這個「力」不僅是物理的「力」,同樣也是心理的情感的「度」。我們在欣賞藝術作品之時,正是依據形式,回到形式的生成過程,去體驗其所伴隨的情感:「畫筆或銼刀的物理軌跡能夠喚起觀者對作者創作這件作品過程的動作想象,一筆一劃,一鑿一刻都會化作動作想象被還原於觀者的身心。」[8]74
然而,可能有人會問,我們在藝術欣賞的過程中不就是在想象和聯想嗎?我們在品讀鄭燮的【竹石】的時候,會想象到竹子、聯想到風,還會聽到風搖竹葉的聲音,甚至是聯想到「任爾東西南北風」的那個鄭燮的形象。但這種想象並非是動作想象,而是與文本相關的聯想。就此問題,筆者曾求教於專業琴師,如果我們在聽琴時所聯想到的是高山流水或清風明月,可能已經脫離了琴聲的本身,這種聯想在我們對琴聲的體驗中某種程度上是會起反作用的,它已經形成了用誌不專。它是跳脫了文本本體所具有的「動作想象」,而進入到了一種描述性的想象。它類似於一種批評,一種可表達的「名狀」。當然,我們不能說這種聯想就一定是消極的但它與動作想象的關系是仍有待討論的。
「動作想象」的實質是以形象動作序列的方式表達「意味」。「形象化(imagery)和內省神經網絡緊密相關,形象化問題正是審美愉悅的關鍵。」[8]8而內省網絡的核心則在於預設模式網絡,該區域負責「自我」的建構,維塞爾等人發現,在深度審美體驗活動中,預設模式網絡便會回到基線活躍水平,這意味著審美的「自我」建構的維度指向。①因此,「形象化」問題便伴隨著「自我」的建構和審美愉悅的發生。因此,「意味」並不能僅僅被視為「情感」維度,它同樣包含「認識」或「價值」層面。那麽,如果說,「意味」具有這兩個維度,是否就意味著「認識」與「情感」的一種沖突?非也。「‘價值’不是事物所固有的東西,而是指物件、知覺或觀念為我們所體驗的一種特征描述,……審美體驗能夠導向認識。」[8]13-14因此,這種「價值」作為對體驗特征的描述,也是認識本身。
此外,神經美學基於神經生物學層面的審美研究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重要啟示:大腦的加工活動是並列分布式加工,也就是說,大腦的各個區域之間是協同、共時性加工,而不是處於一種線性狀態。然而,當前我們關於審美的諸多理論描述仍是一種線性關系,想要找出個孰先孰後來,甚至出現概念的對立與分割。如索爾索所言:「物理世界與思維的分立以及與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大腦處理感覺資訊方式的分立,都是人為的分立。」[5]20在此,問題就在於,審美的一些核心要素,例如想象、情感、意味或認識是怎樣一種關系?我們能否用一種線性關系或非此即彼的關系描述它們。顯然,基於神經美學對於藝術審美感知的研究,我們將這些核心要素的關系描述為一種並列關系似乎更為可靠。
事實上,我們的認識活動是線性的,這是人的局限性。我們的大腦在意識層面只有一個輸出埠「我」,「我」的單元性就決定了「我」的認識的線性特征。而自然界之存在本是共時性的,物與物之間是並列存在的。大腦的共時性加工就在於,大腦的各個構成單元,各個腦區、神經元之間是一種並列關系,這種並置方式就意味著意識之前的加工是一種並列分布式加工。而當大腦將這些加工內容輸出到意識層面,即意識埠的「我」的時候,便成為一種線性方式,因為,意識層面只有一個「我」,而意識之前的加工卻是「我」不可知的。那麽,意識之前和意識層面的加工如何對應?這便是神經美學所提出的另一個概念:原型同構。[25]原型同構所描述的是心理層面的意識內容與物理世界的感知訊號之間對應的一種關系。然而,這種同構關系進入到審美之後,感知所同構的便不再是「意識」,而是意識在審美層面的全部構成,也就是審美的這些構成是一個整體,這些構成之間是一種空間立體的兩兩同構的關系,而不是一種平面的線性相依。此外,由心理學對情緒的界定來看:「我們對刺激的感知直接伴隨著機體變化,與此同時我們的感受也在發生著變化,這就是情緒。」[26]情緒或情感本就包含兩個維度:身體的行為或動作與意識層面的態度或認識。直言之,情感的構成正是認識和動作。可見,每一種意識輸出都會對應著一種機體的反應,而這個反應被我們稱為情緒,情緒既是對某個物件的評價(意識埠),也是對該物件的身體反應(機體埠)。或更直接地說,評價只是對「機體狀態」的命名,我們所說的「歡喜、悲傷、平糊、痛苦」等並不是情緒本身,而只是對情緒狀態的命名,是情緒得以言說或理解的最外層表征。
因此,「有意味的形式」並不僅僅是一種修飾短語,「意味」與「形式」實為一種並置的同構關系。不是有了「形式」才有了「意味」,而是「形式」之「形」在生成的過程中就已經伴隨了「意味」的生成。「形」的生成也是「意味」的生成過程。「意味」可以被理解為「情感」與「認識」兩個方面,但這兩個方面也並不是割裂的,二者也是一種同構關系。形式的「物」的層面與「意味」的同構關系就可以被描述為:藝術形式在「物」的執行層面被轉換為神經電化學訊號,神經電化學訊號在大腦的加工之後輸出給意識埠的「我」,以「動作想象」的方式構成審美認識,與此同時也伴隨有審美愉悅、情感等。動作想象是認識建構的基礎,而審美體驗中所獲得的認識、經驗與反思也是透過動作想象來完成的。

查德·普魯姆 :【美的前進演化】,任燁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
神經美學實驗研究對美的神經生物學基礎的發現:愉悅的獎賞系統、想象的區域、情緒的區域、還有「自我」的預設模式網絡、動作—意義建構的映像神經元系統,等等。表面看來,這些發現呈現出多樣性,但這種多樣性均指向一點—審美:個體的審美活動中包含了愉悅、想象、情感、自我認識、動作這些要素。而且,傳統的美學理論中對美的認識確實存在這些要素。只是這些要素在傳統的審美之中呈現出零散甚至是對立的關系。然而,神經美學的腦區本就是一種並列分布式的共時性加工,這種並置絕不是生理層面的,而同樣包含與其相應的理論層面。神經美學所呈現的原型同構,能夠給審美感知中的各要素形成一種凝聚的關系。「動作想象」作為藝術的表情方式,也是藝術之形式被賦予意味的方式。神經美學研究,以「動作想象」為核心,確立了審美感知區別於非審美感知的特殊性,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藝術之於非藝術的區別。動作想象作為審美感知的方式與橋梁能夠連線藝術的物層面和體驗的精神層面。
結 語
從神經美學的新文科實踐也可以看出,跨學科研究首先是基於自身學科的問題與傳承,也就是守正問題,跨學科所創之「新」,首先是一種新的視野和方法。簡言之,藝術理論的新文科建設是以本學科為體,跨學科為用。當然,這也並不是說,跨學科只是一種「用」的層面,它也有可能轉化為「體」,只是這種轉化首先是基於本學科的「體」而生長的。以神經美學看來,它是一種由「用」的方法而走向「體」的理論。神經美學所「用」之方法在不斷地以其問題為中心與概念相互協調、彼此適應,以實作對研究物件的規定與對研究目的的接近。方法的變革使得我們能夠在現象層面上更為精確、完整地呈現藝術審美感知的過程,而審美理論之完善恰恰是基於現象的完整。因此,便能夠實作由「用」的方法到「體」的理論的轉換。
神經美學的誕生與發展給藝術理論研究的啟示絕不僅僅是它研究的結果。作為審美的實證研究,我們很自然地會關註它的研究成果,它對審美的發生與藝術的本質有怎樣的揭示。然而,如若此,神經美學所能給我們的啟示便會被片面化和直觀化。當然,神經美學所提供的實證成果是最為直觀、最為有效的,但神經美學的研究方法、問題視野、研究觀念,等等,這些都是藝術理論研究值得借鑒的,當然,這些啟示的落腳點仍是藝術理論的基本問題。此外,對藝術理論研究觀念上的轉變也不容忽視:如身心一體連線和落實、藝術與自然的統一、由外而內的問題視野和研究路徑,等等,這些都是本文對神經美學的借鑒,而不是僅僅停留於對實驗結果的吸納與轉化。
「新文科」的概念雖是近年提出的,但其所包含的理念實踐卻早已有之,「學科」是生長的,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其邊界的拓展必然涉及到學科概念的內涵、方法乃至整個學科的內涵的深化與生長。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的方法與觀念的引入本就是一次人文科學的拓展;今天我們所說的「無意識」「力比多」「原型」等概念,在一百多年前也只是心理學概念,但當弗洛伊德和榮格將其用於「討論」藝術的時候,就已經具有了藝術理論的內涵了。這些實踐都是一種由「用」到「體」的轉換,這個轉換的過程也是「新」的方法與學科本體的問題相適應的過程,而神經美學作為一次跨學科實踐也是符合藝術理論發展的必然性的。今天,我們可以透過這樣一次實踐,認識藝術理論研究新文科發展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吳國盛.科學與人文[J].中國社會科學,2001(04):4-15+203.
[2]陶東風.新文科新在何處[J].探索與爭鳴,2020(01):8-10.
[3]趙奎英.試談「新文科」的五大理念[J].南京社會科學,2021(09):147-155.
[4]SemirZeki.InnerVision:AnExplorationofArtandtheBrain[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vii.
[5]羅拔·索爾索.藝術心理與有意識大腦的前進演化[M].周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
[6]李察·普魯姆.美的前進演化[M].任燁,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引言.
[7]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8]加比奧·斯塔爾.審美:審美體驗的神經科學[M].周豐,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21:13.
[9]周豐.西方神經美學的源起、內涵及意義—基於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考察[J].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19(2).
[10]VesselE.A.StarrG.G.&RubinN.Thebrain:onart:intenseaestheticexperienceactivatesthedefaultmodenetwork[J]FrontiersinHumanNeu-roscience,2012(06):66.
[11]RobertL.Solso.「BrainActivitiesinaSkilledver susaNoviceArtist:AnfMRIStudy」[J].LEO-NARDO,2001(01):31-34.
[12]孫曉霞.量化思維與藝術經驗—文藝復興時期藝術與科學關系的再分析[J].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21(01):9-16.
[13]朱光潛.文藝心理學[M].上海:開明書店,1939:1.
[14]童慶炳,程正民主.文藝心理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5]李心峰.試論文學與現代藝術體系[J].藝術學研究,2022(02):4-12.
[16]NalbantianS「NeuroaestheticsNeuroscientificTheoryandIllustrationfromtheArts[J].InterdisciplinaryScienceReviews,2008(04):357-368.
[17]BrownS.DissenayakeE.TheArtsaremorethanAesthetics:NeuroaestheticsasNarrowAesthetics[J].Neuroaesthetics,2009:43-57.
[18]胡經之,王嶽川.論審美體驗[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04).
[19]周星.審美信仰與理論思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思考[J].藝術百家,2020(04):42-49+115.
[20]基利夫·貝爾.藝術[M].薛華,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3,4,5.
[21]周豐.藝術能力的發生:藝術起源的神經美學路徑[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2(01):15-23.
[22]AlvesN.T.,FukusimaS.S.,AznarCasanovaJ.A.ModelsofBrainAsymmetryinEmotionProcess-ng[J].Psychology&Neuroscience,2008(01):63-66.
[23]霍達.穆斯林的葬禮[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606.
[24]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79.
[25]周豐.神經美學的四個關鍵概念芻議[J].美與時代(下),2022(07):4-11.
[26]JamesW.Whatisanemotion?[J].Mind,1884(09):188-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