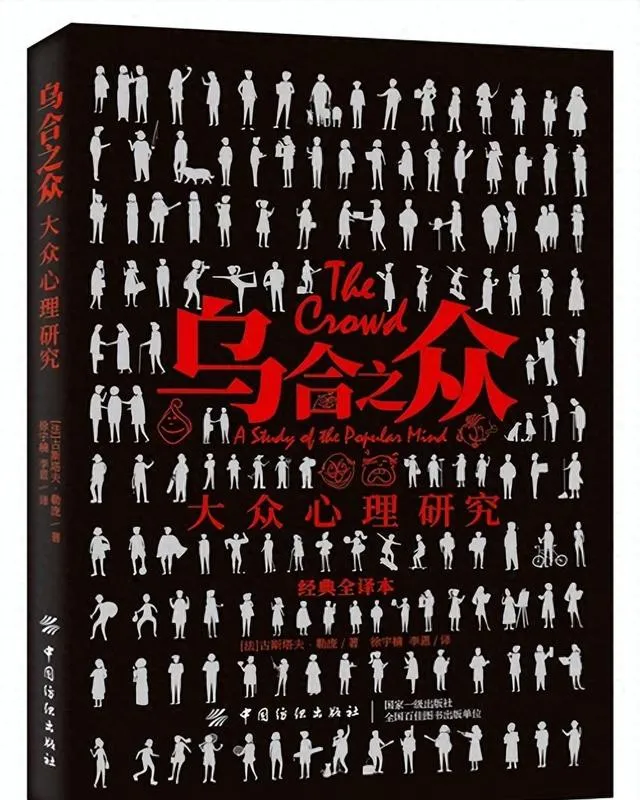
「群體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簡單而誇張。……不幸的是,群體的這種誇張傾向,常常作用域一些惡劣的感情。它們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遺傳的殘留,孤立而負責的個人因為擔心受罰,不得不對他們有所約束。因此群體很容易幹出最惡劣的極端勾當。」
——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一個人的一生,除了要經歷和演繹故事之外,還要去聽、去看很多故事,而這些聽來的、看來的故事大都和自己無關,但總有一些故事會刺痛你。之所以會產生對【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的興趣,就緣於刺痛我的兩個故事。而這兩個故事,也更加深了我對勒龐這部100多年前著作的理解。
公元前399年,經由雅典人的投票程式,蘇格拉底以「不敬神」和「蠱惑青年」的罪名被多數人判處死刑。那一刻,雅典大眾的神聖意誌得到了充分體現,他們以群體的力量戰勝了一個年邁的「另類」並在肉體上消滅了他。但,之後的歷史告訴我們,那些雅典人——生活在當時世界上最為自由城邦之一的「大眾」們,犯下了不可寬恕的暴行。正如蘇格拉底在最後一刻所說:「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活著,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2000多年過去了,在西方思想的歷史上,蘇格拉底因其坦然受死而英名遠播,而公元前399年的雅典「大眾」卻永遠的與「群氓」和「不光彩」聯系在一起。
公元1630年,中了皇太極反間計的大明帝國上下將抗擊後金的主將袁崇煥以「磔刑」(分裂肢體)處死於北京西市。行刑時,圍觀的「大眾」生啖其肉,可憐袁督師大好男兒,頃刻間屍骨無存。據明末史家張岱在其著【石匱書】中記載:「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臟,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如今,袁崇煥的冤屈早已昭雪,而1630年圍觀行刑的大明帝國首善之區「大眾」的靈魂還在被後人嚙噬。
這是兩個關於「多數人戰勝少數人」的故事,當然用勒龐的話,則是兩個「群體情緒」得到滿足的故事。這更是兩個勒龐所界定的「群體犯罪」故事,「通常,群體犯罪的動機是一種強烈的暗示,參與這種犯罪的個人事後會堅信他們的行為是在履行責任,這與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審判蘇格拉底的雅典人、生啖袁崇煥的大明帝國的民眾,在他們實施暴行之後,一定會認為他們完成了一樁重要的使命。
在現代社會,人們可以容忍形形色色的另類行為者,甚或以欣賞、羨慕的目光追隨且仿效之,但在政治以及社會倫理領域,「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是堅定不移的標準。自然,對於維持相對公平且正義的社會體系而言,這是經由殘酷爭鬥後共同達成並遵守的契約。然而,時不時地,蘇格拉底之死與袁崇煥的行刑這一類被有意無意忘卻、忽視的記憶,卻仍如幽靈般漂蕩,在人們耳邊回想:多數人的選擇,就一定正確麽?我想,讀過【烏合之眾】的讀者,大致上都會對這個提問做出一個否定的回答。
蘇格拉底的雅典城邦時代,「民主」曾一度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威,恰恰在此時,蘇格拉底對參與政治事務的「民主」人士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嘲笑:「站起來向他們提供意見的,卻可能是個鐵匠、鞋匠、商人、船長、富人、窮人、出身好的、不好的,沒有人想到責備他。」蘇格拉底扮演了西方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個殉道者,他迫使雅典違反了自己的精神傳統:以言論自由著稱的一個城邦竟對一個除了運用言論自由以外沒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學家起訴、處死。再沒有比蘇格拉底之死更有力的歷史事件證明,在大眾的名義下,並不全都是正義,勒龐甚至認為「群體很容易幹出最惡劣的極端勾當」。
魯迅對中國的國民有一個鮮明而精辟的態度:「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句話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被讀過魯迅書的人廣為參照。【藥】裏面買到用革命者鮮血所浸潤的饅頭的老栓父子,被「大眾」稱為「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欺負阿Q是未莊大眾的賞心樂事;鑒賞日軍殺中國人頭之盛舉的中國大眾臉上呈現的是麻木的神情······也許,有人會說,「大眾」的不幸源於他們的「不自知」。然而,當我們在使用「不明真相的群眾」、「不知者無罪」這樣充滿寬容的詞語時,是否想過,「不明」與「不知」,真的能夠成為合法性的全部基礎嗎?如果,雖然「不明」卻依然從眾;如果,盡管「不知」卻還是參與,那麽這個時候,「明」或者「知」作為行為依據的意義豈非已經喪失?這才是魯迅眼中真正的「不幸」。
受過現代民主教育的人們往往會對輕視大眾、醜化大眾的觀點產生與生俱來的排斥。那些具有精英氣息的人物及其觀點也往往會被當成眾矢之的,接受群眾史觀的人更加會將任何持有質疑「大眾」論點的人視為敵人。倒退數十年,或許還會將此類人打倒在地,踏上一萬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看還敢不敢質疑大眾。出於政治的、經濟、社會的種種原因,「大眾」的地位在現代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因此,長時間來,是否脫離「大眾」就成為一種對人的評價標準,而「自絕」於「大眾」的人往往也是死不足惜的,否定「大眾意誌」的思想就成了一種典型的「政治不正確」。在膜拜「大眾」智慧和「大眾」力量的語境下,對於「大眾意誌」從何而來、「大眾意誌」是否是正確、「大眾意誌」是否會帶來災難性後果之類問題的思考總是容易付諸闕如。
上述質疑,無疑會折磨一些人的神經。然而,也總有一些具有「雖千萬人吾往也」氣概的人站出來思考。我們前面一再提到的古斯塔夫·勒龐便是其中之一。【烏合之眾】這本小書,雖然篇幅不長,卻道出了勒龐在面臨「多數人」這一不斷在沈默與爆發中徘徊、集軟弱與強大於一身的群體時的全部不安與擔憂。【烏合之眾】在面世後一版再版,以其獨特的視角、犀利的見解持續影響著世界,也一直而且一定繼續刺痛「大眾」和迷信「大眾」的人們。
勒龐對「烏合之眾」的指斥毫不留情:「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 「群體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這種疊加的「愚蠢」導致群體意誌顯現出沖動、易變和急躁,容易接受暗示,並變得輕信和草率,被誇張而簡單的情緒化所左右,從而走向偏執、專橫和保守。群體最為明顯的特征是往往陷於缺乏理性的沖動而不自知,喪失判斷力,缺乏批判精神,隨波逐流,人雲亦雲。
自然,對「烏合之眾」的情緒化、易沖動、愚蠢的指責並不是勒龐所要關註的重點,或者說,勒龐並不在意也不擅長探討如何提升理性和智慧在個人生活中的地位,他只是站在個人的立場,對一種反復出現的人類行為進行獨立的思考,並把它表述出來。他所擔憂和恐懼的中心在於,這樣龐大卻智力不高的群體,是多麽容易被利用的武器。「多數人」,對於政治野心家來說,是一面神聖而且可靠的旗幟,它能夠為一切言行提供全部的合理性,哪怕是在四面楚歌、大廈將傾之際。
在勒龐看來,無理性、情緒化一旦在大眾之間彌漫,除了造就大量喪失理性的暴民之外,更為重要的後果就是會被形形色色的野心家所利用和控制,並以之來達到各式各樣的目的。「大眾」為野心家的權力和影響力提供了合法的外衣,而假借「大眾意誌」所從事的種種勾當往往會因為代表著多數人的群體利益而無比神聖。而無數個歷史時刻已經證明,被發動的、情緒化的、非理性的「大眾意誌」會造成多麽大的浩劫。目睹一次又一次的歷史迴圈,勒龐憂心忡忡的說道:「民眾就是至上的權力,野蠻風氣盛行。文明也許仍然華麗,因為久遠的歷史賦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實它也成為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廈,它沒有任何支撐,下次風暴下來,它便會立刻傾覆。」
如果我們善意的或者理性的去理解和分析勒龐的憂慮,不把勒龐的憂慮當作對「大眾」的敵意或者輕視,就會發現這並非是勒龐個人的精英主義在作祟,而是真誠地為一個喪失理性、缺乏獨立判斷和批判精神的社會風氣而憂慮。值得一提的是,勒龐的憂慮在網絡時代不斷應驗:網絡暴民、各色憤青紛至沓來,並在假訊息、流言等的鼓動下走向情緒化、暴力化,美化暴力、謳歌偏執成為許多論壇的主旋律。網絡為狂躁的「烏合之眾」提供了一個可以極端宣泄情緒並且絲毫不負責任的平台,勒龐沒有預料到網絡社會的出現,但網絡時代「烏合之眾」的表現完全在勒龐的憂慮之中。
人有責任成就自己,而成就自己在於讓自己成為一個有主見、有一以貫之的信念和堅定的立場、知識豐富、判斷準確、行動有預見性的人,這樣的人才不會被蠱惑,不會被愚弄,才不會成為「烏合之眾」的一份子。讀勒龐的【烏合之眾】,仿佛是在照一面直擊心靈的鏡子,鏡中的逐漸喪失個性的「烏合之眾」分明有我們自己的影子。照這面鏡子,為的是警惕自己不要淪為「烏合之眾」。否則,在投票處死蘇格拉底、生啖袁崇煥的人群中,就會有你有我。
文/朱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