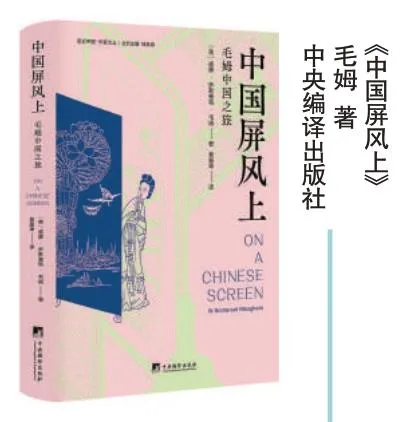
【中國屏風上】是毛姆1919年的中國之行的旅行劄記。 本來他的計劃是先把第一手材料和初步的見聞記錄下來,然後再加工形成一個完整的敘事。但是很快他發現這種松散而隨性的散文,如果強行放在一個框架裏,就會破壞了其自然和真誠的風格。他索性將這些浮光掠影的印象稍加處理,以非虛構的形式發表。
從13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開始,西人中不乏有記敘自己的中國之旅,分享個人見聞和對中國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的親身體驗的遊記作品。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國對世界的開啟,更是湧現了一批以中國為物件的遊記作品,其中包括約翰·法蘭西斯·戴維斯的【中國劄記】、伊莎貝拉·布特的【跨越長江流域】、維克多·默多克的【神秘壯觀的中國】等。
和之前的遊記相比,毛姆的【中國屏風上】更多著墨於人物,而不是鋪陳事件或者追溯歷史。
這些一閃即逝的人和瞬間,同時飽含著飛散和聚合的力量。一方面這些讓毛姆心動和狂喜的碎片印象匯成一幅印象派畫作,讓讀者對中國20世紀初期現代化行程有了具體的認識(也許不是全貌)。毛姆筆下的中國正處於現代化風口浪尖,正在應對政治動蕩、西方影響和內部改革的挑戰。這個現代化的行程和當時封建帝國的沒落、國際移民、對外貿易是密切相關的。毛姆的浮光掠影在某種程度上也讓這個現代化的建構過程浮出水面。 在毛姆的筆下,中國現代化的萌芽是攜帶著巨大的舊文化的基因,伴隨著西方對遙遠國度的熱忱、蔑視、覬覦破土而出的。 毛姆所描述的對外貿易、域外法權和文化掠奪,可以讓讀者獲得20世紀初中國殖民主義狀況的一個直觀的印象。
毛姆對作品中人物細致入微的觀察和描摹沒有像東方學學者那樣,試圖展現其文化的獨特性,而是進入人性的崎嶇精微之處發掘共性的善和惡。因為,不管中國人還是英國人,人性中的奇譎和心理的晦暗都大致相同。毛姆沒有簡單地把中國人等同於中國,也沒有把英國人等同於英國。 而是著力表現在浮世中處於動蕩、遷徙中的個人,來探索人的孤立、流離失所以及身份和文化隔閡等主題。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毛姆旅居中國四個月,由於語言障礙,除了和能夠交流的當地人進行了接觸之外,大部份時間,他都是在一個龐大的被統稱為中國的背景下孤立地探索和前行。他的中國印象自然無法擺脫20世紀早期西方作家的偏見以及西方對東方的文化想象,也不可避免地以西方的視角和標準來衡量中國的藝術和社會現實。比如,在第一篇【幕布升起】中,毛姆把一座破敗的中國城市比作古畫裏被十字軍攻占的巴勒斯坦城堡,並想象在城裏行走的轎車裏的鴻儒是去友人處,緬懷唐宋風韻的黃金時代。除了著力刻畫的人物,在很多章節內, 東方精致的古韻、舊時的窮街陋巷和底層人民的身體融匯成一幅神秘而無法破解的中國群像,他所走過的大江大河也更像是迷霧飄渺的筆墨山水畫。
不過,也不可否認毛姆確實有嘗試避免簡單的刻板印象和東方主義的話語體系的自覺意識。其策略之一是透過使用第二人稱「你」來描述自己的見聞,把自己放在一個我和他之間的位置,這是刻意避免遊記的文化殖民主義的一種策略,也是一種寫作的倫理選擇。
策略之二是避免絲滑。 在遊記寫作中,讀者往往要問的一個問題是,作者對於異域風情和文化的轉譯是否絲滑無縫,還是充滿猶豫、不解和困頓。毛姆對於中國的敘述顯然屬於第二種情況。除了偶爾使用熟悉的事物來對眼前的陌生景象進行類比之外,在文中,他經常使用「我不知道」「天知道」「我分辨不出」「不知何故」等措辭, 表現出一種謙卑和對異質文化的「無知」的外來者的視角,盡量克制自己將所見所聞帶入一個已知的詞匯表和思維框架之中的欲望。
策略之三是反諷。毛姆特有的反諷的筆觸使他規避了西方的先入為主和高高在上的姿態。如果說中國讀者對於毛姆筆下落後的中國感到不適的話,那麽一個西方人也會對書中西方人的貪婪、傲慢、偽善和文化殖民同樣感到羞愧。毛姆尖刻、惡毒的筆觸毫無保留地表達著自己對於偽善和權貴的厭惡,也不吝嗇對窮苦人類的同情和被壓迫人民的贊美之詞。
毛姆的【中國屏風上】在多大意義上改變了西方的東方敘事,我們也許無從得知,但是,它至少糾偏了一些認識,塑造了一個不同於旅行之前的自我。回到英國之後, 毛姆曾經公開表示中國可以「給你一切」 ;中國之行「的確是一次豐富靈魂的經歷」。 而他後期創作的【蘇伊士之東】和小說【面紗】,也可以看出中國之行對其思想和寫作的積極影響。
(作者為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