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指出,二十世紀文學作品有兩種類別,一種是結晶體,一種是火焰。這是兩種歸類事實和理念、風格和感情的範疇。卡爾維諾自稱是代表創新的結晶派,他的小說風格追求形式創新,追求哲理性、圖解性和制作性,強調精確和簡潔。不過,盡管卡爾維諾屬於後現代主義,加繆屬於現代主義,結晶派的這些特征同樣可以在加繆的小說中發現,尤其是他的【局外人】。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 1957 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代表作品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
撰文 | 景凱旋
他追求的不是活得最好,
而是活得最多
沒有一部現代小說的文字比【局外人】更簡潔的了,想想普魯斯特繁復細膩的【追憶逝水年華】,想想穆齊爾未完成的【沒有個性的人】,與他們相比,加繆的【局外人】就像是一顆精工打磨的結晶體,沒有一句多余的話。小說第一部的開頭是:「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麽。可能是昨天死的。」
開頭這段簡潔文字表現出小說的冷漠風格。故事透過主人公默爾索的自述展開。默爾索生活在阿爾及爾,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接到母親去世的訊息,請假前往養老院,幾年前他把母親送往那裏,近一年幾乎沒有來看過她。他不記得母親的年齡,拒絕看母親的遺體,在靈柩前抽煙。他似乎對母親的去世毫不傷心,卻很註意觀察周圍的人群,全書都是透過默爾索對外界的觀察,來表現主人公的漠然。
守靈時,來了幾個母親生前的朋友,都是養老院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靈柩旁邊,默爾索只是感到困倦不堪。「這時,那個女護士進來了。天一下子就黑了。」「從開著的門中,飄進來一股夜晚和鮮花的氣味。我覺得我打了個盹。」第一句寫女護士進來,接著就寫天黑了,中間沒有任何過渡。第二句寫房門開著,其實是在照應前段女護士進來後的情景,夜晚和鮮花的氣味與打了個盹之間,也是句子間的非邏輯跳躍。薩特就曾敏銳地指出,這部小說的每句話都是一座島嶼,一個封閉的「現在」。
這種話語的縮減造成一種疏離的效應,主人公對外界的感受是零碎和隔膜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加繆絕不同於卡爾維諾,盡管在他們的作品中,主題已經變得比人物更重要(結晶派的特點) ,不過後者將文學視作接近事物無限多樣性的方式,而前者則是將文學視作獲取事物實質的方式。也就是說,【局外人】是結晶體和火焰的結合。從表面上看,【局外人】是一部關於罪與罰的故事,實際上卻是一部探索荒謬的小說。
加繆在論及文學的性質時曾說過,作品是「在死亡那裏獲取自己最終的意義。」【局外人】恰恰是以母親去世時始,以主人公被判死刑時終(符合結晶體的結構原理) 。默爾索就像是一個活在絕對自我中的人,他從母親葬禮上回來,睡了一覺就去海裏遊泳,接著與女友瑪麗去看了一部喜劇片,然後倆人回到住處做愛。接下來,默爾索自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周末在陽台上觀看街道上往來的人群:
「我也把椅子倒轉過來,像賣煙的那樣放著,我覺得那樣更舒服。我抽了兩支煙,又進去拿了塊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來。很快,天陰了。我以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漸漸放晴了。不過,剛才飄過一片烏雲,像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陰暗了。我待在那兒望天,望了好久。」
總之,母親去世後的日子沒有任何變化,他的生活一切照舊。瑪麗想要跟他結婚,他覺得怎麽都行,她問他愛不愛她,他認為這句話毫無意義。他說他大概不愛她,但這於結婚無關緊要。鄰居萊蒙是個拉皮條的人,默爾索並不拒絕與他交往,還替他寫情書,引誘他的阿拉伯女友來遭受羞辱。
默爾索能感覺到言語的無意義,卻感覺不到行為的無意義,這讓我們想到之前的法國作家塞利納,主人公知道殺人陰謀後同樣一聲不吭。不同的是,塞利納的主人公本身避免了成為殺人犯,而在加繆這裏,這種無意義的行為最終衍生出一個決定性的事件,默爾索和瑪麗、萊蒙在海灘上玩耍,那個女人的兄弟向他們尋釁,仿佛灼熱的陽光使默爾索感到眩暈,他在漠然狀態中開槍打死了一個阿拉伯人。荒謬就是這樣產生的,正是無意義驅使他開的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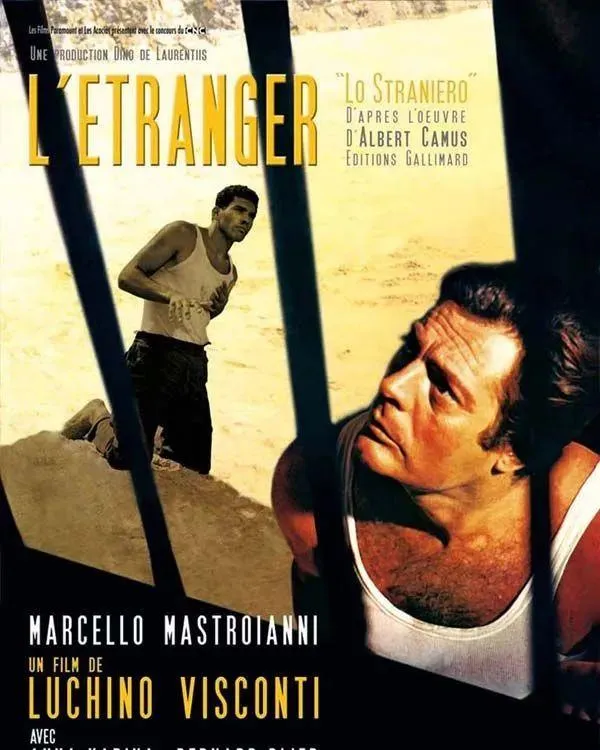
電影【局外人】(1967)海報。
雖然默爾索是敘事者,但由於作者將他放在一個被觀察的位置,於是給讀者帶來的印象是,主人公毫無道德感,麻木不仁,他仿佛只活在「現在」,活在海德格爾所說的「當前化」中。這一點在默爾索跟預審推事的初次會面時體現得最為明顯,分手時他想要跟推事握手,「幸虧我及時想起來我殺過一個人。」不過,如果我們認為默爾索是個阿Q式的人物,完全缺乏自我的意識,那就錯了。用瑪麗的話說,他是個「怪人」。主人公不是缺乏自我,而是無法超越自我,與外部世界建立起聯系。
問題在於,對於默爾索來說,這種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值不值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小說第二部中,默爾索面臨殺人指控,但他從未感到自己有罪,也不相信上帝的存在。預審推事試圖探討他殺人的動機,揪住他對母親的死無動於衷,以證明他是天生的殺人犯。案件被引向道德審判,並得到眾人的贊同。在法庭上,檢察官義正辭嚴地指控道,默爾索「在母親死後的第二天就去幹最荒淫無恥的勾當,為了了結一樁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隨隨便便地殺人!」
默爾索不明白,母親的死與殺人有何關系。他跟所有人一樣愛自己的母親,只是不願像所有人那樣被既定的習俗束縛,當眾表演很悲痛的樣子。但是,事實確實擺在那裏,所有證人的證詞都對他不利,按照檢察官的觀點,默爾索沒有人性,沒有靈魂,他應當因為對母親的去世表現冷漠而被判極刑,這樣才會對社會有警示意義。
在最後時刻,默爾索一再拒絕了神甫主持的懺悔。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孤獨的,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想到了死:「但是,誰都知道,活著是不值得的。」因為,「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實。」主人公在省察自己的一生時,意識到生命的空泛和虛妄,他並不是個沒有思想的人,相反,他在觀察別人時比所有人都要思考得多,他追求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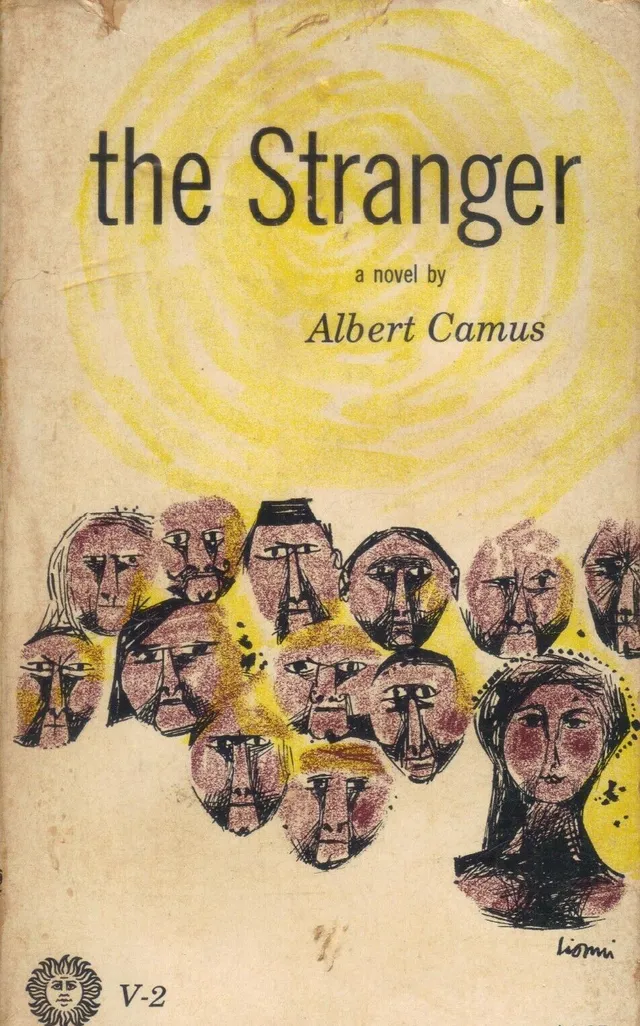
【局外人】外文版封面。
從對荒謬的反抗中獲得自由
顯然,按照社會的法律,主人公是有罪的,但默爾索絕不是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那種為生活所迫的罪人,能激起人們對社會的批判。如果加繆想引起讀者對主人公的同情,讀者只能將作品看成具有更深的含義才行。
這更深的含義就是加繆的存在哲學。在他看來,人是被偶然擲入這個世界的,孤獨感來自生存的荒謬,來自世界的無意義。加繆在其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裏指出,人與世界的唯一聯系就是荒謬,意識到荒謬世界的人就是荒謬人。因此,默爾索感到自己對何為生命比神甫更有把握。蘇姍·桑塔格曾評論道,加繆常常從虛無主義的前提出發,把他的讀者帶向人道主義的結論,而這結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從其前提得出來。「這種從虛無主義深淵向外的非邏輯的一躍」,正是默爾索最後時刻的感受。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滿天星鬥照在我的臉上。田野上的聲音一直傳到我的耳畔。夜的氣味,土地的氣味,海鹽的氣味,使我的兩鬢感到清涼。這沈睡的夏夜的奇妙安靜,像潮水一般浸透我的全身。」他的身上發生了某種深刻的變化,「面對著充滿資訊和星鬥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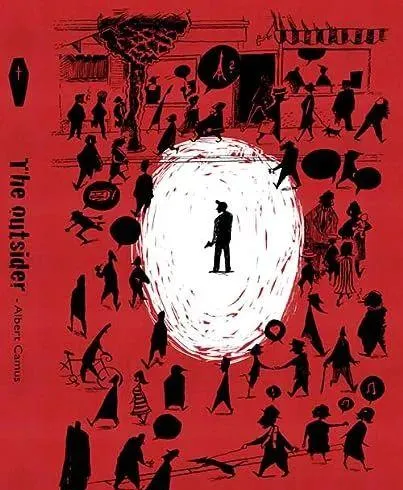
【局外人】外文版封面。
還是讓我們回到前面的敘事,看看默爾索為何認為自己是幸福的吧。默爾索對養老院周圍蔥綠田野的喜歡,對大夥在海灘巖石上嬉戲的欣喜,對從陽台上望出去萬千模組屋的觀賞,以及從監獄視窗看到波濤起伏的大海所感到的幸福,在在表明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正因為如此,加繆才在美國版序言中寫道,默爾索「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沈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那麽,應該如何理解加繆所說的「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默爾索拒絕與這個世界和解,選擇獨自面對死亡,按照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的闡述,荒謬的人只承認「自我決定的道德」。我覺得,這個「自我決定」就是默爾索身上對絕對的激情。世上大多數人都是與世浮沈,每日寄望於虛妄的明天,默爾索意識到這種荒謬,決心要反抗這種荒謬,這使得他在這個平庸的世界顯得異常孤獨。面對無意義的人生,主人公以荒謬為自由的根據,從對荒謬的反抗中獲得自由,「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之以仇恨的喊叫聲。」主人公這最後一句話的態度就像神話中的西西弗,鎮靜地走向巨石。

畫作【西西弗】。
隨著近代以降上帝的離場,十八世紀的人重新贊頌古希臘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欲圖以這位古代英雄來取代上帝,拯救人類。於是我們看到,從近代小說誕生之日起,小說家們就加入了尋找意義的大軍,歌德、司湯達、狄更斯、巴爾錫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雨果、羅曼·羅蘭……這些偉大作家塑造了眾多反叛的世俗英雄。但是,也正如雷蒙·艾朗所說,意圖掌控歷史的這種普羅米修斯野心是現代極端思想的根源之一。他們用文學改變社會的理想最終落空了,二十世紀的文學於是產生了某種「反英雄」, 默爾索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投身反抗,但絕不指望反抗的結果,因為荒謬本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存在境況。加繆曾指出:「荒謬,其實就是指出理性種種局限的清醒的理性。」他在自己所處的時代目睹了現代理性主義的濫用,這使加繆得出自己的生存觀:「荒謬在這一點上使我豁然開朗:不存在什麽明天。從此,這就成為我的自由的深刻原因。」對加繆而言,生命的意義不在目的,而在過程,人的歷史因而是一部反抗荒謬的歷史,意識到這一點就是意識到自由。
那些認為加繆揭示了存在本質的讀者,對加繆充滿了感激之情。其中還有一個原因,結晶體不是火焰,它不會灼傷人。就像蘇姍·桑塔格所說,加繆是當代文學的理想丈夫,他的魅力不在於他的思想,而在於他表現出的道德之美,如果說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喚起的是敬意,加繆喚起的則是愛。愛這個荒誕的世界。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景凱旋;編輯:張進;校對:陳荻雁。封面為攝影師Henri Prestes作品,有裁剪。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