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个村,名字叫做吕公堂。相传是吕洞宾曾来过,后人修建庙堂,来往者祭拜,得名。
曾听说有个孩子坐在庙里的铁牛像上,坐上去,下不来,老人来给烧了把纸钱,才好。
自小年,迎来灶王爷爷,吃饺子,年来了。接着,做年豆腐,蒸饽饽,年猪肉,三道功夫活。我家老妈打下手,老爸做事细象,手艺漂亮,是主要负责人。
年二十九,爸妈煮肉,我再回村里。今年他们做了四大锅,全诚为了让我和老姐吃够。老爸还特地学了个大肠包小肠,耐嚼,香嘞。下午,妈妈请仙客,在炕上摆好桌子,九道菜,要有鱼有豆腐,有香烟,有酒,然后说道些什么。大致是祈求来年连年有余,风调雨顺,平平安安。

今年是大进年,年三十上午去祭祖。挎着垸子筐,里面五个饽饽,四盘菜,三道纸,两份水果,一瓶老酒。以前,还让带上几支鞭炮礼炮,现在管得严,入口处派人看守,不让放了。
大伯说,已经连续几年小进年了,今年是大进年。
立春时,下了一场大雪。陵园墓地里的泥土路混着雪水,比冰坚硬。我们顺着攀上去,路边地里长着麦苗,上面铺着雪,老爸说今年这好,麦子长得好了。大伯说,年五更不下雪就行。我问得知,年五更下雪,来年地旱。
爬上坡,找到碑,压好坟头纸。从同治年间第十世老祖,从右往左,十一世、十二世、十三十四十五世,再散叶,一代代生枝,成家成族。
到了我爷爷奶奶那儿,老爸明显变得柔软,给我介绍啊,然后自己悄摸地对着说话,给爷爷奶奶喝酒,给奶奶点上颗烟,最后叫我跪拜。记得爷爷去世时挺年轻,很突然,我小,长大我听我姐描述,老爸那时候整夜睡不着,眼睛里布满血丝,通红。
整个山上生满了侧柏,我站那儿,望天的视野唯独留了个空处,烧纸熄灭后升起了烟,我一抬头,刚好看到了旺盛的太阳,阳光穿过,吵闹之间,肃穆安静,我鼻子一酸。
路上也有女性,这里没有那么严格的男女区异,只要带着思念。
回家,贴对子(对联)。我要先去姥姥家贴,这是我和小姨家表弟的习惯。今年姥姥姥爷还没来得及熬仗子(面黏糊),去了我给现弄,很快就好,我也贴好,贴正当。和表弟同他们说会话,后天再来,别牵挂。
年三十中午,吃大米干饭。老妈用大锅做了笨鸡炖粘窝子(牛肝菌),肥肠猪肉粉条。伴着昨天熏好的猪肉,昨晚做好的肉冻、贺菜(胡萝卜丝)和香椿。姐夫他们家没有这习惯,老姐姐夫小外甥一并来吃。吃得很香。
吃罢,姐夫老姐他们一起收拾好碗筷,我偷懒带着小外甥玩,老妈老姐在沙发上聊天。她告诉我姐,一年里面最好的日子一定是年三十晚上,没有比这时候更好的时候了,叮嘱他们发动一下汽车,说一些祈福的话。
三十下午,收拾家里,然后躺着,直直腰。休息好,给客厅茶几、厨房灶桌、院子里的台子摆好鱼饽饽、花饽饽或钱袋,众多水果,还有三双筷子三酒碗,一座香炉。客厅还要更丰富,有些熟食,会一直续燃蜡烛。
将近八点,全家出动,炒菜上肴喝酒。十二点,最爱的菠菜豆腐素馅饺子上桌,带着面制的「钱串子」(类似面条),包着钱币,另配有红烧黄花鱼与煎豆腐。拜年,收第一份爸妈的压岁钱。夜里,从大门到里屋,各个门口放上拦门棍,我去天井院子里踩芝麻秆,应着早以来那句谣话「踩芝麻秆,当大官」。
朋友问我为什么吃菠菜豆腐馅,我问妈妈。她说,要论起来,菠菜是一种蔬菜,然后各自寓意(豆腐:都福;菠菜:有菜——有财);还有说道就是过年年五更守岁,不吃肉类,吃素,同菩萨同佛一样,吃素,不伤「岁」(动物)。朋友回复到,讲究。三十往后,新年伊始,就是我小家习惯。初四基本歇下,上山,拾柴(拾「财」)之余,并呼吸新鲜空气,健康身体。老爸开车,路上沿途村庄,会一路介绍。有些名字起的好,福禄并,满堂峪,光明村。

民间是一个实践的概念。民间故事经由传与说,不停地完善,民间故事是最伟大的文学母本。
初一到初四,是我在村里和小学同学、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刻。大家讲话,从前往现在,各村子,各个人,说在了「命」上。
痛事。癌症大致是农村里来势最凶最快的病。癌症,谁也无法抵抗,把人身体炼干,并把人硬生生地疼死。在以前,村子里将这种病隐晦地称为「不好的病」。现在普遍了,直言说癌。具体到什么癌。
今年,又听到这样的事。一位老人活到了八十岁,一辈子健康,突然吆喝身体疼,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淋巴。整个人以极快地速度从能站着、勉强站着,躺着,再到爬不起来。听说儿媳妇照顾,婆婆偶尔哗哗地流泪,是在说着抱歉。
还有一对兄弟,都七十多岁,一位一辈子从医高明,一位一辈子种地辛苦,同一年得癌,并随着同一年死去。成家立业后,他们的交集不多,上天却安排地如此默契。
不止老人,还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位母亲,肝癌,走后,结婚的女儿被婆家认作怕有「遗传」,「抬不起头」。还留下一儿子,丈夫带大。
除了癌症,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病。折腾着钱。
一壮男力,父亲早走,只剩母亲。成家立业,有了一对孩子。就突然地肾不好。家人借钱,十几万。他的母亲为他捐肾,愣是说哪怕我疼死了,我也不能让我儿子一家就这么败了。好在成功,老人和这男人身体都挺好,可以干活挣钱。还完债,孩子也健康地长大,一家很好。
也有相似的故事,父母没有为孩子捐肾,男人身体慢慢地塌了,两天一做透析,他的妻子从相伴到不伴,带着孩子在另个屋子里住。公婆管着这个男人。人们做出理解,天长日久得,谁能熬住呢?谁又有资格说这是必须去做的呢?该当的命运。还有人说他们刚结婚没多久,丈人车祸离去,这个媳妇和这个地冲着,命里压不住福,不该来啊。

玄事。说起来怪,玄,很多地方都和不同的人冲着。史家庄的去不了姓「朱」的;朱家庄去不了姓「史」的;郭村店子发不了姓「郑」的。还有姓「解」的去不了大娄村,听传当时孙膑把这儿给封住了,没有下地水,都从面上流,换到河西村,就好很多,「解」(蟹子)找到水,奋生。还有村子都有着自己的谣传,柳树沟出「疯汉」,小管庄吹唢呐,但流传被人坑害,给地主家的狗出殡去吹,没有人再用了。
我问咱村呢,我妈说咱们村这都发,以前是庙,来来往往。
还有些人家冲路,家里不旺,各种出事。是风水,找人破。这些人有些会算,有些人会看事,有人有「阴阳眼」,能通着。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天定。但这些人一定不会算的全准,时准时不准,话也是七八分数,否则,这是伤天理。
还有事关坟地(林地)的故事,有位老人去世,放骨灰盒时,有同族别家兄弟偷偷在棺材里放了一个秤砣,那几兄弟紧接着靠贩菜卖菜发了家,在那时候一大车土豆挣一两千块钱。但是后来,没几年也就败落了。
还听他们说很久以前,村子里有道士,每到过年都用符,老鼠都来进盆里,他洒粮食给它们,说道着过年了。道士都是半夜行事,鸡鸣回家,不看回头路。还有个厉害的道士被请去不知道做了个什么事,再也不做,很快也逝去。
这些民间故事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历代传说。听听就好。
人事。说回现在,姥爷今年八十岁,知道村子还有九百多口人,四百多户人家。四大间平房再怎么好也不惹人喜欢了,人人都奔计住楼。
村子里以前周围是田地,现在全是工厂。村前的「场」早已经全是挺拔的杨树,等着被占,等着赔钱。大地永远都在奉献。
和小学同学们每年见一面,现在,他们有些已经工作,太大的压力,太多叹气声。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大都是沉默。我们只好回说着以前,那片「场」,我们跳树桩,我们在土地上奔跑,没管辖。接着有网,各种游戏丰富我们跑在田野,走上学路上的玩法。
工厂成为人们的生活,村子里除了极少数老人留恋大地,没人想去种地。但工厂也累,男人一天两百左右,女人一天一百二十左右,算是不错。以前的争在田间地头,现在争在工厂。为了钱,为了活轻快,人性的「坏」极具在此。我还听说一些,同村的落户的人将同村的孩子在那年冬天撞死,赔不起钱,坐牢。同村的人给同厂子里的人下药,赔不起钱,坐牢。这个世间总是浓郁着一些伤感,中和着希望的美丽。凝成一个民间常说的字,就是「命」。

之前老师发过一首诗,开头:
以前我在农村,
和村里人格格不入。
后来我在城市,
和城里人格格不入。
孤独像乌鸦的双翅,
不离左右,统筹兼顾。
我评论:为什么,我总是体悟到,我既是农村人,又是城市人,格格都入,是假象还是真相?
老师说,你是百搭,我是白搭。各顺其不自然。
现在我想,这不是假象与真相之争,这是喜怒哀乐,这是我生长在农村、所拥有的天然的情感。
这是一个个风俗习惯,经历了众多的手;这是一个个村子里的故事,经历了众多的口。
每个人都是最后一代。大致去年,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周围同龄人知道这些的「最后一代」。随后,我便有意识地听他们说,而这说的,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今年,能去往拜年的人家越来越少,拜年越来越简单,老人也越来越少。
在广袤的大地,大地苦得真实,让人生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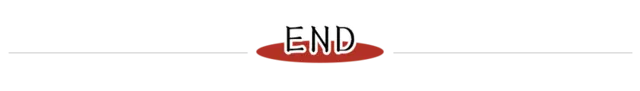
张涛
壹点号一食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