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改版后,
为了方便大家以后找到我们,
不要忘记 「星标」 哦 ~
「
这场大雪似乎会持续到永远,它们来自一团混沌的灰色旋涡,填满了无边无际的虚空,仿佛每一片雪都诞生于我感知到它的那一刹那。
-
[美] 菲利普·肯尼科特
」
最近几天,你的城市下雪了吗?
身在北京的未读君,这几天由衷感受到了大家的快乐,在社交媒体上也刷到了来自南方的羡慕。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明明长大了,还是会像孩子一样期待下雪呢?
每个人对雪的愿景不尽相同,但一场大雪,能为我们带来冬天最特别的记忆。
在你的印象中,哪场雪最让人难忘呢?
在 柯克斯书评2020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 【复调】 中, 菲利普·肯尼科特 回忆起童年时的大雪,以及与母亲不算美好的相处,坦诚成长历程中的思考。

[美] 菲利普·肯尼科特|著
王知夏|译
未读·文艺家|出品
天还没亮就开始下雪了,当闹钟在六点半响起的时候,地面上已经积了几英寸的雪。学校停课了,我满心欢喜。窝在暖和的床上,打着瞌睡,我暂时幸免于每天早晨去上课前都会填满我内心的恐惧。
那年我十四岁,正在上初中,受到一帮残忍暴戾、喜怒无常的校园混混儿欺凌。不过这一天却属于我自己。

母亲关在自己的卧室里不出来,这可是喜上加喜。早上起床以后,我下楼去她存放大学时代的旧藏书的地方,翻出了一本从未读过的但丁。
我惊讶地发现它居然如此通俗易懂,很快我便迷失在他的【地狱】里,为之惊心动魄,我又害怕又激动地邂逅了「忿怒者」「愤怒者」「亵渎者」,看到软弱善变的天使们太害怕在诸神的争斗中站队,因此永远徘徊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有的名字我认识——狄多、特里斯坦和阿喀琉斯,还有其他一些人名我完全没见过——塞米勒米斯、忒瑞西阿斯,还有宁录。我渴望认识他们所有人,这些富有魅力的悲剧人物来自不同的神话、历史和传说,被苦难联系在一起。
然后我开始练琴,在走音的钢琴上弹了一首舒伯特的即兴曲——尽管已接近正午,我还是害怕惊动母亲,故而专门挑了其中相对平缓的部分来弹。
到了午饭时间,母亲依然没有动静,我只得走到她的门前,轻轻地敲门,请求她允许我给自己做个三明治。对我来说,饿肚子是家常便饭。

那个午后我美美地吃了一顿,直到饥饿感退去,而雪还是下个不停。 我想要冲进雪里,尽情撒欢,感谢它为我带来了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天 ,于是我决定给母亲一个惊喜,自发把车道和小径铲干净。地上的积雪又湿又重,足足有一英尺多厚。
这活儿干起来虽然累,却让人心情愉快,我一边铲雪一边哼起了歌,哼着舒伯特和我最近学会的其他乐曲片段。我想象当母亲发现我主动认真地完成了一项不讨喜的体力活时,该有多么吃惊,多么高兴。
在傍晚时分的灰色暮光中,我感觉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大功告成以后,我脱下靴子,把它们留在了前门边上,然后回到自己房间,钻进被窝里接着读【地狱】。

我又一次沉浸在但丁的书里,突然间,我听到她在喊我的名字。她向来如此,当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看书的时候,她就会变得焦躁不安。
她以前上过文学课,我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她的,里面遍布圆珠笔写下的笔记,字体很小,运笔娴熟,字迹漂亮。可是随着岁月流逝,出于某种我永远理解不了的原因,她开始对读书产生了怀疑,尤其猜忌别人读书。
我父亲是通俗小说的狂热爱好者,尤其偏爱惊悚小说和间谍故事,他习惯把书藏在屋子里的各个角落,偷偷摸摸地看。
我年幼的时候,身体可以塞得进沙发和墙壁之间狭窄的缝隙,我常常躲在那儿看书,一连看好几个小时,或者至少躲到她发现我不见了然后开始喊我的名字为止。
我总是事先就做好了阅读随时被打断的心理准备,特别是在没办法把它伪装成作业蒙混过关的时候。 对此我已然形成了一种惯性,无论何时只要我开始读书,我的注意力就会分一部分去防备她的出现,时刻准备着被她打断。
而她但凡知道我在看书,就会编出一件要我立刻去办的事情,一些突然变得紧急的闲差事,什么打扫车库啦,把书架上的杂志按大小和颜色排列整齐啦。
有时候,当她的喊声驱散了我的白日梦以后,我走到她跟前,会发现她愣在那儿,一时间想不出什么事来差遣我。她搜肠刮肚地想啊想,终于想出一招:把二楼窗户的窗轨擦干净,用湿纸巾把客厅护壁板的凹槽擦一遍。我答道:「可我昨天才擦过了啊。」她这才死心,放我回去继续看我的书。

这一次她喊我,我还以为会看到她眉开眼笑的样子,甚至还能得到她的褒奖。可她的声音却带着怒气,当我跑到前门的时候,她已怒不可遏。靴子,只听她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放在后门。「我们不是动物,」她呜咽道,「我们不住在牲口棚。」
我从没听过这个规矩,可能是她在那天下午新制定的。我嗫嚅了几句铲雪的事,她却依然怒火中烧。她用两只手扇我,打我的胸口,打我的头,她让我拿着靴子,沿着门厅把我一路推到后门。她个 子小,打人不怎么疼,除非手边有扫帚柄或梳子之类的工具可抄。
挨打是件丢人的事,但也无非是看着对方大吼大叫,挥舞双臂,被掴几巴掌而已。
可这一次,她的愤怒却甚于往常,也有可能是她误判了自己的力气。
我就这样被赶到了房子另一头,那里有一扇通向露台和后院的滑动玻璃门,我看到她的靴子整整齐齐地摆在下面的垫子上,于是我俯下身把我的放在它们旁边。她一掌狠狠地打在我后颈上,我一个趔趄扑倒在地。我趴在那儿,脸贴着地面,双臂紧紧地抱住头。我哭了起来,眼泪让我羞愧难当。我想对她大吼,要她明白她打伤我了,可我还在变声期,从我嘴里吐出来的话语只不过是孩子急促的尖叫。
「别他妈演戏了。」说完,她气冲冲地走掉了。
我想,她大概是在生自己的气,气自己让暴力失去控制,超过了平常的限度,我也生气,因为我哭了。
我拼命唤回了我的尊严,哪怕在学校里被男生们折磨殴打我也一刻不曾放手的尊严。我终于止住了眼泪,强行压下喉咙里正在转为啜泣的抽痛。我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不仅因为铲雪铲得太辛苦,更因为完美的一天就这样毁掉了。
母亲已逃回她的房间,房子里又一次只剩下我自己。我在地板上翻了个身,仰头望着天空,大片大片的雪花密密麻麻地从那里落下来。

这场大雪似乎会持续到永远,它们来自一团混沌的灰色旋涡,填满了无边无际的虚空,仿佛每一片雪都诞生于我感知到它的那一刹那。 它们让我的意识变得迷蒙,我躺在那儿,在白昼逝去前的最后一丝光线里,试图想象自己身在别处。
我想跟我不存在的朋友聊聊但丁。我想找博览群书的人请教一下,但丁的地狱为何谁也不饶恕。为什么未受洗之人就必须受苦受难,哪怕他们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一生完美如楷模?为什么在地狱的现实和神怒的威力抹消了对上帝存在的一切怀疑之后,受天谴的人还是一个个怨气滔天,满口咒骂,互相攻击,甚至反对上帝?我想,他们可能是在怨恨主,怨他的规则翻来覆去,怨他残忍无情。他们也有自尊,他们都在心里认定了一个事实:他们罪不至此。
我把这一刻定为我个人神话中的一座纪念碑。 从此我决定告别童年,至于这个决定是否确实是那个下雪天我躺在地板上做出的,其实并不重要。
我只是选择以此来纪念那个时刻,即便不是那一次,它也必定发生在我人生中差不多的阶段,也许是另一次挨打以后,也许是她当着别人的面打我——那就更让人难堪了。 无论如何,我下定了决心,我不值得沦落至此,不值得这么丢人现眼,躺在地上哭哭啼啼,生闷气。
刚才我还读着但丁,自主地承担了扫雪的职责,我还觉得自己独立了,长大了,谁知一转眼又变回了小男孩,任由母亲摆布。
于是我决定立即结束我的青春期,全身心投入重要的事情。 至于重要的事是什么,除了但丁和舒伯特之外,我还不太确定。但我隐隐觉察到在书籍、音乐和艺术之中还存在另一种生活,比起将我引至眼下这个时刻、这种卑微境地的纷乱琐屑的人生,那儿要充实得多。

那天下午我制定了自己的规则。我把母亲设定为我的敌人,下决心再也不被她偶尔的亲善迷惑,再也不跟她说任何重要的事,再也不要信任她。我看透了,如果不将她从我的生活里连根拔起,她就会把我的人生撕成碎片。
我会行为端正,举止得体,最重要的是不失体面。 可我知道我必须跟她保持距离。 我知道我必须远走高飞,再也不回头。
要将这些决断付诸实践并不容易。 我还要跟我的家人和这个家绑在一起好几年,权宜之计就是以退为进,自我放逐,缩进一副沉默寡言、捉摸不透的躯壳里。 而一旦有了机会和条件,我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严肃、有意义的事,然后我开始严格地践行我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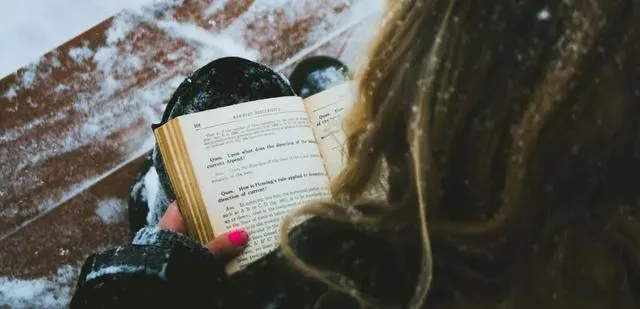
如今回想起来,把自己的情感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东拼西凑的脆弱基础上,此种做法似乎愚蠢得很。但我别无选择,更何况随着岁月流逝,借来的东西或许终将属于我们,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所有物,如同我们生命中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真实。
所有的品位都是从别处得来,我们要么主动在世界中找寻最佳范例,要么下意识地将身边的事物照单全收。
起初,读书不过是一项生存技能,让我遁入母亲永远无法尾随我到达的玄秘之境,久而久之却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与我真正的自我意识融为一体。
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看烂书,哪怕是消遣性的闲书我也不大爱读;我也从未对流行音乐产生过丝毫兴趣,除非有些歌与旧日恋情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 我依然相信每本好书、每首伟大的乐曲都蕴藏着救赎的希望,哪怕我心里一清二楚,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迷信。

-本期话题-
你记忆最深刻的那场雪,发生了什么故事?
留言区分享~

编辑| 泰若克塔
封面|【小森林 冬春篇】
图片|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