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臭鳜鱼是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的产物,也是相对昂贵的食材,发酵风味、重火功,是徽菜当仁不让的代表作;笋则是「山珍」,平易近人,唾手可得,代表了徽菜的乡野风格。』
记者|驳静
摄影|张雷

臭鳜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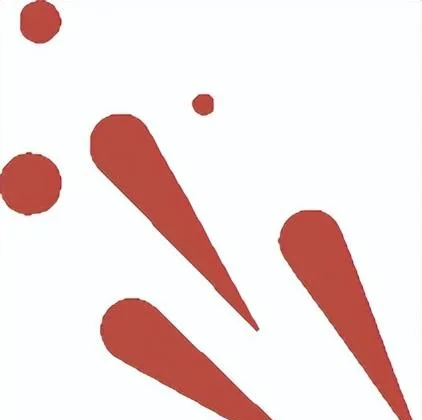
古徽州历史悠久,可这臭鳜鱼的历史或许不足100年。时间有待商榷,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臭鳜鱼还只是祁门人——至多徽州人逢年过节吃的一个大菜。徽菜厨师大规模开始学习鳜鱼腌制,也要等到2000年以后。徽州摄影师张建平说他20年前听朋友讲起一桩笑话,说是1987年,也就是黄山设立地级市那一年,屯溪有个祁门人开的餐馆,给两位上海客人做了条臭鳜鱼吃,上海人接着就将此事告到了卫生部,谴责黄山人做臭鱼给他们吃。
但臭鳜鱼在徽州地区流传开来并不难,因为徽州人本就擅长吃深度发酵的东西,毛豆腐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我们到徽州的第12天,开始跟张建平走年俗的寻访之旅,其中非常有意思的插曲,是到祁门县城后,小小地探索了臭鳜鱼的起源。
关于臭鳜鱼的来源,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 这个版本里,徽州人所吃的鳜鱼来自安庆与贵池,而从安庆到徽州走山路,路程需要走一周,过去徽商将货物运至安庆后,会在当地采购鳜鱼返乡,为防变质,于是加盐腌制。然而鳜鱼仍然发臭,没想到烹饪之后非常美味。这道菜由此开端。不过张建平一直觉得这个说法并不靠谱,他判断的依据之一,在于祁门水系发达,徽商以陆路运鱼,莫若水路合理。
旧时徽商进出祁门有三条道,去往江浙沪的走新安江,去南京的走青弋江,还有一条就是阊江,它发源于祁门深山,途经江西景德镇,最后注入鄱阳湖。祁门三里街沿阊江而建,凭借水路,一度十分繁华,特别是连接阊江与金东河的周家嘴码头一带,商贾众多。三里街最西头,曾经有座中和楼,创办于1909年,创办者陈凤卿之子陈达人曾手写过一本回忆录。我在原稿上读到他写,中和楼到1942年,「因政局动荡、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方歇业」。

▲钟大厨做的臭鳜鱼
中和楼的第三代陈再贵今年70多岁,他出生时中和楼就已经没了,但从小听长辈提及当年盛况。陈再贵退休之前,与张建平是同事,二人都在祁门县教委工作。他现在仍然住在三里街,只是中风后就不太能说话了,看到张建平,能含糊地吐出「教委」二字。张建平对一切有传承的东西都相当留心,多年前,他听陈再贵跟他谈起过,说臭鳜鱼就是他家发明的,也曾讲述过当年中和楼是如何开始烧臭鳜鱼的。
故事是这样讲的:祁门水系发达,但大多湍急,不产鳜鱼,下游鄱阳湖的鳜鱼相当便宜,中和楼每年冬天都会从鄱阳湖流域买鳜鱼。有一年春节后,中和楼想打个时间差,趁3月份的倒春寒,让货船再带两桶鳜鱼回来。结果带到半路天热了,等货船抵达三里街,鱼稍微就有点臭了。臭了怎么办呢?中和楼的大厨索性就用盐腌一腌,腌完后他们自己烧一条来吃,徽州人本来就能吃点臭的东西,这一烧,发现鱼肉有股特别的风味。
不过遗憾的是,陈达人的回忆录中并未提到关于臭鳜鱼的太多信息。陈再贵的夫人不是祁门人,她告诉我们,她嫁到陈家之前,也不会做臭鳜鱼,但长辈与左邻右舍都会,她也很快就学会了。无论起源如何,臭鳜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是确信无疑的。曾在北京一家徽菜馆吃饭,一进门就有浓重「臭」味,这味道在食客与从业者心里,或许已经代表了徽菜风格。
到徽州头一天头一顿,徽州文化博物馆前馆长陈琪带我们到「钟大厨」吃臭鳜鱼。主厨兼老板钟少华从业30多年,做臭鳜鱼是一绝。后来再回想之后16天吃到的种种臭鳜鱼,最大的感慨是,发酵食物果然风情万千,在小饭馆,在乡村厨娘家中,在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知名馆子里,同是臭鳜鱼,风味却有很大不同。 比起烹饪手法的不同,更能造成差异的还是腌制鳜鱼的手法。
鳜鱼腌制之前,实际上得是新鲜活鱼。但不像江浙一带,不管多小的馆子,都得备一个水缸,让客人直接从水里挑活鱼,徽州饭馆厨师备菜,通常在菜市场就让老板杀了鱼取走内脏。腌制的关键当然是码盐的量。厨师会说,这是非常依赖经验的手艺,当天的气温、鱼的大小,都是影响因子。少量腌制还相对容易控制,大一点的饭馆,一天腌几百斤鳜鱼也是常事。那种时候需要厨师额外用心, 因为码过盐的鱼要一条一条压到桶里,那么上层的鱼与下层的鱼,所受压力与盐卤浸润也有区别,每隔一天需要翻桶,把底下的鱼换到上面来。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怎样判断腌制是否到位了呢?不止一位厨师告诉我,就看鱼嘴,一旦变红就要收手,等到鱼嘴发绿,那就为时已晚。在这一点,钟少华有不同看法。他腌制鳜鱼的秘诀恰恰就在等鱼嘴变绿,这个变化基本发生在第八天左右,这意味着鱼肉开始二次发酵了,那时候的微生物更加丰富,也正是风味层次的来源。闻味道固然可以作为判断依据,钟少华说他光看流下来的卤汤汁就能分辨,「假如汤汁是油性的,不是水水的感觉,就到位了」。
钟大厨给我们烧的不是整条的鱼,而是鱼块。原因很简单,我们一桌四人,都是好这口的,一条鱼大概率是不够吃的,反而不如上一份块大量足的鳜鱼鱼块来得过瘾。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鳜鱼质地原本就紧实,腌过之后,鱼肉变得更硬朗,吃进嘴里,对牙齿会有微微的抵抗,这是鱼肉少有的质地。我们一桌四人,包括钟大厨和陈琪,很快就将其瓜分。这还不算,又要了米饭,拌进汤汁,一人又来了一碗。我一边吃一边心里面担心,吃过如此美味的臭鳜鱼之后,恐怕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想吃普通的鱼了。
徽菜本来就注重火候,钟少华现在教徒弟,会跟他们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盖盖焖烧的时间。菜籽油下锅后,第一步就是把五花肉丁煸散、出油,再下生姜和大蒜等佐料,但鱼要两边各煎烤一下,之后加入酱油、料酒和高汤,此时要盖上锅盖焖烧起码20分钟,入味的秘诀自然在于时长,鳜鱼好就好在这里,它是很经得起烧的,一定不要浪费它的潜质。其次是大火收汁的尾声,再加一勺猪油入锅,能让整个汤法变温柔。这个臭鳜鱼的酱汁,很多小饭馆会因时制宜,比如到冬天,会加入冬笋丁提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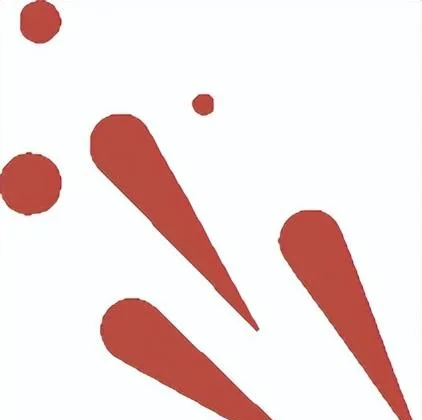
笋与笋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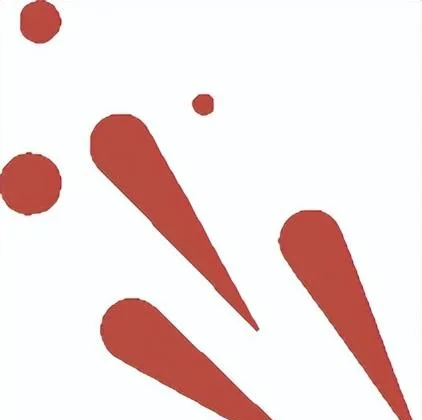
除了臭鳜鱼,徽州另一样深得我心的是笋。在歙县的安若餐厅,小胡师傅打算给我们置办一桌全笋宴。
我是在浙江山上见过「孵笋」的,在恰当的时节里以水浇灌地表,就着湿润的土地,铺上厚厚一层竹叶。假如以温度计测之,会发现竹叶底下比外面高上好几度。这种欺骗的成果是,临安春笋能比它原本的上市时节早上大半个月,那便是宝贵的溢价时机。在歙县,一切服从自然。举头看问政山,满山竹林,翠绿可亲,小胡说这意味着今年算得上大年,冬笋产量不错。像去年,下半年普遍干旱,那个时候看到的竹林是枯黄的。他们餐厅去年也买不到冬笋,有阵子不得不拿福建和江西的笋代替,那是小胡头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笋与笋之间可以差别那么大。

▲最理想的笋是「两头尖」,这说明它很嫩
传说中,歙县的问政山笋嫩如婴儿肌肤,吹弹可破。不止一个人向我描述,他们经历过的神奇场景:一不小心将笋摔在地上,白花花地碎了一地。一个夸张的叙述一旦成势,就容易在人们脑海里固定为一种「事实」。我们当然是没有荣幸见证这样的现场的。不过问政山笋的确是鲜嫩可口,非常值得一吃。
关于笋,有三大乐趣。先是背着锄头去挖笋,其次是挖到笋,最后才是吃。比起吃笋,显然挖到笋的乐趣最为无穷。
12月,农事已忙完,备年货尚不紧迫,有山的人家会趁这时上山松土。我们在紧挨着问政村的范家村地界里,碰到一位大爷。大晌午的,老人家在竹林翻土,半小时未曾停歇,只微微出汗。旁边一只簸箕,装着的三四颗冬笋有手腕粗细,头上冒着尖儿,颜色嫩黄曲线伶俐,十分可爱。与此同时,隔壁山头,还有小胡师傅与一位比他年纪更小的同事,正在为晚上的全笋宴全力挖掘食材。
我一会儿跑去大爷这边问东问西,一会儿又去小胡师傅那边指指点点。以我这个外行人来看,两位小年轻的道行太浅,几次见他们一锄头下去,就有一颗笋被拦腰斩断。「挖断笋」更好,或者干脆「挖不到笋」?很难在两个次级方案里选出优劣。我像是在两个直播间里来回切换的猎奇观众,咂摸出一点味道后,便对两位技艺不精的年轻人失去兴趣,转而专注地欣赏大爷松土。只见大爷的锄头轻起轻落, 有时明明已经击中泥土里的冬笋,却能在感觉到阻碍后迅速收力,千钧一发之时,总能保全冬笋的完整身躯。

▲我们在山上碰到的大爷正在给山松土
最后,我这位观众擅自为「两个直播间」打分。只是为了松松土的大爷,战果是完整好鲜笋七颗。小胡二人组收获倒也不小,共计六颗,其中四颗有大破损。年轻人可以说是完败。不过不要紧,小胡还可以凭借厨艺为自己扳回一城。当晚,小胡果然烹饪了六道菜。
餐厅里头吃问政山笋讲究外形,所以会先拿整颗笋与整块火腿先煨,入味之后再改刀,都切成薄片上桌前可以一蒸了事,切成块那么可以炖,都是鲜与鲜的组合。煨过的笋凉了之后还可以切成丝,拌上雪里蕻,就是一个上好的凉菜。另有腌笃鲜和油焖笋,其实这两道菜一般总以用春笋较为常见。春笋大量上市的时候,价廉物美,可以放肆地以笋为绝对主角去烹饪菜肴,但既然到了笋的产区,春笋能做的菜,冬笋当然也做得。
「山上笋,山下柴」, 冬笋埋在地下,更是见光就老。小胡说吃笋的极致体验是上山的时候带上块火腿和一口锅,挖到笋后,劈个灶,用山泉水直接煮,方法粗野,但是味道鲜美。徽州多山多茶,茶季上山劳作是很多村里人每年必做之事,早上出门,中午吃干粮,天黑回家,出门前煨在炭火上的咸肉炖笋已经饱经火候。笋是最经得起炖的东西。
比起鲜笋与腌肉的组合,我更中意的却是两个小菜。
一个 是炒杂酱。 徽州人会制作冬酱。入冬前的小黄豆,蒸熟,让它们发酵,与秋天下霜前采回来的新鲜辣椒碎拌在一起,加入蒜和姜,当然蒜要多一些姜要少一些。这几样主要元素混在一起后,就可以密封,让它们二次发酵。过上一个月,时间也来到了深冬,冬酱就可以开坛了。春节期间,总得红烧牛羊肉,这些腥味较重的肉菜里,主妇可以大胆地往里搁冬酱。在安若餐厅,小胡还会在冬酱的基础上,再炒一个杂酱,五花肉、冬笋、茶干,都切成丁,与冬酱炒制,就是一个上好的下饭菜,要拿去拌面吃也是不在话下。
另一个说起来也是小炒。在徽州,我发现当人们说起「浇头」,大概率是特指笋干炒肉丝。 起初是在歙县的「两棵树馄饨」见到一大盆浇头放在灶边,老板娘说,她店里老客人多,虽然都是冲馄饨来的,但一天下来浇头面总也能卖出不少碗,总归有嫌馄饨饺子吃不饱的客人。徽州人办红白喜事,乡宴厨师一大早会烧好一大盆笋干炒肉丝,来送礼的、帮工的,谁来了都吃碗面再走。厨师总会把这盆浇头做得油水十足,除了笋干,其实还有豆腐干丝,加茭白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有人说,不知怎么回事,这浇头,一大早赶做出来的,总不如头天晚上的滋味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