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刚建立那会儿,邵阳县城有个毛县令。这毛县令可是个断案的行家,经他手处理的案子那可多了去了,每一件案子都让人佩服得不行。
这天毛县令在书房看书呢,突然唐捕头和肖捕头急急忙忙地跑进来,嚷嚷着:「大人,坏事儿了!开武馆的单西六让人给毒死啦!」「哦?」毛县令把书卷放下,赶忙问:「在啥地方?」
唐捕头回话说,在东城浴池!行,那别耽搁了,跟我走!毛县令领着俩捕头火急火燎地奔到了东城浴池,店掌柜把他们领到最里头的一个单间,就瞧见单西六光着身子趴在地上,那脸上的神情痛苦得很。
浴池边的石桌上放着一把大茶壶和几块七巧板,地上有个打碎的茶盅,毛县令弯下身子认真瞧着,发现茶盅底部有些褐色茶末,便把茶末抓起搁到了石桌上。
毛县令问掌柜:「你啥时候发现单西六死了的?」掌柜回答说:「单西六每次来,都先在浴池泡半个钟头,完了起来喝杯茶,再练会儿气功。今儿个我没见着单西六练功,也没听着他叫小二给他冲茶,我就觉着不大对劲儿,赶过来一瞧,单西六已经躺地上了。」
当毛县令跟店掌柜说话的时候,唐捕头和肖捕头把所有进过浴池的客人都询问了一遍,初步判断,这个单间没人进去过。
唐捕头说:「这就怪了,单西六咋就被毒死了呢?」肖捕头回应:「肯定是有人悄悄溜进单间下毒,浴池里客人喝的茶水都是花厅那大茶缸泡好,再灌进茶壶的,要是凶手把毒药放到那大茶缸里,这儿的客人恐怕都得遭殃。」
毛县令指着茶盅碎片上的茉莉花瓣,问店掌柜:「你们店用这茉莉花茶吗?」店掌柜摇头回答:「哟,咱店可没那钱用这么金贵的茶叶。」
毛县令点了点头,把那带着茶末与茉莉花瓣的碎片以及茶壶,一块收拾好给了唐捕头,让他好好收着带回县衙去。
唐捕头把碎片拿油纸包起来,猛地瞧见石桌上有个七巧板,再一瞅,不对劲呐,就喊:「大人,您瞧瞧!这七巧板少了一块!」
毛县令一低头,嘿,还真是少了一块呢!再瞧那躺在地上的单西六,右手攥得紧紧的,难不成在他那手里头呢。
毛县令把单西六的右手掰开,嘿,这手心儿里还真有一块三角形的七巧板。得,这准是单西六临死前匆忙弄好的,那他这是想跟咱说啥呢?

毛县令起身去了账房,让账房先生讲讲单西六今儿来浴池的事儿。账房先生答道,大人,单西六是咱店里的老主顾,每两天来一回,今儿个单西六跟平常一个样,中午的时候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就来了。
毛县令接着问:单西六来了以后,又有啥人来了?账房先生答:随后米铺的习掌柜就来了,要了个单间,再后面来了四个小伙,他们洗的是大池子。
哟,毛县令一听这话,眉头就皱起来了,问道:「你认得那些小伙子不?」账房先生回答说:「有三个看着挺眼熟,就一个不认识,那人穿一身黑,黑衣服黑裤子,还戴个黑帽子,把眼睛都遮住了,脸都看不清。」
毛县令问:「你瞧见他们从浴池出来没?」账房先生琢磨了一下回答:「嗯,没瞧见,大人,您瞧,那几个小伙在那儿呢!」账房先生猛地指着前面一个人高声喊道。
唐捕头动作麻利地把那小伙给叫了过来,毛县令询问道,你们今儿一块儿来的这伙人里,是不是有个穿一身黑的?小伙回答说,哟,大人说的是这人啊!我们都不认得他,前几天我们来的时候,就瞅见他在浴池店门口晃悠,好像是在等人,今儿我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们一块儿进去了。
哟,听到这儿,毛县令心里一紧,忙问:「那你看清他长啥样没?」小伙回答说:「他又矮又瘦,帽子戴得很低,有一撮卷发露出来,眼神可凶了。他买的是单间的票,可我们没见他去单间洗澡。」
好嘞,晓得了!毛县令跟小伙、掌柜还有账房先生道别后,领着两个捕头回县衙去了。第二天上午,开医馆的古掌柜,就是那县城县衙的仵作,把验尸报告递给了毛县令,讲道,大人,茶盅底部的茶末跟茉莉花瓣都有毒得很,茶壶里的茶倒是没毒。
嗯,毛县令点了点头,说道:「照这么看,那个穿黑衣服的小伙肯定就是凶手了。」唐捕头问道:「大人,您为啥这么说呀,那浴池里来来往往的可有六十多个客人呢。」
毛县令慢悠悠地讲,别人没法儿进单间还不被察觉。凶手穿黑衣裤,那是因为浴池伙计都这么穿。这凶手买了票但没泡澡,瞅着浴池雾气大的时候,悄悄溜进单间下毒。就算有人瞅见了,也会当他是店里伙计。
唐捕头点了点头,问道:「大人,那接下来咋整?」毛县令说道:「你去瞧瞧,单西六的徒弟当中有没有个长得矮的?」这时,肖捕头搭话了:「大人,我觉着不用查,单西六是开武馆的,他那些徒弟我熟得很,全是五大三粗的,没一个又瘦又矮的!」
唐捕头不甘心地嘟囔:「那凶犯有没有可能是女人装的?」肖捕头乐了,回应道:「那更不可能了,单西六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毛县令说了,嘿,这没准就是跟单西六结仇的关键呢,单西六把一个女子的追求给拒了,那女子气得不行,就狠下心把单西六给毒死了。
唐捕头回应道,毛县令讲得在理,越是对一个女人表示拒绝,那女人反倒越对你有好感,女人的心思啊,着实让人摸不透!
毛县令吩咐道:「你们去查查看单西六的徒弟,瞧瞧单西六最近是不是跟个女子有往来,再把古掌柜给我找来!」「是,大人!」两个捕头领命离开了。
两人离开后,毛县令一个人在书案那儿反复摆弄着七巧板。嘿,突然之间,摆出个图形来,毛县令一下子来了精神,哟,是只燕子,这图形是个燕子!
这当口,古掌柜进了来,毛县令发问:「那凶犯拿啥毒药毒死单西六的?」古掌柜答说:「大人,这毒药挺常见的,要是从这儿着手查,怕是没啥效果!」
毛县令问:「古掌柜在县城住好些年了,知不知道这街巷里有没有不守妇道的女人?」古掌柜想了一小会儿,说:「大人您要不提,我都快忘了。城隍庙有个年轻寡妇,叫珍娘。这珍娘凶巴巴的,还挺泼辣,长得有几分好看,念过几年书,能说会道的,就爱招惹人。她男人叫杜大亮,死了还没半年呢。杜大亮死得挺奇怪,可前任县令处理得太随便,没验尸也没备案,就这么稀里糊涂结案了。」
哟,还有这档子事!毛县令皱着眉,示意接着讲。古掌柜又道,那珍娘花钱雇了个姓杨的走江湖的医生,给杜大亮弄了个因喝酒太多、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的证明,交给了官府。
我那会儿瞧了瞧杜大亮的尸首,发现他脸色没啥变化,眼睛却鼓着,我觉得他可能是后脑被狠狠打了才死的,就跟前任县令说了,哪承想前任县令倒埋怨我瞎操心!
毛县令问:「如今还能寻着那姓杨的江湖郎中不?」古掌柜答:「他早走了。」毛县令严肃地说:「杜大亮死得蹊跷,我定要查个明白,给死者讨个公道!」
古掌柜走了之后,唐捕头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讲道,大人,真被您说中了,我问过单西六的徒弟,其中一个叫穆群的徒弟跟我说,有天晚上,他去师父家,碰巧看见师父跟一个女子在屋里聊天!
哟,毛县令赶忙问道:「那女子是谁呀?」唐捕头答道:「当时穆群没瞧见那女子的面容,就只听到那女子在屋里发脾气,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师傅管那女子叫燕子!」
燕子!听到这个,毛县令心里咯噔一下,来!赶快把珍娘叫来询问!得嘞,唐捕头领着衙役走了。
没一会儿,珍娘就被带到了大堂上,毛县令仔细打量,发现珍娘也就三十来岁,皮肤又白又嫩,脸蛋像桃花一样漂亮,确实是个好看的人。
毛县令发问:「珍娘,我问你,你男人杜大亮到底咋死的?」珍娘瞪大了眼,说道:「之前的老爷早就给我男人的死备了案、做了了结,今儿个老爷咋又提这事儿呢?难道是对我男人的死有怀疑,还是衙门现在没事儿干,拿我这寡妇寻乐子呢?」
珍娘这么一顿抢白,把毛县令给弄得心里特不痛快,心里想着,这女的果然是嘴皮子厉害,说道:「衙门仵作古掌柜本来要给杜大亮验尸,你却跟个江湖郎中一块儿先把证明给开了,想这么蒙混过去,是不是有这回事!」
珍娘一听,那气可就上来了,别跟我提那个古掌柜,他老是调戏我,啥便宜没捞着,就记恨上我了,还诬陷我!
毛县令一听,气坏了,嘿,这蛮不讲理的泼妇,大堂之上怎能由着你随口乱说、瞎扯一气呢,来人呐,给我使劲打!
左右衙役把珍娘给按倒了,抄起板子就开打。珍娘还挺横,扯着嗓子喊:「你这糊涂官,我到底犯了啥王法,你给我一条一条说清楚,让我服气,今儿个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我跟你没个完!」
珍娘给打得浑身是血,嘴里还不停地大骂,毛县令赶忙让衙役停下,这会儿没抓到啥有力证据,也没法把珍娘咋地,先把她收押起来等着审问。
第二天一大清早,毛县令把唐捕头和肖捕头喊到身边,这般那样说了一通,这俩捕头明白了,然后就转身走了。
过了晌午,唐捕头急急忙忙地回来了,讲道:「我跟珍娘的左邻右舍打听过,珍娘还没嫁人那会,小名叫燕子!」
哟,毛县令一听,眼睛放光。这当口,肖捕头兴高采烈地跑进来,拿出一套黑衣裤,说道:「大人,您瞧瞧!这是从珍娘家里搜出来的,我问过浴池的账房先生,那小伙穿的就是这套!」
好嘞,这就提审珍娘!毛县令这么一说,衙役们分作两排,立马就开堂了,没一会儿,珍娘就被带到了大堂上。
毛县令问珍娘:「我问问你啊,你还没出嫁的时候,小名是不是叫燕子?」
珍娘听了,呆住一下,接着嗤地笑了一声,说道:「大人,我小名叫燕子,这难道还违反大唐律法啦?」
毛县令把那身黑衣裤丢在珍娘跟前,大声质问:「这黑衣裤是从你家搜出来的,浴池账房先生确认过了,单西六被害那天,进浴池的年轻人穿的就是这身黑衣裤,你咋说!」
珍娘脸一抽,满是轻蔑地说道:「哟,大人问这黑衣裤啊?那是我家亲戚落在我这儿的。我这漂亮女人,咋会穿这么难看的东西呢,大人这问题可真怪!」
毛县令憋着一肚子火,把那天进浴池的三个小伙叫到公堂,让他们好好认认,这三个小伙对着珍娘瞅了老半天,摆摆头讲,大人,不是这人啊,那天进浴池的明明是个男的呀。
听了这话,珍娘愈发张狂,扯着嗓子喊道,大人断案就是不一样,我一个女人咋能进男人洗澡的池子呢,这话要是传出去,不得让人笑话死!
毛县令一脸严肃地问:「珍娘,你和那单西六啥关系?」珍娘冷冰冰地回应:「大人,您是不是没招了,咋又平白无故扯到单西六身上,谁不知道单西六是个练武的,我一个小女子,跟他能有啥关系!」
毛县令发火喊道:「你这泼妇嘴皮子厉害得很,可你犯了大罪,凭你那张嘴就能糊弄过去?想都别想!来人,上刑!」
衙役们一下子冲上去把珍娘摁在地上,紧接着就是一顿抽打,没一会儿珍娘就被打得浑身是伤,血直往外冒。这珍娘也是真有骨气,紧紧咬着嘴唇,都给咬破出血了,就是不认罪。毛县令摆了摆手,让衙役把珍娘带下去了。

退了堂,毛县令把古掌柜、唐捕头、肖捕头叫到后堂,毛县令问古掌柜:「之前你讲过,要是杜大亮后脑被狠狠击打,就会双眼往外凸,那杜家人给他下葬的时候,瞧见杜大亮后脑有伤痕没?」
古掌柜回应道,要是凶犯拿棉布包着铁锤去打人,那就不会造成伤口。毛县令问道,要是现在验尸,那被砸碎的后脑壳肯定会有痕迹,要是杜大亮确实是被毒死的,那现在还能查验出来不?古掌柜回答说,要是杜大亮是被毒死的,这检验起来倒不算难。
毛县令听后琢磨了一小会儿,随后很坚决地讲,行,我要开棺验尸!唐捕头赶忙说道,大人呐,开棺验尸风险可不小,要是找不着杜大亮被害死的真凭实据,大人您就得自己承担责任辞职走人,要是珍娘故意诬告大人您,那到时候可就麻烦大了!
毛县令眼神坚定地说道:「行了,这风险我愿意担,所有后果我来扛,你们都别多说了。明天下午,去北门杜大亮的坟那儿,开棺验尸!」
第二天下午,北门一下变得热闹非凡,老百姓听闻毛县令要开棺验尸,都跑来看热闹。衙役用草席搭了个凉棚,没多久,一口没坏的黑漆棺材就被抬出来了。毛县令在棚里坐好,珍娘被衙役带到旁边。毛县令见都准备好了,大声叫道:开棺!
衙役把杜大亮的尸首抬出来,缓缓搁在草席上。古掌柜认真地把尸首擦拭一番,就专心致志地查验起来,大伙都一声不吭地盯着。
古掌柜托起杜大亮的后脑勺仔细瞧了瞧,摇摇头,接着拿银棒把死者的嘴撬开,认真瞅了瞅腐烂皮肉下露出的白骨,啥异常也没发现。这时,古掌柜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好的感觉冒了出来。
最后古掌柜起身,跟毛县令讲,大人,杜大亮身上没挨打留下的印子,也不是中毒死的,估计是突然得病死的。
听到这话,毛县令大吃一惊,难道自己判断有误,杜大亮难道真是因心病而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毛县令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似的。就在这时,珍娘猛地扑到杜大亮的尸首上,嚎啕大哭起来,可怜的丈夫啊,死了都不得消停,都怨我名声不好,把丈夫给连累了,我还有啥脸活在这世上,不如死了拉倒!
周围的老百姓瞅见珍娘哭得那叫一个伤心,都在那纷纷议论着。珍娘哭了好一阵儿,突然瞪着毛县令,怒喊道:「你这个糊涂官,这下你得意了吧!你给我记着,我要去府衙告你,告你乱用权力,我跟你没完!」
瞧着珍娘哭得愈发厉害,场面都快没法控制了,毛县令正着急呢,这时候古掌柜的老婆,也就是县衙监牢的女典狱万苦花过来了,她小声跟毛县令讲,大人,一般女人在家里干家务,不光得洗衣做饭,还得给自家男人钉皮靴,那钉皮靴的铁钉又细又长,要是从人的鼻孔往脑后钉,不费啥劲儿,并且一点儿痕迹都不会有,别人根本发现不了。
哟,这事儿啊!毛县令听了后眼睛睁得老大,赶忙跟古掌柜说,得嘞,赶紧瞧瞧杜大亮的鼻孔!
古掌柜弯下身子,仔细瞧杜大亮的鼻孔。这一瞧可不得了,真发现不对劲了,随后用钳子夹出一根又细又长的铁钉。这铁钉在身子里待的时间太长,都锈得不成样子了!
铁钉一露面,大伙都惊讶地叫出声来,毛县令指着珍娘说,你还有啥可说的!珍娘一下子没了力气,软趴趴地倒在地上。

第二天一大清早,毛县令开堂审案子,这一回珍娘没了以前那股子威风劲儿,只能老老实实地把实际情况给说了出来。
我是珍娘,打小就好强,可命不好,嫁了个老实巴交的杜大亮,他就是个成天跟算盘、账本打交道的账房先生,我俩没啥恩爱,跟他过日子,没啥乐子。这天杜大亮回家,说皮靴后脚掌坏了,让我帮着修钉,我正修鞋呢,他又催我去做饭,说马上要出去收账,我一下来气了,就往饭菜里下了迷药,他吃了就昏睡过去,然后我把铁钉从他鼻孔钉进去了,这就是我害他的事儿。
那单西六咋死的?毛县令大声问道!珍娘叹口气说,哎,都怪我太痴迷了。一个月前,我在乡下走着,不小心把脚崴了,正着急呢,正好单西六经过,把我背回武馆,还帮我治伤。我瞧单西六长得壮实,模样也不错,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开始单西六也挺喜欢我,可没过多会儿,他就反悔了,想把我甩了。我珍娘哪是能随便让人甩的,我心里气不过,就扮成男人混进澡堂,悄悄把喷了剧毒的茉莉花瓣扔到单西六的茶碗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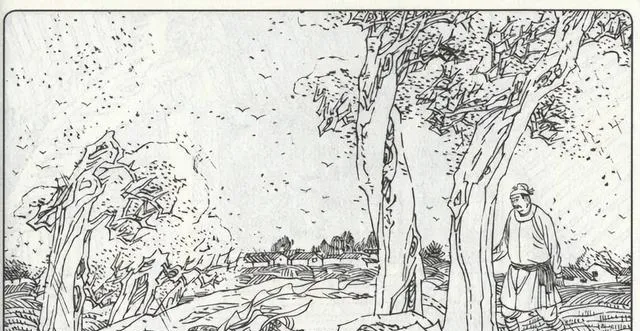
嘿,这妇人可真够恶毒的,求爱没成,就下这般狠手。来人呐,把这凶犯押进死牢!衙役把脸色惨白的珍娘给带走了。这案子算是结了,大家都挺高兴,可毛县令却满脸忧愁,把古掌柜和唐捕头领到了书房。
毛县令问古掌柜:「你啥时候跟万苦花成亲的?」古掌柜答:「三年前,那会儿她男人死了一年多了。」毛县令又问:「那她男人咋死的?」
这,古掌柜没法立刻回答。哟,我清楚了,唐捕头说道,她男人也是突然死了!
毛县令皱着眉,这事儿啊?那她丈夫死的时候有啥症状?唐捕头琢磨了老半天,猛地喊了一嗓子,哎哟,大人您要不提,我还真给忘了,她丈夫死时的样子跟杜大亮死的模样那是特别像啊!
哎,毛县令的心都快蹦出来了,那他们两口子感情咋样啊?唐捕头叹口气说,万苦花这名儿真没白起,就是个命苦的女人,她男人爱喝酒,脾气还贼差,老是揍她。她男人死了以后,万苦花这才嫁给古掌柜,总算过了几天舒心日子。
听了这话,毛县令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头乱糟糟的,纠结犹豫了老半天,最后才声音沙哑又痛苦地说道:「唐捕头,明儿个把万苦花带到大堂来,我有事儿要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