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想过,母亲癌症去世后,我还要面对同时患两种原发癌症的父亲。
他的病情没有我母亲那样凶猛,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医生对我解释, 父亲还能有半年的生存期。
半年时间当然很短,很让人焦心,但是对于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来说, 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其实不是怎么「留住」他,而是怎么更好的「送走」他。

这不是一个能被传统亲情关系接纳的说法。
当时我爸爸确诊不久,我阿姨就特意打电话来说,你一定要留住你爸,这是你在世上最后的亲人,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
我没结婚,没孩子,母亲九年前去世,父亲已经是我唯一的直系亲属。
坦白说,作为一个独生女,那一刻的无助慌乱是有的。
我不想让我爸爸离开我,我想让小时候那种有人依靠、有幸福家庭的感觉再延续几年。
甚至当时我还想,怎么年轻的时候不去结婚呢?这时候要是有个人能陪着我,说不定感觉能好一点。
但后来再去想,那只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感性,就算身边有一百个人陪着我,他们也无法改变我爸爸确诊癌症的事实。

我带着我爸,跑了很多次专科医院, 带他把基因测试、CT、各种自费检查这些都做了个遍。
某一个瞬间里我都会恍惚,我已经到了能带父亲看病、能替他去和医生沟通的年纪了吗?
我83年出生,我爸确诊那年我正好40岁,不惑之年,这份责任感不是不想要就能不要的。
我也必须站在我的角色上,替我爸决定很多事——
检查做完之后,我决定把他送到安宁病房。
当时我爸很高兴,他当时刚在中医院做完调理,真以为是去治疗的,以为自己的病还有痊愈的可能。

温馨如家的安宁病房
其实是没有的。
他的前列腺癌肿瘤标记达到三百多,比正常值高出几十倍,骨、淋巴、肝脏、肺上都有癌细胞转移,肝上还有个阴影。
医生说他贫血,做不了化疗,我只能带我爸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不过都能靠吃药控制住。
2023年年初他的炎症又开始发作,突然开始发烧,之后就开始掉秤,前后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
而且他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八九次,厕所的灯永远亮着。
我是当女儿的,不知道他的病到底是什么感觉,反正他睡不好,我也睡不着,带他去检查,就发现是癌症了。
拿了药之后,我本来以为他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这个说法不好听,我知道,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我爸变得非常惜命,非常注意吃药忌口,整天活在病情的阴影里,也开始焦虑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
他的生命体验感只剩个零头,但还是自己努力在往好的方向走。

安宁病房内部
药吃了一段时间,我爸的指标降下来很多,我高高兴兴带他去复诊,结果又发现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我只能一遍遍去问主治医师,又托人问了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最后大家都确定目前没有办法治疗, 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
作为独生女,其实九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给六十多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已经近在咫尺。
就是没想到,能这么近。
我对死亡和离别的态度,其实还比较理性 ,反正大家谁也不是神仙,没人长生不死,都得经历这么个过程。
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
我不惧怕死亡,但我怕我爸受罪,疼痛,最后毫无尊严的死去。

癌痛是很折磨人的,确诊结果出来之后,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
前期是癌痛,后期如果出现肠梗阻,腹水出来,他的痛苦程度会翻倍。
「疼的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生不如死」这种字眼到处都是,我看的难受,很不愿意让我爸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说的再难听点,这么多医生都已经给他下了半年的生死契约, 我难道要抱着那点主观性的期望,等着我爸在无比痛苦的治疗里,传出类似「能多活一天」这样的好消息吗?

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所以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我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
这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因为没有那么多仪器,气氛显得没有那么凝重。
不一样的是这里可以配到吗啡,这是最高等级的止痛针,我觉得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家属,这都是优点。
住在这的人奇形怪状。

这样形容不太礼貌,但当你真的看到那些腹部肿大、双脚浮肿、四肢各部分都扎着吊针的人,你可能也会这么去形容他们。
这些人多数都是中老年,陪伴在病床边的也多数都是中老年,应该是他们的老伴,年轻人就我一个。
他们一开始还很吃惊,觉得我这么年轻,天天往病房跑,自己的事怎么顾呢?
事实上我也不想来,但凡我爸还能有另外的儿女,我不会天天来。
这是我的老实话,我有我的创业工作,早上十点忙到凌晨两点,下班之后骨头都是酸的。
但我要让我爸身边有人,他已经病重到不能自理,我做不到让他自己在病房待着。

我也没有太多话和我爸聊,即便我坐在他病床边,多数时候也是两个人头对头看各自的手机。
我们俩就是中国传统父女,共同话题不多,讲话也简洁。
之前我爸还健康的时候,我表示感情的方法就是带他去吃饭,吃好的,但是不会说太多话。
我是八零后,我爸是一九五几年出生的,我俩代沟很大,看事看人的方法也不一样。
他当初想让我考大学找工作嫁人生孩子,我不喜欢这样,也没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我觉得我首先是我自己吧,先做好我自己,我才有精力去做你女儿,才能带你一起好好生活。

不过我做不到完全自由,作为独生女,我小的时候享受过绝对的爱护,现在也得接受这种「捆绑」生活。
我放弃过异国的爱情,放弃过外地的工作offer,寸步不离的守在上海,守在我爸身边。
就像他之前替我赚学费一样,我自己创业,开始替他赚以后看病住院的钱。
我妈去世之后,我把我爸接过来一起住,换了一套适合两代人居住的房子,就算我之后真结婚了,过其他类型的生活,我也能照顾他。
只不过我爸的身体没给我照顾的机会,他住进了安宁病房,并且可能再也不能回家了 。
肠癌发展到后期的时候,我的亲戚们开始出主意,有的说认识医生,有的说知道哪种药好用,但我觉得这种都已经被客观确定的事实,根本没有必要用这些主观的妄想去弥补。
这些说法如果被我爸知道,那么好,他就觉得自己多了一种被治愈的可能;
但根据他的现实病情,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吃完,他的病情很可能还是没有好转,甚至更差,这种巨大的精神落差不亚于新的宣判。
我的亲戚们只需要提一嘴,但去签同意书、承担我爸负面情绪的人是我。
当时我爸爸已经是肠癌晚期,和前列腺癌还不同,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晚期患者难以控制自己的排泄。
而且他们的排泄物和正常人的还不一样,是黑色的,带有癌细胞特有的异味。
护工给他换一次尿布,满病房都是那个味道,很难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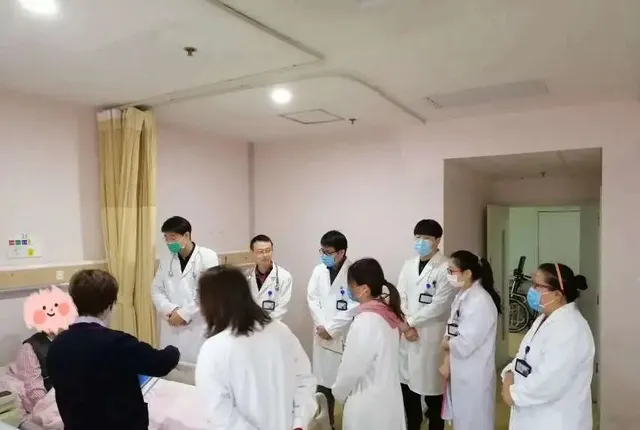
他很难接受自己最后变成这样,沉默的吃药,沉默的看着仪器滴滴响,癌症让他的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经常莫名其妙开始有脾气 。
人家要换尿布的时候他说自己还没有,然后闭着嘴不理人;
我姑姑们来问他想吃些什么?他说要吃东北菜,吃酸菜肉片;姑姑去烧了菜,他嫌难吃,又找了东北人来烧。
他也只吃了一口,继续保持沉默。
偶尔说几句话也是问我,病情有没有好一点?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没法欺骗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也不能直接说没救了,你马上要死了。
这个无限接近死亡的过程,把我的爸爸变成了另一个人。
其实原来刚进安宁病房前,他还不知道自己会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很真切的告诉我,如果真是到了癌症晚期,不要开刀手术,也不要化疗,那样太受罪。
但越往后你越能发现,真的没有人不怕死,我爸爸的求生欲望随着病情的严重程度,直线上升,他渴望被救,求生意愿非常迫切。
所以在他生命最后那段时间,大概是六月吧,他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说话夹枪带棒的。

谁来看他他就跟谁抱怨,是他的女儿没有给他治疗,没有带他去四处看病。
我当然不可能去跟他打辩论赛,纠正他说是你自己一开始不想治的,然后为自己辩驳,是我让你少受了很多罪。
说心里不舒服肯定是有的,感觉像被「背刺」的感觉。
但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了,他的埋怨是只是为自己不安恐惧的情绪找一个出口,要是说我几句能让他心里松快一点,那我也愿意。
最后我爸爸离开的时候是在7月,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折腾之后,我居然对他离开的那个瞬间并没有太大的悲伤。
当时从凌晨起,他就已经意识微弱了。
趁他还能听见我说话,我贴在他耳朵边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一直都表现的很了不起,放心吧。
然后我在走廊里打了个盹,大约三点,亲戚来叫醒我。
我进病房一看,他像几个小时之前一样安静的躺在床上,一边的仪器显示,他心电图变成了零。
然后我赶紧去联系殡仪馆,准备证件去开死亡证明,缴清医院的各项费用,一阵风一样忙了几天,最后筹办了一场挺风光的葬礼。
一直到亲戚们在葬礼上哭成一团,我在一边看,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是忘了什么事。
悼亡词念完,我终于反应过来,是我爸爸没了。
陪着亲人迎接死亡的过程很快,没有时间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显得太矫情。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为我爸爸做了我当下经济条件能做的一切,当年没为我妈妈做到的事情,我都想办法做了补偿。
吃喝用度,生理心理,都对我爸爸没有什么遗憾了。
所以我心里有不舍,但是没有愧疚。
不舍是因为我成了家里最后一个人,再怎样自由、怎样潇洒,户口本上也只剩了我自己的名字,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送走我爸爸之后,我也想过,我自己会不会老了也有这一天?会不会我的基因里也藏着一些莫名其妙会爆发的东西?
周围朋友尤其是亲戚,都在劝我赶紧结婚生一个孩子。
但我不想,这种带着包袱和压力生活的日子我过不起,有限的日子,那就无限的灿烂吧,我觉得再过几年可以准备好我的遗嘱。
至于那是要留在国内请护工还是飞国外安乐死,那都不是我现在要考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