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是詩詞的巔峰,但並非詩詞的全部。
自唐宋以降,文人騷客無不以吟詩作曲為必備技能,文學史的車輪滾過之處,便是詩歌生息之所,任何在文學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必有詩作傳之後世。
及至清朝,詩詞的黃金時代或已遠去,但這種文學體裁的魅力卻並未減損,仍是透視彼時文學大家思想感情的一處視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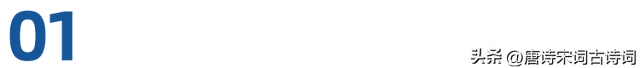
以詩觀人:康乾時代的兩位大文豪
且先看兩首詩。
其一:
身在甕盎中,仰看飛鳥度。南山北山雲,千株萬株樹。
但見山中人,不見山中路。樵者指以柯,捫蘿自茲去。
句曲上層霄,馬蹄無穩步。忽然聞犬吠,煙火數家聚。
挽轡眺來處。茫茫積翠霧。
其二:
秋山高不極,盤磴入煙霧。
仄徑莓苔滑,猿猱不敢步,杖策陟巉巖,披榛尋微路。
直上萬峰巔,振衣獨四顧。
秋風天半來,奮迅號林樹。俯見豺狼蹲,側聞虎豹怒。
立久心茫茫,悄然生鞏懼。置身豈不高,時有蹉跌慮。
徙倚將何依,淒切悲霜露。微言如可聞,冀與孫登遇。
第一首詩名為【青石關】,出自清康熙年間文學怪才蒲松齡之手;
第二首詩名為【自題秋山獨眺圖】,寫自清乾隆年間文壇巨人紀曉嵐筆下。
從詩來看,二人詩句皆偏向質樸平實,少有浮華造作之氣。無論是蒲松齡,還是紀曉嵐,此等才名之人,絕非矯揉造作之輩。
於是,讀他們的詩,不僅無粉飾雕琢之態,且比唐宋山水田園派更加平白,乍一看,形同白話,似難登大雅之堂。
其實不然,蒲、紀之人,文以寫心,詩以言情。 主打一個直來直去,有一說一。以紀昀為例,在詩歌創作中,奉行自然詩學觀的他主張用情為上、傳情為本,真實地描摹觀感,為此或可無視詩歌的形式技巧與藝術手法。
再來看兩首。
其一:
【夜渡】
清·蒲松齡
野色何茫茫,明河低欲墜。
水月鱗鱗光,馬踏月光碎。
其二:
【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
清·紀昀
濃似春雲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
斜陽流水推篷坐,翠色隨人欲上船。
唯有真誠,最動人心。將眼前之景寫入內心,樸實無華地描繪出來,清淡之中足見功力。自然如何,便如何,詩歌者,最本質真純之處,也在於此。
自古以來,文無第一。高手對決,各擅勝場。蒲松齡與紀曉嵐,是清朝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相同的是他們都成為了文學大家,不同的是他們一個身處廟堂之高,一個偏居江湖之遠。
如果說詩歌的天然質樸讓兩個天才的靈魂產生共鳴,那麽世道的波譎雲詭則讓他們彼此迥異。不同的人生軌跡便有不同的文學結晶,也自然帶來了盛名之下永無休止的比較與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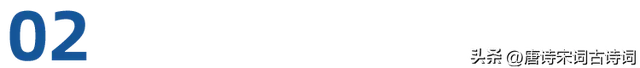
「一代文宗」卻敗給了「教書先生」
單就古代文人最為看重的科考仕途而言,紀曉嵐無疑是贏家,他不僅在24歲時就奪得鄉試頭名的解元,且最終高居大學士之位。
而蒲松齡,他雖少年成名,19歲便連奪縣、道、府3個第一,但此後屢試不第,直到71歲才得到一個貢生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號稱「大清第一才子」的紀曉嵐卻被老前輩蒲松齡隔空「打臉了」,而「打他臉」的竟還是自己的親兒子。
作為紀曉嵐的兒子,他不僅冷落了父親頗覺滿意的【閱微草堂筆記】,反而津津有味地捧讀紀氏一直「耿耿於懷」的【聊齋誌異】。

須知,紀曉嵐何人也?
他是造詣精宏的大儒,是桃李遍地的大師,是典籍工程的總纂官,是官方學術的代言人,是乾隆皇帝的文學侍從,是聲名遠播文壇領袖。
而蒲松齡,雖有文名,不過是始終未中鄉試、教了一輩子書的塾師罷了。
事實上,他們並非同時代的人。然而,有蒲松齡【聊齋誌異】珠玉在前,且風行天下、萬眾贊賞,紀曉嵐這個文學領袖不得不對此有所回應了。
【聊齋誌異】直接帶動了清朝文壇的一波誌怪小說熱潮,其中最有名者,就是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這是紀曉嵐「不服」蒲松齡作品的結果,也是其立誌以更加高明的路數寫作誌怪小說的成果。
最終,還是沒比過。

一方面,【聊齋誌異】不僅批判地繼承了六朝誌怪小說、唐傳奇的神話鬼怪素材,而且創造性地將其作為文學創作與表達的審美意象。
在他那裏,鬼狐精魅即人。
這使得他的作品及其人物在讀者那裏以具身的方式存在,這種文學表達效果與閱讀體驗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另一方面,蒲松齡的坎坷經歷使其始終居於民眾之間,他的文學也介於傳統雅文化與民間俗文化之間,他的故事來自民間,又可回到民間,他的故事敘述遠多於教化評議,其鄉俗俚曲多有流傳,能夠引起大眾的共鳴。
他本為民,自能為民請命。
蒲松齡不僅為平民教育總結師者經驗,也為底層民眾傳習農學藥典。他是鬼怪轉世的文壇聖手,能夠「寫鬼寫妖高人一等」;他是剛直磊落的民眾代表,由此「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紀昀呢?
紀曉嵐的富貴通達或許恰恰是他無法在此超越蒲松齡的原因。
一方面,他是學術型的一代文宗、文壇巨人,他的主要成就在於訓詁考據、編書著錄,文學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滲透了說理教化的色彩。
在他那裏,講理重於敘事。
這可能是紀曉嵐這類人的一種偏執,唯有講理、評析才能實作故事的深刻性表達,才能登上正統著述的「高雅」堂室而被載入籍冊。
另一方面,他是平步青雲的高官,是地主豪強的一份子,這使得他的作品無論如何追解蒲氏的浪漫主義歌頌與現實主義批判,都無法完全跳出為統治者勸誡世人、撫壓草民的套路。
他本為官,難改禦用之風。
在「文字獄」最為盛行的極致專制時代,無法張開嘴的他或許掩埋了太多內心的真實,或主動,或被動,或兼而有之,他在躋身上流的同時,也完成了自我的「精神閹割」。

正如他那皇皇【四庫全書】,修了多少,就毀了多少。
他被「閹割」的,恰恰是蒲松齡那悲憫眾生的一口「靈氣」。
這是他們的不同,這只是他們的不同。
但絕非背道而馳,不相往來。
紀曉嵐的廟堂,何嘗不是蒲松齡的夢想?蒲松齡的江湖,何嘗沒有紀曉嵐的向往?
否則,他不會考到七十歲;否則,他不會寫【草堂筆記】。
功名是執念,是永遠流動的血液。如今的我們看範進覺得可笑,其實彼時人人都想成為範進。
蒲家世代皆崇尚科考,蒲松齡等落第之人的一生,盡管表露了太多對仕途的失意決絕之情,卻始終無法掩蓋內心對於科名的不甘與艷羨。
不是不重要而不想得到,而是得不到而無法重要。
【九日望日懷張歷友】
清·蒲松齡
臨風惆悵一登台,台下黃花次第開。
名士由來能痛飲,世人元不解憐才。
蕉窗酒醒聞疏雨,石徑雲深長綠苔。
搖落寒山秋樹冷,啼烏猶帶月明來。
哪個兒郎不想「一日看盡長安花」,不想一腔襟抱得開展?可是才華扣響廟堂之門的路是如此的一生之遙。
這時,他又何嘗不是敗給了紀曉嵐呢!
他老了,他認了,他在心灰意冷中看到了自己的稀疏須發,一身骨頭。
【拙叟行】
清·蒲松齡
生無逢世才,一拙心所安。
我自有故步。無須羨邯鄲。
世好新奇矜聚鷸,我惟古鈍仍峨冠。
古道不應遂泯沒,自有知己與我同鹹酸。
何況世態原無定,安能俯仰隨人為悲歡!
君不見,衣服妍媸隨時眼,我欲學長世已短!
在這一副不能彎曲的脊梁之下,又怎不是對滿腔才華空許的一種悲憤呢!
當紀昀在清朝愈加嚴重的文化高壓中不斷喘息時,曾經被參流放的一幕幕在他腦海裏一次次閃過。烏魯木齊的風沙,讓他學會了在惡劣的環境中學會適應,學會為自己找尋一個出口。
文學天才都是有夢的,除非現實讓他難以成眠。
他閉上了百無禁忌的巧嘴,說了不少有人愛聽的大話。
【平定回部凱歌·滿耳秋風入短簫】
清·紀昀
滿耳秋風入短簫,黃榆葉落草蕭蕭。
西蕃已破無征戰,只向高原試射雕。
他在廟堂與江湖之間,同樣重復著蒲松齡的掙紮,那些熱血和野性的文學原始沖動,一次次地撞擊他內心的路標。也許他曾想過,在村口擺攤兒、收故事的江湖生活何其快意。
被「閹割」後的殘留使他在虛擬空間中找尋寄托。於是,他在教化世人與表達情感間維持著巧妙的平衡。或許,他的【閱微草堂筆記】比不過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但那也許是他在思想與藝術範圍內能做的最大限度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黑暗與人性的諷刺:
【刺汪太史】
清·紀昀
昔曾相府拜幹娘,今日幹爺又姓梁。
赫奕門楣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
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為郎。
百八念珠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
他看不慣的,他要想辦法說;他看不起的,他要表示不屑。
【聊齋誌異】對男女情感力量的歌頌,在他這裏也有回應:
【三生緣】
清·紀昀
三生誰更問前因,一念纏綿泣鬼神。
緣盡猶尋泉下路,魂歸宛見夢中人。
城烏啼夜傳幽怨,怨冢樹連認化身。
萬骨青山終瀝盡,只應鐵骨不成塵。
他扒開自己的官服朝帶,尋找那份他油然感佩的氣血,在燈下奮筆:
【過景城憶劉光伯】
清·紀昀
古宅今何在?遺書亦盡亡;
誰知馮道裏,曾似鄭公鄉。
三傳分堅壘,諸儒各瓣香;
多君真壯士,敢議杜當陽。
也許,以他的驚世才華,其文學藝術的高度遠不止於此。可是,他無法擺脫時代的強壓與階級的局限。
在那個時空,廟堂與江湖,是糾結的,也是交纏的。
在文學的聯通之路上,蒲松齡與紀曉嵐,是友非敵。
以前,我認為蒲松齡該更羨慕紀曉嵐;現在,我覺得紀曉嵐或許更羨慕蒲松齡。還可能,他們不會。
無論如何,他們都在各自的存活領域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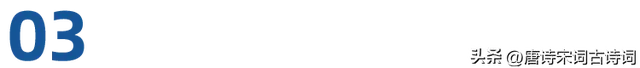
無謂成敗,做好自己
江湖與廟堂,可能本就是在撕扯中相互應和的一家。
無論彼此羨慕,還是互相憎惡,誰也無法取代對方,誰也無法成為他人。
紀曉嵐之所以是紀曉嵐,在於他的廟堂;蒲松齡之所以是蒲松齡,在於他的江湖。
這令我不得不深入地思考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學術與大眾的關系。
曾經我認為學術可以完全地傳遞給大眾,如今看來是如此的不現實。
正如紀曉嵐的著作無法像蒲松齡那樣得到最為廣泛的呼應一樣,學術性的作品註重說理,註重對於深刻本質的發掘與探討,而這與大眾的認知方式及閱讀習慣是較難契合的。
學術語言,或學術化語言是無法完全轉譯為大眾語言的,即便是科普性的作品,其與學理已然不同且受眾面有限。學術有學術的話語,通俗有通俗的表達,大眾有大眾的理解,這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當我們把學術話語說成白話來表達時,它所能達到的目的就是為普通人所更好地理解,但這種表達距離學術內涵已經失真或失準了,至少會打一個折扣。
也就是說,雖然學術表達也追求質樸簡潔,力避艱澀造作,但這並非強求學者或專家把學術說得像講故事、拉家常完全一樣,那樣或許並不是對民眾的親近,反而是一種缺失學術立場的逢迎。
民眾往往不解其深意,莫名被拖入對方的行銷陷阱之中了,被媒體營造的以學問為名的人設光芒迷得狂熱而躁動,動輒以「學術明星」、「配享太廟」待之。
事實上,真正做學問的是在自己的專業崗位內做專業的事情的,他們當然可以科普教化、啟蒙聽眾,但這既不是主業,也無法強求,學者渴求流行,學術追逐流量,徒增弊爾。
簡言之,真正做學術的人,可能大眾平時是感知不到的,他們或埋身於案頭田野,或奔走於實驗場所,其為大眾服務的方式就是做出專業的貢獻,而這並不一定直接作用於民眾的具體生活,最為著名的莫過「兩彈一星」等。
相反,那些頻頻在社交媒體上露面發言的人,走的是大眾路線。他們分為兩種,一種是做大眾生活化的知識科普,另一種則是投機主義的話術販賣,前者無可厚非,後者則需審慎對待。
比如,我們很多人對小說感興趣,也能讀能理解,但是對於文學理論著作則較少閱讀,而且難以讀懂;作家容易為人共知,而文學教授則較少出名。這是正常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理論著作、文學教授不重要、沒價值。
不可否認,不能排除現在某些無良專家大放厥詞、脫離實際、假公濟私,但我們不能走向反智的極端,而應對學界有個清醒的認知,那就是他們做的事情要從專業角度而非個人或大眾的主觀好惡上來理解。
誠然,學者做學術是具有專業性的,但這並不是說學者要脫離大眾,他們理應具備人文關懷與大眾情懷,盡力承當傳播知識與改造社會的責任,站在眾生的隊伍裏,同呼吸,共命運。
從這個意義上講,詩歌是大眾的精神食糧,是我們能夠共享的文化成果。對此,我們可以依托各種媒體平台廣泛交流、各自品鑒。

第二,教育與自我的關系。
李鎮西說過「 教育,在其本質與理想意義上,就是解放自我,實作自我的不斷超越。 」
而現在經歷的很多教育,則是他者化的、外在化的、功利化的。
成為什麽人,這是教育的根本問題,是進行生涯選擇的重要問題。
居於廟堂的紀曉嵐與處於江湖的蒲松齡,各有各的風采,各有各的成就。而要做的,就是讓自己積累、擁有能夠撐起自我的底氣與實力。
我們總是在別人的期望中存在,甚至不免幾番掙紮;我們總是在別人設定的路線裏行走,甚至不惜消滅誌趣;我們總是在別人宣揚的成功經裏苦修,甚至不會提出質疑。
不得不說現在的編制熱。我雖然無法否認這些崗位的「優勢」,但我卻深知這類崗位的特點。
蒲松齡可以做的,紀曉嵐也許不能做;【聊齋誌異】能寫的,【閱微草堂筆記】可能不行。
如果想要存留一個真實的自我,那麽在這個標準之下,有些選擇可能就會徹底改變。
現在的「雞娃」現象也是如此。
這個世界不是完全按照垂直序列設定的,因為人不是物,也不是數。豐滿而有機的人類是立體的存在,這意味著方向不止有一個,成功不止有一種。
請那些成為政界新星,成為商業巨子,成為文壇巨擘的培養目標與行銷口號都歇一歇吧,這樣的勵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
我們可以瘋狂地追逐第一名,但事實是第一名永遠只有一個。如此,絕大部份人永遠都是失敗者,這是一個零和的無底深淵與無終陷阱。
如果教育能夠使大多數平凡人、普通人體會到溫暖和驕傲,那麽這樣的教育似乎才稱得上人道。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那些世俗意義上的精英拔尖人才,往往不是教育的功勞,而那些被剩下的大多數,才應該是教育的物件和教育釋放魅力的地方。
須知,有些崗位或職務永遠是有限的,而成功也不是這些有限的東西能完全確證的。我們大可不必消極或釋然地說「接受孩子的平庸」,這並不是接受,也不是平庸,而是客觀事實,自然而然。
如其所是地存在,自然自我地存在。
你可以成為什麽,你就是什麽;你想要成為什麽,你就追求什麽。
按照世俗設定的功利主義評價體系,我們可能窮盡一生都是陪跑者、犧牲品,這說明我們在為一個抽離的、抽象的自我而活,還有什麽比這個更悲催的嗎?
如蒲松齡與紀曉嵐,任何人都要在無數個兩難中平衡,由此完成自己的一生:與自我對話,與內心相處。
-作者-
風子,用文字記心,用心緒成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