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華書局出版柳立言先生所著【宋代的宗教、身分與司法】。全書分為上、下兩編,分別以僧人與妾侍為主題,嘗試分析宗教與身分對司法的影響。上編投擲三個問題,即僧人為何犯罪、僧人如何犯罪、司法如何審判,先以奸罪(色戒)為例,分別從佛教(內)與世俗(外)兩個層面加以回答,再依此路徑拓展至其他犯罪,如犯罪之所以發生,既有教團自身的問題,也有俗眾的外力推動,既存在僧人特有的犯罪手法,也有僧、俗共享的犯罪方式,至於依法審判、逾法審判抑或是無法可據時的自由裁量,士大夫既可能出於政策、治安、財政的世俗考量,也可能受自身信佛或排佛的信念影響。下編則從禮(婚娶與喪服)、法(株連與奸罪)兩個角度判明妾與婢全然不同的法律地位,運用縝密的邏輯分析史料所見的「妾」與「婢」,推定這些概念究竟是實指還泛稱,由此質疑既往學界混淆妾、婢所得出的相關結論,再立足司法案例,輔以法令政策,剖析宋代妾侍所享財產權(對己產、亡夫遺產的權利)與身分權(立嗣權、教令權)的變化。
柳先生在自序中言:「僧人犯罪是佛教史稀見的一章……審判僧人也是司法史少見的一章」,「身分等級制及相關的禮與法,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基礎,從前者的變動來觀察後者的變動,是較能從大見大的」。正因如此,即使出版已逾十年,本書依然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青睞,認為它契合「長城磚」叢書的選題方向「關註人的命運、日常生活、司空見慣的概念、潛意識的觀念,以及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焦慮的問題」,擬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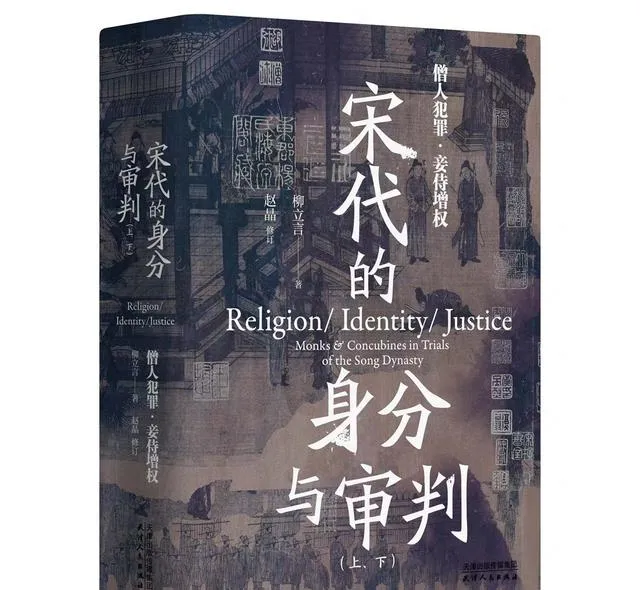
【宋代的身分與審判】(修訂版),柳立言著,趙晶修訂,天津人民出版社

柳先生榮休時將自存本寄贈給筆者
2022年1月21日,柳先生來函囑我全權負責校正、修訂本書的所有事宜。這是訓練學生的良機,我求之不得,於是一口答應。當年5月30日,我給學生雲夢沙(本科畢業於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現為中國政法大學專門史碩士生)寫信如下:
近日接到史語所柳立言先生來信,天津人民出版社擬重版他的著作【宋代的宗教、身分與司法】一書,希望我能代覓一位學生幫助修訂,不知你是否願意參與?我想了一想,修訂的工作包括如下內容:
第一,柳先生目前存有繁體字word版(包括對中華書局一校樣的修訂意見),因此第一步工作就是將繁體轉化為簡體。如你所知,繁簡轉化時會出現各種問題,除了「乾道」變成「幹道」之類外,切勿勾選「轉換常用詞匯」,否則容易出現更大的錯誤。因此,在繁簡轉化之後,理應對照中華書局出版的定本,逐一對讀,一是校正轉化之誤;二是補入出版社編輯在二校以後所作的修改。當然,如果你認為這種修改並無必要,請標紅,以便我來做最終的判斷。
第二,第一步工作是提供出一份精當的簡體word本,這是形式上的工作,雖然需要花費精力,但基本是體力勞動。第二步工作涉及內容,也考驗你的學力,甚至可以從中尋找學位論文的選題。我的大致想法是:
1.以其書名、集結成書之前的單篇論文名,在中國知網等數據庫中做「全文檢索」,檢出參照過此書或此文的論文,檢視商榷意見或研究進展,認為可取者,可出「補註」以「*」打頭,與原本的註腳進行區別,內容則是評斷是非,提醒讀者留意。
2.征諸網絡評論,部份研究者認為,柳先生此書前半部份的最大問題是多據聖嚴法師的作品立論。那麽我們或特許以參讀宋代佛教史乃至於通代佛教理論的一些經典作品,看看聖嚴法師的判斷有無問題,尤其是柳先生賴以為據的觀點是否並非通說?如果這種背景知識被瓦解,柳先生的看法是否需要修正、如何修正?是否修正,也應出「補註」予以說明;至於「如何修正」,或特許由你自行撰寫文章,導向更為妥帖的結論。當然,這是舉例說明,在你覆按柳先生之著時,隨時隨地都應留意他的論證,判斷他立論的基礎是否有其他不同觀點,若前提存疑,是否會影響他的結論?當然,若透過你的研判,聖嚴法師的看法與其他學者的論點並無二致,僅引聖嚴之說,並不影響柳先生的結論;哪怕聖嚴之見與他人有別,但立足其說,也不影響最後的結論,那麽我們也可以藉此修訂回應那些研究者的質疑。
3.這樣的商榷與回顧,不應限於漢語學界,也可按圖索驥,看看域外的研究成果,能否對柳先生的觀點加以回應。甚至於你也是一位獨立研究者,如果你對柳先生的看法有不同意見,也可利用「補註」提出商榷。如果你覺得這種商榷可積累成篇,不妨獨立撰寫成一篇書評,或可先單獨發表,再作為附錄,加在書後。
補註可用修訂模式,以便我覆核。待正式出版時,書中會明確標記你的貢獻,並給予相應的報酬。此書的篇幅不大,未知你意下如何?
夢沙十分爽快地接下了這一校訂任務,並分三次發來了校訂稿。在補註部份,她盡可能地為聖嚴法師的說法找到內典的依據,也檢索出許多本書出版以後的成果。我在初讀之後做了大量刪節,考慮如下:
第一,既是證實聖嚴法師之說,自然不影響柳先生的立論,留之無益。從「法庭辯論」的角度上說,只有在反方亮出證據後,我們才可以圍繞其「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進行質證,目前無需盲目增加同質性證據;
第二,夢沙采用了常見的學術史綜述的寫法,面面俱到地臚列各種新發表的成果,而不加辨別。其實,沒有任何學術推進、甚至可謂「學術倒退」的新成果,實在沒有必要浪費字紙、予以回顧。
柳先生冒著眼疾再度惡化的風險(事實上最終又導致左眼外出血),審讀全稿,對夢沙的補註、我的答復作出了許多回應。以下列舉未被我納入書中的兩點:
第一,「撰文之時,我有點擔心某些讀者會模糊焦點,把我對佛教的批評視為‘宗教戰爭(基督教vs佛教)’,故的確有意多一些參照佛教學人來助陣。可惜,的確是幹一行、愛一行吧,正如研究新儒學的學人很少批評新儒學,研究佛教的學人也很少批評佛教,有時也不算很高深,但我還是可引則引,避免孤軍作戰。……聯軍之中,自以聖嚴的知名度和可信度最高,他不但是學人(立正大學,博士論文為明代佛教),又是高僧,他對自家人的批評應能代表高度的公平、公正和善意。他的著作也多,可以讓我在多處參照來助陣,也表示他沒有改變他的批評。所以,說我借重他來支持我對佛教的批評,是對的;說我的批評來自他,只對了百分之一(腹語:錯了百分之九十九),他畢竟是明代而非宋代佛教的專家。要測試其實不難,把我參照聖嚴的地方全部刪去出處,看看結果如何?是否不參照亦可以?」(2022年6月4日回信)
第二,「不妨參照,因為研究佛教與立法的著作實在不多,X氏亦可算一家之言了」、「不妨參照Y文,以見拙著出版後的研究情況」、「列出亦無妨,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史朋】20,但願譯者是能手。今日的英文書價奇昂,加上動輒25美元的運費,我都只看中譯本」、「既是一說,可加入」……(2022年11月4日、6日,2023年7月25日批註校訂本,X、Y皆是我做的替換修改)。
根據柳先生的第二點意見,我又恢復了部份研究論著臚列的條目。而上述的校訂流程,最終將以「雲註」(雲夢沙補註)、「趙案」(趙晶案語)、「柳答」(柳立言回答)的方式在新版註腳中呈現。除此之外,我在修訂過程中始終著力揣摩柳先生的行文運思,反復拷問自己:面對同一命題,自己會如何拆解、想法是否與柳先生有別、能否對本書有所補充?由此也形成了一些「續寫」此書的想法。

2012年11月28日,柳立言先生與趙晶在「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
柳先生在自序中曾引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條文表述,如「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提出一個「大哉問」:所謂性別、宗教、種族和出身等因素與法律執行的關系為何?隨後,他將此問拆解為刑、民兩個部份,分別以僧人的犯罪與妾侍的權利為例,輔以「歷史六問」(when、where、who、what、why、how),嘗試呈現宋代身分(原題中的「宗教」可化約入身分)與司法互動的一個側面。
把大問題拆解為中、小問題,以及「歷史六問」等無疑是一種「史有定法」,本書的示範自然也提供了後學可資效法的門徑。然而,柳先生在自序中也曾坦言:「個人時常感到困難的,不是提出大問題,而是不知道應把這個大問題分解成哪些小問題(how to break a big question down into small component questions),以便逐一回答,最後才能比較完滿地解決這個大問題。」這就屬於「史無定法」的領域了。如果是我,又該如何拆解?
第一是身分。身分的意義只有運用「比較」的方法才能彰顯,即該群體相較於其他群體而言,擁有的權利是更多還是更少、承擔的義務是更少還是更多,即處於更加有利還是不利的法律地位。以「僧人」為例,其宗教身分的意義須與哪些人進行比較才能獲得彰顯?首先是非宗教人士,如官吏與平民;其次是其他宗教人士,如道士與巫覡;再次是同一宗教群體內部的不同子群體,如著眼於階層,就有僧眾與僧官之別,如著眼於性別,則有僧與尼之分。以妾侍為例,首先是以性別為標準,比照的物件自然是夫;其次是同一性別之下的其他群體,如妻與婢。
第二是司法。司法又可細分為兩個部份,一是對實體法的適用(如刑事領域的定罪量刑、民事領域的定分止爭,即柳先生在結論中所謂的「判」),二是對程式法的適用(如訴訟資格的限定、口供證言的采信等,類似於柳先生所謂的「審」)。二者皆須被追問:是依法而行,還是違法而行,或是無法可依?若是依法而行,因身分產生的區別對待,則由立法所致;若是違法而行,則須判別立法與司法分別受到身分何種影響;若是無法可依,則是司法對身分問題的獨特回應。
以此檢視本書,柳先生在妾侍部份對「身分」關照甚切,尤其是妻、妾、婢之辨,完全貫徹了比較的方法;在「司法」上則重視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落實,尤其展現官員在「無法可依」時如何自由裁量(如圍繞寡妾對亡夫遺產的承受權,又如針對寡妻的立嗣優先權和親母的教令權出現競合的情況)。至於程式法適用是否受到「身分」影響,限於史料,本書並未回答。如【宋刑統】卷二四【鬥訟律】「告周親以下」門規定:「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因妾為嫡妻所服為「齊衰」,所以妾告妻的訴訟權利受到限制,但若人身權利受到侵害,則允許妾舉告。宋代自然不乏妾被妻毆虐致死的例項,同樣也有妾受寵而掌家政、惡待嫡妻的例項,此類案件一旦進入司法程式,官員該如何查明事實、采信證供?尤其是妻、妾各執一詞,形成「事有疑似,處斷難明」的僵局,即「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無證見;或傍有聞證,事非疑似之類」(【宋刑統】卷三〇【斷獄律】「疑獄」門),此時庶子出身的官員與嫡子出身的官員會否因「身分」有別而作出不同判斷?帶著類似疑問研讀史料,雖然未必能找到最終答案,但有時也會別有所獲。如【夷堅誌·支甲】卷五「劉氏二妾」載:
從事郎劉恕,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又娶於高氏,攜媵婢四人。淳熙初為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年一十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雄,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己寵必衰,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誌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外治事或對客,輒啼嘑奔叫。恕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無言,而於屏處訴雲為母所箠,恕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恕驚問,見針,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規兒性命。恕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鞫,不得情。郡守念閨門茫昧,難以置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罹決絕,外間皆明知其誣,恕獨弗之悟,旋用他事罷去,還鄉而卒。
故事的敘事者自然有其立場與「後見之明」,如「妾性悍狡」、「高誌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之類的主觀評價(若出現在審訊時,這就是「品格證據」),自然決定了情節發展的走向,以及輿論評價「外間皆明知其誣」。若立足事實邏輯推想,作為生母的妾確有誣陷嫡母的動機,作為嫡母的高氏也不排除謀害庶子的想法。犯罪的直接嫌疑人是隨高氏陪嫁來的媵婢,兇器是「針」,二妾「共證」媵婢是受高氏之命行事,且劉恕「以為然」,將四婢俱送官訊鞫似乎也有「項莊舞劍」之意,因為按照「造意為首」的原則,首犯或是高氏,尤其是在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新法頒布之後,嫡、繼、慈、養母殺子,皆同凡人論,嫡母身分所具有的法律特權受到限制。作為官員,在查明此案事即時至少會遭遇以下難題:「針」並非特殊之物,無法斷定必是媵婢所有;即使能確認是媵婢所有,也難以斷定是她將針貫於菜莖中;即使能確認是媵婢故意為之,也難以斷定是高氏指使。因此,郡守最終只能以「閨門茫昧」為借口,不了了之,但至少表明他沒有因妻、妾身分之別,乃至於風傳的「品格證據」而偏聽偏信。
以類似的思路反觀本書的僧罪部份,如相較於非宗教人士,讀者可據此了解僧人在行為規制層面被課責的義務更多,觸犯同樣罪名後所受處罰更重,在犯罪上可采用的手段與伎倆亦夥;又如與巫覡的異同,讀者也不妨將本書與柳先生的【人鬼之間:宋代的巫術審判】(中西書局2020年)對讀,應能獲得部份答案;至於僧人與其他群體的比較,本書著墨不多,如討論立法禁制時相關條文通常「僧道」並舉,又如論及僧人利用職權犯罪時也兼顧尼姑等,但「同」大於「異」,難以析出「身分」因素的影響。就「司法」而言,本書表明官員在定罪量刑上存在「依法」、「逾法」的不同處置,或許與他們在主觀上對佛教的認知、態度有一定關聯;而且在司法程式的適用上,理學官員還對僧人提告抱有歧視等。但因本書同樣未暇顧及與其他群體的比較,自然也會令讀者產生一些疑問,如北宋中葉以後宋廷的抑佛,尤其是徽宗的排佛崇道,有無在司法領域影響僧人與道士的法律地位?當然,因史料所限,此類問題未必會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此外,柳先生在上編部份兩次提及南宋晚期包恢在隆興府秘密處死淫僧案,現概述案情如下:寡母告子不孝,包恢見其書狀而生疑,後查實是其母與僧人通奸,嫌惡兒子勸諫,由僧人執筆書狀,試圖坐罪其子。包恢並未追究寡母與僧人通奸及誣告之事,而是責令其子侍養寡母、寸步不離。後來其母托言丈夫忌日,入寺做法事,讓僧人藏於籠中帶回,包恢勘破其情,命人將籠置於公庫中,將僧人活活餓死,旬余後投籠入江(【宋史】卷四二一【包恢傳】)。這不由令人想起【朝野僉載】卷五所載之事: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雲「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寡母與人通奸而以不孝罪告子的情節,唐、宋均同,只不過唐代的奸夫是道士,宋代則是僧人,【折獄龜鑒】卷五「懲惡門·李傑覘婦」所附曾孝序斷案、「察奸門·李傑覘婦」所附葛源斷案,都是發生在北宋的相似案例,奸夫分別為寡婦的鄰人和為寡婦代書狀紙者,皆為普通人。這說明「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此類犯罪手段縱橫唐宋兩代,為宗教與非宗教人士所慣用,可謂人性的普遍問題,難以析出「身分」的影響。

2019年8月14日,柳先生在交代給我寄送相關書物的信中言:「彌勒佛之謎,與李力當年在史語所講演之海報合觀便能解開。」2019年11月下旬,筆者返京後檢點受贈諸物,內有一尊銅制彌勒佛。或因郵寄時有所顛簸,佛像與底座分離,方知奧妙在佛像底部的春宮畫,但窮盡各種手段,也未找到李力教授當年的演講海報。柳先生於12月31日來信言:「海報是一張日本浮世繪,描畫布袋和尚掀起一位睡夢中的藝妓的裙子偷窺春色,故謎底是‘掀’起木板底座,可惜被他力掀了,真是無趣到了極點。」實則早在2018年6月12日,他就曾來信言:「撰寫僧人犯罪時,還搜集了一些宗教人仕(大多是僧尼)犯色戒的浮世繪和置物。有一個銅制和尚,法相尚算莊嚴,掀開底部,一男一女在交合,不知是日本特色還是中日都有?多年前李力在史語所講演僧人犯罪,我挑了一張浮世繪作為海報,是布袋和尚在掀一位女仕的下擺。日西兩地研究春畫者極多極佳,其中或有專門針對宗教人仕的,如西方版畫之諷刺牧師,但不知程度如何?【色戒】刊出後,被台灣和大陸各收一次,可惜都沒有插圖。似乎道教人仕犯奸的畫面較少見,不知明清的版畫有多少?又不知有無巫覡犯奸的?」
從司法上看,唐代官員公開杖殺奸夫淫婦,宋代官員則悄悄計殺奸夫、放過淫婦。征諸法律,【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凡奸」條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同卷「監主於監守內奸」條規定:「諸監臨主守,於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喪,若道士、女官奸者,各又加一等」。據此,寡母犯奸罪,徒二年;道士加二等,徒三年。【唐律疏議】卷二三【鬥訟】「誣告」條規定:「諸誣告人者,各反坐」;卷二四【鬥訟】「告緦麻以上卑幼」條規定:「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論」;卷五【名例】「共犯罪造意為首」條規定:「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同卷「共犯罪本罪別」條規定:「諸共犯罪而本罪別者,雖相因為首從,其罪各依本律首從論」;至於「不孝」涵蓋九款罪行,僅「告言祖父母父母」、「詈祖父母、父母」處絞刑。據此,寡母誣告兒子不孝,毋需論罪;若道士為從犯,以誣告死罪而反坐、減一等論處,刑罰為流三千裏;若道士造意為首,則處絞刑。【舊唐書】卷一〇〇【李傑傳】載「開元初,(李傑)為河南尹」,可知案件發生的時間。【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載「若大理寺及諸州斷流已上若除、免、官當者,皆連寫案狀申省案覆,理盡申奏」,若李傑按照法定流程處死道士,需要先申省案覆,最後由皇帝決斷。【舊唐書·李傑傳】後文還詳述了長孫昕等毆打李傑案:
(李傑)尋代宋璟為禦史大夫。時皇後妹婿尚衣奉禦長孫昕與其妹婿楊仙玉因於裏巷遇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為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下敕曰:「夫為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疏。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誌從深諫,情亦惜法,宜寬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即宜決殺,以謝百僚。
據【舊唐書】卷八【玄宗紀】載,此案發生在「開元四年春正月癸未」。根據【獄官令】的規定,「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斷屠月日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所謂「斷屠月」是指正月、五月、九月,因此為長孫昕等求情的馬懷素才會說「陽和之月,不可行刑」,而玄宗最終的變通方案是以「杖殺」(枯木之斃)代替斬刑。論者曾以開元二年(714)三月廓州刺史左感意因坐贓而被杖殺為例,說明從彼時起杖殺已非私刑、濫刑,而開玄宗朝杖殺法定化之先河(金珍:【唐後期以杖刑為中心刑罰體系的形成】,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頁46-49)。因此,李傑杖殺奸夫淫婦案或許亦應置於這一脈絡下理解。若是如此,那麽令人好奇的是:唐廷當時為何要逾法處死道士與寡婦呢?【新唐書·李傑傳】雖收入此案,但未言杖殺寡婦,【折獄龜鑒】襲之(稱「舊出唐書本傳」)。這或許表明宋代作者對寡婦遭刑的不理解。無論如何,這些討論是否可以關照唐宋之際的宗教、身分與司法關系?
【宋刑統】繼承了上引唐代【律疏】的相關規定,若目前的史料難以反映立法修改的情況,一般認為相關條文皆通行於兩宋,如【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二【懲惡門·奸穢】「因奸射射」載「在法,諸犯奸,徒二年」,因該案針對的是有夫之婦,「徒二年」恰是對【宋刑統】奸罪條文的適用。至於包恢之所以不追究奸罪,恐怕亦非單純顧念孝子之情。如【宋刑統】卷二四【鬥訟律】「部內犯罪不糾舉」門規定「諸監臨主司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三等」,卷二九【斷獄律】「不合拷訊者取眾證為定」門規定「若因其告狀,或應掩捕搜檢,因而檢得別罪者,亦得推之。其監臨主司於所部告狀之外,知有別罪者,即須舉牒,別更糾論,不得因前告狀而輒推鞫」。據此,包恢所接訴狀雖是告子不孝,但其查得寡母奸罪,可「舉牒」別論。但南宋時對奸罪另有特殊規定「諸奸犯奸,從夫捕」(【慶元條法事類】卷八〇【雜門·諸色犯奸】),如胡石璧在查知呂道士可能犯奸時,明確表示既然丈夫「未有詞,則官司不必自為多事」(【清明集】卷一二【懲惡門·奸穢】「道士奸從夫捕」);又如範應鈴認為「若事之曖昧,奸不因夫告而坐罪……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則今之婦人,其不免於射者過半矣」(【清明集】卷一二【懲惡門·奸穢】「因奸射射」)。目前雖不知法律上如何規定針對無夫之在室女與喪夫之寡婦的奸罪,但在司法實踐中,除非捉奸在床,否則奸罪證成的難度極高,所能采用的手段只有刑訊逼供而已,「如必欲究竟虛實,則捶楚之下,一懦弱婦人豈能如一強男子之足以對獄吏哉,終於誣服而已矣」(【清明集】卷一〇【人倫門·夫婦】「既有曖昧之訟合勒聽離」),所以許多官員的態度是「不欲以疑似之跡,而遽加罪於人」(【清明集】卷一〇【人倫門·夫婦】「女嫁已久而欲離親」)。因此,包恢對此案的處理自然有法律技術層面的考量。至於最後淫僧之死,已非「司法」所致,與唐代淫道被「杖殺」的性質判然有別。
上述漫無邊際的「瞎想」,只想說明一點:若欲更加完滿地回答柳先生的「大哉問」,需要我們搜集更多的例證,拆解更多的中、小問題,增列更多的比較項。典型已在,我輩當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