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法學家韓幽桐不幸患了肺癌。當癌細胞擴散到腦部以後,她已不可能對病床前的老伴說什麽了。

張友漁(二排中)
1985年8月13日傍晚,她輕輕地閉上雙眼,無聲地辭別了親人和她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
她的老伴、著名法學家張友漁,沈重地站立在她身邊。
相親相愛的五十七個年頭,多少次幸福的相聚,多少次匆忙地分離,一切都成為過去。眼前,只是永遠的分離。
底事愁思為慕韓,夜來開眼到更殘。
春風疑不渡東海,島國櫻花帶淚看。
這是三十一歲的張友漁旅居日本時,寫給二十一歲的韓幽桐的。那時他們相識三年,已經相互熱戀了。

張友漁
他們是在嚴酷的政治鬥爭中熾熱地相愛起來的。
1927年12月,北京市委被破壞,當時擔任市委秘書長的張友漁不幸被捕。
彼時,韓幽桐有事去找市委副書記馬駿,結果與馬駿一同被捕。
在敵人審訊時,韓幽桐看到了張友漁。以前她在馬駿的住處見過這位青年,似乎沒有什麽可以引起她註意的地方。
這次,在敵人的法庭上,他,還是那身布衣,還是那副面龐,但是那深沈而鎮定的學者風度,那堅定而簡短有力的語言,在張牙舞爪的醜惡敵人面前,如鶴立雞群。

她突然發現了這位青年人的光彩。
不多久後,他們相繼從監獄裏被營救出來,繼續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張友漁到了天津,打進了閻錫山派系勢力控制的天津市政府當新聞科長,韓幽桐回到北平大學法學院上學。
北平、天津的黨員秘密地共同辦了一個進步刊物【人言周刊】,在北平編輯,到天津的租界出版。他倆都參加了這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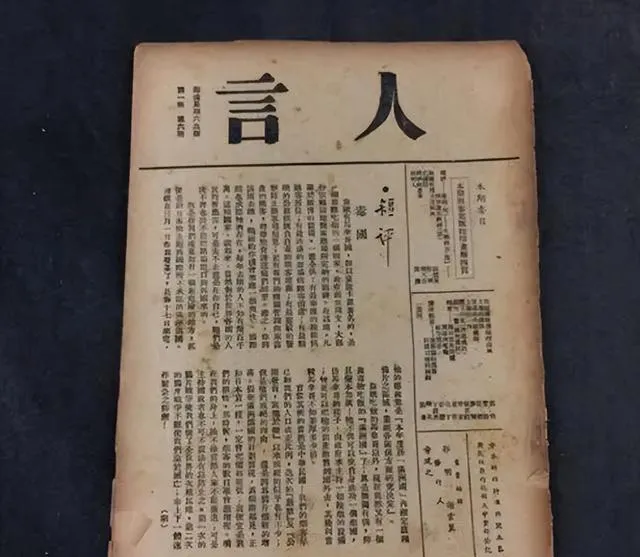
韓幽桐,這位漂亮而又活躍的十九歲女大學生,道求她的男同學有一群,已經二十九歲的張友漁默默地工作著。
他似乎並不是韓幽桐那些追求者的對手,也確實沒有想當他們的對手。
不過,同生共死的鬥爭,勝過任何追求者的甜言蜜語。韓幽桐往天津給他寫了一封信。
如果真有所謂情網的話,一向只知埋頭做學問、做工作,並不會和女性打交道的張友漁,在書信往來中,可真的深深地「掉進去了」。
緊張而殘酷的地下鬥爭,使這對青年沒有機會、沒有時間在一起慢慢傾訴他們的愛情。
一封書信,便是極大的祝福。會面的幸福幾乎被他們看成是奢望。
秘密黨員重任在身,不能隨意跑動。有時連書信也會突然中斷。

1930年冬,蔣介石聯合張學良打敗了馮玉祥、閻錫山,天津市的政權由閻錫山手中落到了張學良手中。
張友漁有可能被捕,組織決定讓他迅速離開天津去日本。他不能去北平,也來不及寫信向韓幽桐告別,匆匆登船東渡。
在船上,在東京,他不斷寫詩抒發對愛人的思念,有時還把詩投寄報社登出來。
在以後的地下鬥爭的那些歲月,他倆的深情厚愛,以生死與共的艱苦復雜鬥爭,譜寫著詩的續篇。他們或沖向鬥爭的第一線,或巧妙地戰鬥在敵人身邊,幾臨險境,幾次虎口余生,匆匆地相會,頻繁地分離。
他們難得有一次相聚的機會。

「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愛國的氣氛大為高漲,張友漁奉命從日本回到北平工作,公開身份是【世界日報】主筆和燕京大學、民國大學教授。
韓幽桐在北平大學法學院還沒畢業。
這次,他倆相聚北平,都珍惜無比。人家都說「談」戀愛,大概戀愛在交談中能保持最佳發展狀態。
這對戀人卻例外,各忙各的,化得把「談」戀愛的時間都擠掉了。

張友漁每天夜裏一兩點鐘以前,必須在世界日報社寫社論,早上起來又上燕京大學或民國大學講課,下午進行黨的活動或在左翼文化人士中活動,沒有一刻的空閑。
韓幽桐這時是北平學生抗日聯合會領導成員,她和學生抗日聯合會其他領導人,組織北平大專院校及中學的學生去南京示威,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

隆冬時節,她和同學們在北平前門東火車站進行了三天三夜的臥軌鬥爭,迫使北平當局為他們派出列車去南京。
在這震動全北平城的臥軌鬥爭期間,張友漁一次也沒有去看韓幽桐。
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權利輕舉妄動暴露自己的身份,韓幽桐當然也沒有和他聯系。

激烈的鬥爭占去了她全部的時間,她在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傳南下示威的目的,和同學們砸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中央日報社。
回到北平,她就被國民黨逮捕入獄了。
卻沒曾想,不久後,他們居然有了一次共同旅行的機會。
這是1932年夏。張友漁不能再當【世界日報】主筆,因為張學良懷疑他是共產黨。

【世界日報】負責人成舍我請他離開北平,去日本東京當特派記者。
黨組織同意他去,作些日本形勢的調查。
韓幽桐從獄中被保釋出來後,又回到北平大學法學院。
這時,她大學畢業,準備去日本留學。兩人結伴而行。
張友漁在日本搞調查研究、寫文章;韓幽桐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第一個女研究生。每天的傍晚,是他倆的共同時間。

他們的嗜好,是到舊書攤買書。
東京大大小小的書攤前,經常出現這對熱戀中的中國青年的身影。
第二年,他倆結了婚,婚後不久卻又分別了。
張友漁因工作需要回到北平;韓幽桐獨自留在東京。

「七·七」事變以後,張友漁曾任中國共產黨豫魯聯絡局書記。
他去鄭州處理問題時,在西北聯大任教授的韓幽桐抽空去看他,正趕上敵機狂轟濫炸,房子搖晃得厲害,電扇掉下來砸到張友漁頭上,多虧韓幽桐給他拉了一條棉被頂在頭上。
這對幸存者走出屋子,周圍已是屍體橫臥的一片瓦礫,韓幽桐很不放心地回到西北聯大。
不久,幾度反蔣的西北軍系的石友三,要求中國共產黨長江局派一個左派人士到他的部隊擔任政治隊長。

張友漁奉命以左派教授的身份到了敵後石友三部隊。韓幽桐知道,他去的是一個比飛機轟炸更險惡的環境。
她想一同前往,但工作需要她留在西北聯大,發展那裏的左派力量。多疑的石三友,有兩次差點殺握張友漁。韓幽桐所在的西北聯大也不平靜。
左派力量發展很快,陳立夫坐不住了,把手伸到這裏,解聘了八位進步教授,韓幽桐是其中之一。
他倆天各一方,都處在鬥爭的前沿,彼此深知對方為黨獻身的精神,心是相通的。
兩人生活在一起的時候,也難得安定的家庭生活。

1939年到1941年的大概兩年間,他倆都在重慶。
張友漁又進入一個危險崗位——到孔祥熙掌握的【時事新報】任總主筆,利用合法手段,盡量宣傳國共合作,團結抗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突然發生。
他還沒有接到如何應變的通知,張友漁繼續按時去時事新報社上夜班。
1月17日,國民黨中宣部發了一條顛倒黑百的訊息:「新四軍叛國」。
當局命令各報必須登載,還要發表討伐新四軍的社論。

【時事新報】的總經理張萬裏把國民黨中宣部的「指示」給張友漁看,張友漁不知道他是什麽態度,冒著危險明確告訴他:「這文章我不能寫。叛國的不是共產黨,應誅討的不是共產黨。」
張萬裏意味深長地對張友漁說:「現在,我的處境很困難,你的處境很危險,最好早有安排。」
張友漁明白了他的意思,兩人同時伸出手來,用力緊握,說了聲「再見」。
見到匆匆提前趕回家的丈夫,用不著語言解釋,韓幽桐配合默契,兩人迅速轉移隱蔽起來。

黨組織派他倆一同去了香港。珍珠港事件發生,香港淪陷,他們又奉命隱蔽起來。
隱蔽的住處被炮彈打壞,幸虧兩人都沒在屋裏。
他們又隱蔽到另一個住處。不料,一天半夜,闖進來幾個武裝的偽軍,用刺刀頂住了張友漁的胸膛。
張友漁用日語訓斥他們:「幹什麽!」
偽軍一怔,再看韓幽桐,一身西式衣裙,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

他們懵了,以為走錯了門,闖進了日本人家,嚇得轉身跑走。
而張友漁和韓幽桐也不敢再久留,立刻又搬了家。
完成地下黨交給的疏散、安排一些同誌的任務後,他倆也撤離香港。
深夜,他們乘著地下黨組織準備的小船,到了九龍的懸崖絕壁下,崖上接應的同誌垂下長長的繩子,讓他倆抓住繩子往上登。

腳下的小船在海上搖晃著。黑夜中看不清絕壁有多高,萬一掉下來,韓幽桐會遊泳,張友漁可一點也不會。
他倆咬緊牙,先後都拽著繩子登上去了。
在岸上,他倆脫下西裝,換上棉袍,化裝成商人夫婦,在東江遊擊隊護送下,回到了桂林。
日本投降後,許多在抗日戰爭中分散的家庭得到了團聚。
他倆卻開始了一次長時間地分離。
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團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張友漁擔任代表團的顧問,幫助研究民主憲政問題。

他的黨員身份完全公開了。韓幽桐原在重慶搞民主憲政運動,公開職業是美國新聞處日文轉譯,張友漁的黨員身份一公開,她無法再在美國新聞處呆下去。
這時期東北解放,需要大批幹部,韓幽桐奉命去東北作文教方面的工作。
張友漁愉快地支持她遠赴千裏之外,還幫助她戲劇性地帶走了高崇民同誌。

高崇民同誌要離開重慶去上海,交通工具都被國民黨壟斷,正苦於無法動身。
韓幽桐以美國新聞處工作人員的身份可乘美國的運輸船去上海,張友漁就讓高崇民冒充韓幽桐的丈夫上了船。

一直到全國解放後,韓幽桐才離開東北,回到了天津,並出任天津市教育局長,1950年時,韓幽桐又調回北京,先後任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華北法院副院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副庭長。
而張友漁在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北京市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副市長。
夫妻倆終於在北京團聚,不過這個團聚也是短暫的,不久,韓幽桐又調到寧夏,一直到1963年又調回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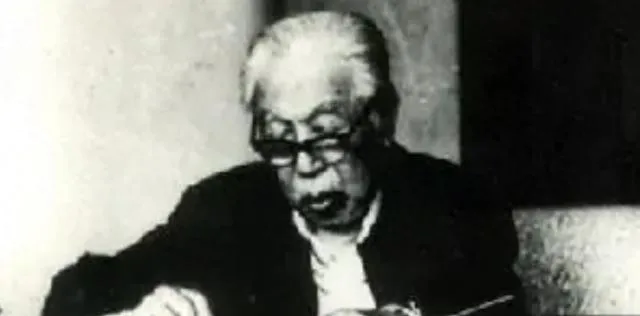
這期間,學法學的倆人發揮專長,為新中國的憲法法律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85年韓幽桐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7年後,1992年2月26日,張友漁在北京逝世,終年94歲。
倆人自此走完了伉儷情深、是夫妻也是戰友,為理想和熱愛的法律事業奮鬥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