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年:1947
現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研究方向:現代西方哲學
主要著作:【人生天地間】【沈默的視野】【話語的真相】【經驗之為經驗】【哲學的基本假設與理想國】【當代哲學問題九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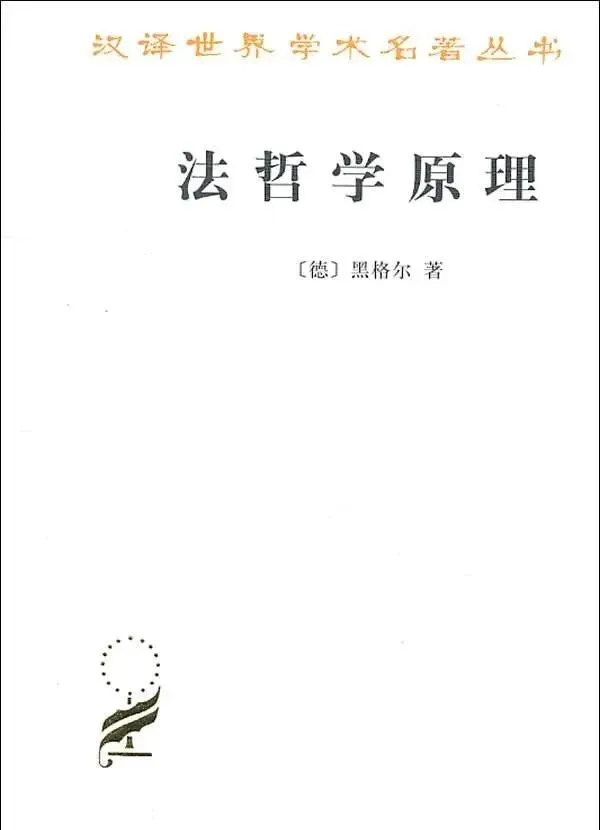
【法哲學原理】,[德]黑格爾著,範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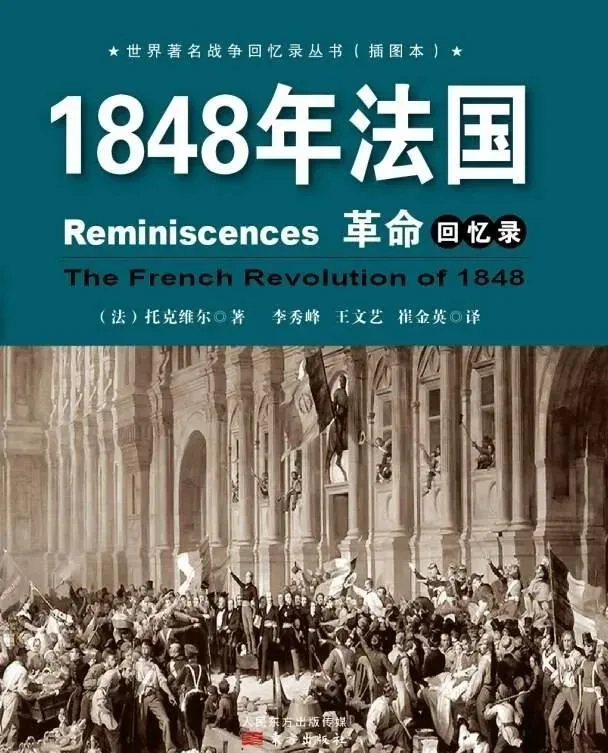
【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法]托克維爾著,周熾湛、曾曉陽譯,上海人民,2005(【托克維爾回憶錄】,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2004)

【舊制度與大革命】,[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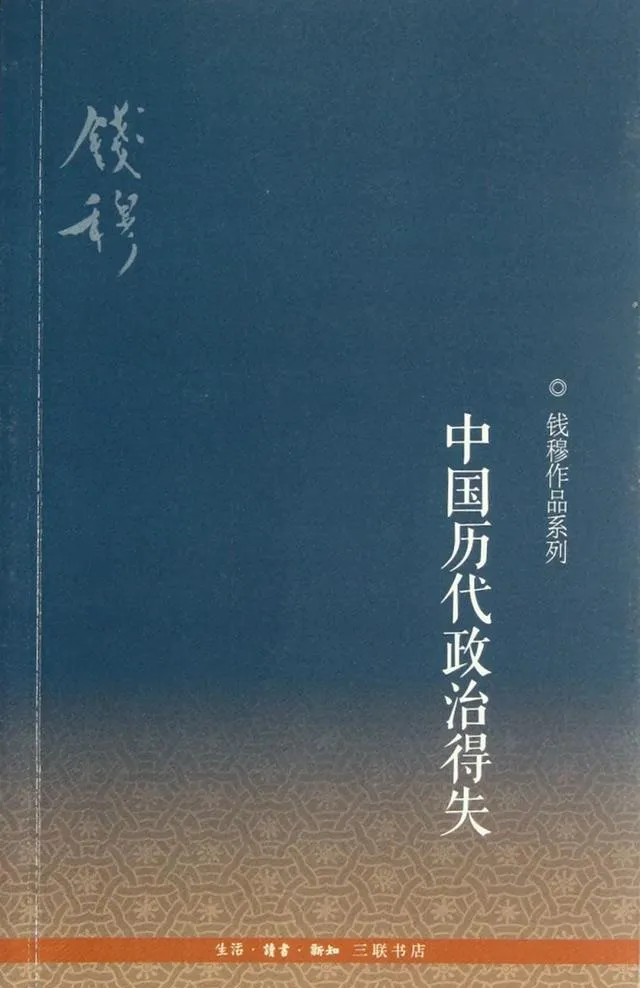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著,北京三聯,2002
「開卷有益」是一句很小就知道了的話,那時候的家長和老師常用這句話鼓勵讀書,後來,就知道了只有「好書」才讓讀,才「開卷有益」;再後來,有了「讀書無禁區」的討論,那該是【讀書】雜誌創刊時由李洪林的一篇文章所引發的,當時我也寫了一篇文章,說是要讀「社會這本大書」,其實是支持「讀書無禁區」。
但不管有沒有禁區,人其實都受著各種各樣的限制,而且,一旦發現那些不大容易看到的書,是一定會拿起來看看的,這倒不是因為那些書就是「好書」,而是純粹出於「好奇」——好奇是人的天性,是一切知識得以可能的前提。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的一開始就說:求知是人的天性,而求知則起於好奇。
當我也開始步入老年的時候,對「開卷有益」卻有了許多新的體會。一是對一個人來說真的有「開卷有益」的「效果」,那一定是因為這個人已經讀了許多許多的書,而且總在思考,總在想表達什麽;只有在此前提下,任何一本書,甚至偶爾隨便翻翻的報紙、雜誌,才談得上「開卷有益」,因為總有所觸動,而且馬上聯想到另外的問題,於是就要把這些觸動趕快記下來,怕過後忘記。這樣很苦,也失去了書籍本來所帶給自己的樂趣,這時的「有益」,具有很強的功利性。我很想回到過去那種散漫地、無所用心地讀書狀態,可惜一時回不去。因為某種可以被稱之為「範式」的東西已經深入內心,即使自己不知道,其實只能在這種「範式」的指導或引導下閱讀。
其次,所謂的「開卷有益」,並非指的只是「新書」、以前沒看過的書。真正「有益」的,倒往往是重讀時的感受。但人為什麽會去重讀一些書呢?無非是因為要用了,這才重新翻找。我不知道別人怎樣,就我而言,寫一篇文章,大部份時間都花費在翻閱過去看過的書上了。為了找到某段話或某個意思,真是費盡周折:明明記得在這本書裏,而且似乎記得在左面,但就是找不到;找不到就無法下筆,卡在那裏。但,往往也正是為了尋找某段話而在一本早已看過的書中有了新的另外的收獲。這說明人心中的「範式」是網狀的,就如蜘蛛網一樣,隨時可能捕獲一個偶然的闖入者。自然,「網狀」越密集,也就越「開卷有益」。
由此可見,「開卷有益」的「益」,本身總免不了功利的目的,而收獲卻在那直接性的功利目的之外;所謂「之外」,無非是為下一個或另一個功利目的提供了準備;當然,為了實作那一目的,又會意外得到許多超出那一直接性功利目的之外的收獲。
人生與書結緣,大約就是這樣一個迴圈反復的過程,而且總在那種直接的功利性目的的滿足與不滿之間。
但畢竟,有些書是真的可以稱得上「開卷有益,百讀不厭」的。
我這裏首先舉出兩本書:一本就是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另一本是托克維爾的【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
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是要給研究生們上「原著精讀」,所以自己先要不斷地看。這本書從我自己讀研究生算起,至少總讀了不下十遍。現在給別人講,再讀,而且每次都有新的體會,甚至可以做到每次講的都不一樣,同一段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幾種理解,再加上對時代、作者當時的心境、具體的語境、幾個不同的譯本或譯法、面臨的問題的轉換、在後人那裏所引起的不同反應等等因素,於是就會說出幾套完全不同的話。一篇【法哲學原理·序言】,不過15頁紙,但裏麪包含了多麽豐富的內容!僅「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把哲學當作私人藝術來研究,哲學具有公眾的即與公眾有關的存在」這一句話,就需要討論一個到底「什麽才是哲學」的問題;還有柏拉圖的理想國本質上無非是對希臘倫理的本性的解釋,而且他已經意識到一種更深刻的原則正在突破這種倫理原則,於是就想借助於某種外在的形式來壓制住這種渴望,「殊不知這樣做,他最深刻地損害了倫理深處的沖動,即自由的無限人格」;以及那三段廣為流傳、幾乎人人皆知的雋語:「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東西都是現實的」,「這裏是羅陀斯,就在這裏跳罷」,「密納法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就能讓人有多少感慨、多少議論可發!它不但要講到你所理解的哲學,講柏拉圖的理想國,講希臘倫理的本性及那種倫理深處的沖動,即自由的無限人格,還要講他所理解的「現實」與「合理」,講哲學與現實的關系(包括馬克思為什麽要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及他為什麽會認為「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等等),當然,在這些話後面,是對中國當下哲學狀況的認識,包括對啟蒙或「再啟蒙」(也就是思想閃電)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和感受,是我十幾年前萬萬想不到的。
以前談到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認為這是他最保守、甚至最反動的一本書,現在我卻認為這是他最深邃、最成熟的奠基之作,這期間所發生的轉變到底折射出了什麽,是時代的變遷?還僅僅只是我個人從心態到觀念上所發生的轉變?這裏面的差異,其實也就是黑格爾自己的歷史觀(絕對精神、時間中的理性)與海德格爾的歷史觀(生存論、時間性的情緒)的區別。而我們,恐怕又只能在這二者之間尋求解釋。
至於托克維爾的【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就不多說了,僅就那種把理論思索轉變為一種敘事結構的體裁就足以使人陶醉;而且這是一種我心儀已久、並多次試驗(如我的【沈默的視野】)的方式。要知道,正是這個人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做出了如此深刻的論斷:在未來的黑暗中,人們已經能夠洞察三條非常明顯的真理。第一是今天的人們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你可以控制或減緩它,但卻不能戰勝它;第二,世界上所有社會中,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就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復存在的社會(想想馮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論】,就知道被我們所誤解了的「封建社會」,難道不是一個逐步消滅「貴族制」和確立皇權至上的過程嗎?);第三,沒有哪個地方,專制制度產生的後果比這更嚴重了,因為在專制政府中,人們之間已經沒有種性、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系,他們一心關註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於是專制制度也就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等於把人禁閉在私人生活之中……只要平等和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將永遠不斷下降(馮棠中譯本,前言)。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說出過這樣顯然是真理但卻完全不被人所意識到的話呢:「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第210頁)這幾乎可以稱之為托克維爾的一個基本信念,因為這本書的第一、二兩編幾乎都是圍繞著這一主題而展開的:「有件事乍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余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第64頁)
至於說到一本國人自己所著的書,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錢穆老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裏面有些非常精彩的論述,這種精彩不在歷數中國歷代政治變遷的過程,而在歷數中所透露出的那種悲涼與無奈。秦漢以後,奴隸制度早已推翻,至此再無貴族承襲,只有皇室一家世襲,這是一;在古代中國,皇室與政府是分開的,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但到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據正史記載,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吸取了這個教訓,從此就廢止宰相,倘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只一個皇帝獨裁,用來講明清就可以叫名副其實,這是二;相對於西方世界,中國有制度無憲法,有法制(一個制度有了毛病,就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治它)無法治(法治隨多數人意見而決定,是謂民主),有職責(須盡力踐行之道義)無主權(自由意誌之權利意識),有士人政權與部族政權間的交替(於是很可能事事出於部族、某特定集團之私心),無貴族政權與軍人政權間的更叠(二者不易區分,貴族多為軍人,軍人掌權便為貴族),有造反(每到政治極端腐敗,造反的結果就是換一批人,重修製度)無革命(變法派與革命派在到底什麽才是中國革命之物件上爭論不休,反倒使憲法、言論等革命性政制建設無法成型,即擺脫不了「不成文法」的慣常模式),此其三;最後,就是因對清朝政權之不滿而擴充套件為對全部歷史上的傳統政治的不滿,進而再表達為對全部歷史傳統文化的不滿,「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沒有了」,「試問哪裏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
於是,我們也就在錢穆老先生這裏隱隱看到了一種與黑格爾和托克維爾相似的東西。
有了一個可供參照的基點,於是一開始所說的那個「範式」,便在暗中導引著人的讀書生活;而一個人在朦朧中所期待的,無非是對這個基點的深化或擺脫。
(2007.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