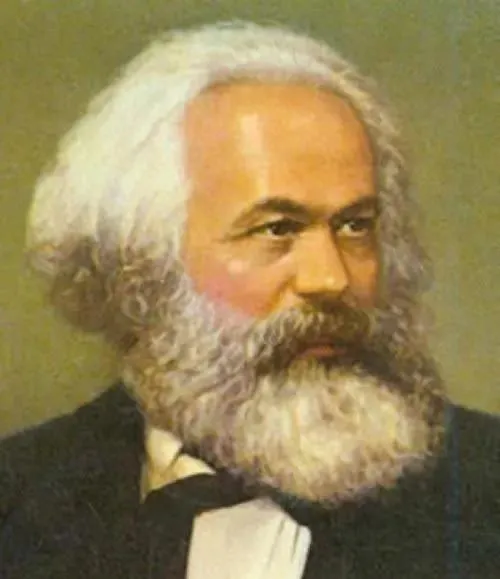
20世紀70年代,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影響,激進的地理學家把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思想納入文化地理學科體系,生發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興起。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和新文化地理學的交互作用促成馬克思主義風景觀。
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風景觀的探討尚未引起國內外學者的足夠關註。1989年的論文集【地理學新模式】首次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地理研究,地理學研究的新模式主要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啟發。論文集裏僅有少數作家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展開人文地理學研究,其中馬克思主義學者史蒂芬•丹尼爾斯(Stephen Daniels)關註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和風景之間的相互關系,但並未系統闡釋馬克思主義風景的內涵和思想脈絡。
此外,【勞泰瑞奇風景研究指南】(2019,第二版)零星提及馬克思主義思想與風景研究的幾位學者。英國地理學家約翰•懷利(John Wylie)在【風景】中在論述馬克思主義、藝術史和風景互動時,對風景作為「面紗」在文化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地理研究中的表征和象征意義做了簡要概述。國內學者對於馬克思主義風景觀的研究更少見,【新文化地理學視角下的文化景觀研究發展】一文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對文化地理學的影響表現在靜態和動態兩方面:一在靜態的意識形態構造上,景觀呈現的結構是垂直的。景觀作為面紗,掩蓋的是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差異和不公平。二是作為生產實踐的風景聚焦風景的物質層面,關註景觀的勞動生產過程,揭示風景在日常經濟活動中的動態結構。
本文擬首先梳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與新文化地理學在思想脈絡上的相互影響,並對馬克思主義風景觀的內涵和主要研究議題進行探索,旨在為國內外文化風景研究提供一個新思路。
一、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與新文化地理學的相互影響
從歷史軌跡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歷史階段正是新舊文化地理學爭論正酣之時,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與新文化地理學相互影響,共同發展。其中,美國著名文化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馬克思主義學者丹尼斯•科斯格羅夫(Dennis Cosgrove)和丹尼爾斯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學家受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啟發,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思想,研究風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內容和空間生產模式。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被界定為「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觀點、概念和理論框架對地理問題的研究。 盡管沒有局限於某一類社會,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主要集中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地理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是70年代激進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相結合的產物。
1977年【激進地理學】一書的出版標誌著激進地理學高潮時期,激進地理學家幾乎對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所有的地理問題進行了反思,他們反對自由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對地理學的影響,批判人文地理學家忽略社會弱勢群體包括女性、流動工人以及貧困、犯罪等城市和鄉村社會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被現代地理學所接受,導致新興的批判人文地理學的興起。
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給文化地理學帶來的新思路是:地理學所關註的空間超越了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概念,更關註社會空間的塑造、空間和時間的關系以及空間的生產。
文化地理學家哈維也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主張套用歷史-空間-社會三維辯證法把空間生產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的核心中,把馬克思主義空間化,開創了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空間美學新模式。
1969年,哈維概括了地理學中空間概念的演變,揭示出空間概念的差異是與空間背後的文化價值觀密不可分的:「一個社會所發展的用來表示空間的概念框架不是靜態的,自古以來空間概念已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文化的變化一般包括空間概念的變化,但有時透過科學發現突然需要對空間概念進行重新評價,這對現行的一套文化價值給予了猛烈一擊。」哈維認為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應聚焦城市化理論,為此,他把社會正義引入到城市空間地理學研究之中。
同樣,後現代地理學先驅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中認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空間是一種上層建築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空間和時間的生產,也同時生成了相應的社會關系。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空間的生產,尤其是差異空間的生產是理解資本主義存在及其理論內核的關鍵。
20世紀80年代之後,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地理學之間的雙向互動日益深入。 在哈維、多琳•馬西(Doreen Massey)以及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等多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的共同努力下,歷史地理唯物主義進一步成為文化地理學的重要理論依據。空間化歷史唯物主義成為包括新文化地理學在內的現代地理學的核心概念並被批評性地套用,這一時期的現代地理學受到人文主義、現代主義、結構主義以及解構主義等思想的沖擊和影響。
例如,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受艾爾都塞結構主義影響,主張用結構主義的社會分析模式解讀城市社會空間,他的馬克思主義城市地理學「強調確定的分析範疇,如生產方式和社會構成;強調各個重要鏈條中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他主張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系統來解讀城市空間。總之,80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以激進的風格重寫文化地理」,引導科斯格羅夫和丹尼爾斯等地理學家在資本主義再生產新模式下,對新文化地理學的核心概念「風景」進行全新界定。
二、馬克思主義風景觀的內涵
1987年,科斯格羅夫和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發表的【文化地理的新方向】標誌著新文化地理學登場。新文化地理「既聚焦歷史也聚焦當代(但始終關註情景化和理論化),既探討空間也探討社會(不僅僅局限於狹義的景觀),既探討鄉村也探討城市,既思考主導意識形態也考察文化的偶然性。總之,強調文化在人類生活的中心地位」。1989年,丹尼爾斯也強調新文化地理學應密切關註文化作為社會權力的媒介,在維護精英或官方權威中起到的作用。其原因是作為傳統文化地理學核心概念之一的風景,不會輕易接納權力和沖突等政治觀念,甚至試圖消解或掩蓋風景的政治話題。可見,新文化地理學正是融合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交叉領域,對傳統文化地理學中的風景概念重新界定。
早在1983年,科斯格羅夫就敏銳地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為文化地理學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首先,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地理學都關註文化生產和實踐的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地理學從同一個本體論觀點出發,都反對任何形式的決定論或者線性的因果解釋,堅持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定義為歷史的。
這一點也是以卡爾•索爾(Carl Sauer)為首的舊文化地理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索爾在【風景形態學】中力主反對環境決定論,從概念上區分自然風景和文化風景概念,指出自然是文化實踐的基礎和產物,強調文化和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科斯格羅夫指出舊文化地理學存在的兩個問題把文化地理學理論研究帶入困境,一是沒有從理論上界定文化產生的原因和文化的特性,二是忽略了文化中的階級內容。
科斯格羅夫為新文化地理學總結了三大任務。第一,文化地理學家要揭示不同生產模式下,地方和風景所隱含的社會意義,並且把這種研究與社會和經濟形態的歷史背景結合起來,原因是每一社會和經濟形態都有其具體特性,其生產和再生產都發生在具體空間例如風景之中,社會形態在空間中書寫歷史,社會形態的形成是風景在不同生產模式中的疊加。文化地理學的第二個任務是把空間並入文化生產的象征程式碼中,原因是意識形態作為階級社會的象征性權力,其空間的占用和再生產旨在維護階級統治的合法化和長久化。
「風景既建構象征性權力,又被象征性權力所構建。」第三,作為革命性實踐活動,文化地理學不僅要揭示人類行動在風景生產和維護中所起的象征作用,更要批判性地審視空間組織和風景中的新形式。總之,科斯格羅夫首次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納入文化地理學的理論方法之中,提出把空間生產、空間建構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形態列入風景的理論框架和研究主題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包括經濟形態、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體。
1984年,科斯格羅夫在【社會形態和象征風景】一書中進一步明晰了馬克思主義文化風景觀。 他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下對風景概念從15世紀開始的演變史進行梳理、概括,形成激進的文化風景觀——「風景是一種意識形態概念,它代表某些階層的人們透過想象與自然的關系,表征自我和世界」。科斯格羅夫把風景概念的起源定位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早期資本主義城市,「城市是資本主義和風景的發源地。」
這段高頻參照正是對科斯格羅夫風景觀的概括:「風景作為一種觀看方式經歷了自己的形成史,但其形成史必須置於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史視域下才能得以理解;風景有自己的假設和結果,但其假設和結果在起源和意義上遠遠超越對土地的使用和感知上;風景有獨特的表現技巧,但這些技巧是與文化實踐的其他領域共享的。」
總之,科斯格羅夫強調風景是作為主體的人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過程中的社會實踐活動。風景的形成受到不同歷史時期社會關系的影響,風景既是客觀的物質存在,更重要的是主觀意識的反映,風景背後是不同觀察主體的觀看方式,代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場,不同的表征方式和美學思想。在傳統的文化地理中,風景被當作一種傳統的視覺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不僅有意掩蓋了各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更掩蓋了平常百姓對自然風景的認知和體驗。
科斯格羅夫在該書1997年再版引言裏,對自己的風景概念再次進行闡述,他認為這本書的創新點是透過參照「社會形態」這一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概念,把風景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象、表述和意義挖掘出來。
英國歷史學家西蒙•沙瑪(Simon Schama)在【風景與記憶】(1995)一書中穿越時空,勾勒出一幅浩瀚宏大的風景隱喻的漫長歷史,引導人們重新發現「隱藏在表面之下的神話和記憶的脈絡」。沙瑪指出,風景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人類對於風景的規劃、使用和改造由來已久,風景神話與人類歷史、民族認同及國家身份緊密相連。風景是自然背後的文化,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例如「帝國、民族、自由、企業以及獨裁——都曾借助地形學,將自然形式賦予自己的統治理念。」
沙瑪的研究意義重大,因為他開啟了記憶和風景研究的交叉領域。 後殖民主義理論家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 Said)指出,記憶和記憶再現是關乎國家身份、民族主義以及權力和權威的重大問題。對於沙瑪的樂觀史學觀,薩義德提出了另外一種思考,提醒學者們關註虛構在記憶和風景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建構社會、政治和歷史記憶過程中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和階級紛爭。
薩義德一針見血地指出,「虛構傳統是當權者經常采用的一種實踐。它是他們在大眾社會中的一種統治工具。……虛構傳統就是選擇性地使用集體記憶的一種辦法,其做法是篡改某一部份的國家歷史,對其他部份進行壓制,以及透過完全功能性的方式擡高特定部份的地位。這樣,記憶就不一定是真實的,而是有用的。」薩義德多次用自己家鄉巴勒史坦作為例子,重申對於巴勒史坦人和以色列人來說,耶路撒冷神話記憶至少意味著兩種沖突的記憶、兩種歷史虛構、兩種地理想象。
W.J. T.米契爾(W.J.T. Mitchell)也對沙瑪的風景記憶觀表示了不同,「我將風景當作一個記憶缺失和記憶擦除的地方加以研究,一個用‘自然的美麗’來掩蓋過去、遮蔽歷史的戰略場所。」薩義德和米契爾警示人們要對風景記憶所涉及的國家身份、民族認同和文化價值觀等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批評的態度,建構風景記憶的過程就是某個國家、民族和種族在某一地方或者空間所進行的空間生產、文化實踐活動,就是權力維護、文化霸權和階級沖突的過程,就是以隱秘、虛構的方式利用、誤導來集體意識,構建國家敘事的過程。
米契爾在關於「帝國的風景」中進一步提出作為一種權力的文化實踐,風景是「人與自然,自我和他者之間交換的媒介」,是它所隱匿的社會關系的象征,不僅僅象征著復雜的權力關系,更是文化權力的工具,是社會和主體身份得以形成、階級概念得以表述的文化實踐,甚至是權力的手段,風景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構型,與歐洲帝國主義密切相關」,是帝國主義為了實作自己的目的,「解放」「自然化」「統一」這個世界的手段和媒介。將帝國意識灌輸到當地風景之中,實作風景的「自然化」。 除此以外,殖民者更多地透過風景的空間擴張推進殖民活動,其結果是,「在它們面前展現的‘前景’不僅僅是一個空間場景,還是一個被投射的‘發展’與剝削的未來。」
科斯格羅夫和沙瑪主要從歷史層面探究風景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地方文化傳統,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弗雷德•英格裏斯(Fred Inglis)對風景的概念界定則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思想。他把風景視為高張力概念,其目標是直接打破統治階級的幻想,原因是「風景位於幾個概念的交叉點上,這些概念正是一個社會科學家竭力區分的:‘機構’‘產品’‘過程’和‘意識形態’」。這種張力還表現在把風景當作精英階級的「觀看方式」與風景是日常的「生活方式」兩種風景觀的差異上。因此,不能把風景看作一個客體,而是一個鮮活的過程,風景創造了人,反過來又被人所改造。談論風景時,人們必須考慮風景生產的實踐過程:它被生產的同時其定義被接受和被解讀。英格裏斯對風景研究帶來的啟示是,對風景的解讀闡釋有助於理解和評判某一社會及其文化思想。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在【鄉村與城市】中從文化唯物主義出發,分析產生於地理或者風景中各種文學和文化形式的變化,指出這些變化是英國社會鬥爭、階級沖突及權力更叠帶來的結果:「勞作的鄉村幾乎從來都不是一種風景。風景的概念暗示著分隔和觀察」;風景是英國貴族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權力,透過風景繪畫、風景寫作、風景園藝和風景建築的歷史進行再現,而這些歷史必須與「土地及其社會的歷史聯系起來」。威廉士從豐富的城市和鄉村主題的文學分析中得出結論,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家從不同視角描繪自己親歷或者記憶中的英國歷史和現狀:「不管過去的還是當代的意象,它們都是歷史的建構,是不同政體和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的不同觀點所塑造的。這些意象沒有一個不是沒有實際的鬥爭和修辭爭議的。」
英國左翼藝術史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同威廉士一樣,指出視覺藝術尤其風景畫在揭示土地與人的關系時要考察更大的現實、歷史、物質因素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任何時代的藝術,都是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服務的」。在【觀看之道】(1972)中,伯格審視了西方風景畫傳統中資本主義策略在經濟、社會和性別方面的操控和挪用。伯格首先指出過去的藝術作品之所以被神秘化,其目的是把統治階級的統治合法化,少數特權人物有意編造歷史,使普通民眾被剝奪了了解歷史的權利。
同樣,藝術作品被上層人士收藏,脫離了大眾,成為統治階級文化的一部份。隨著影像裝置的普及、藝術復制品的大量出現,古代藝術被新的影像語言所替代,伯格提出新的問題,「誰在使用這種語言?目的何在?」約翰•巴威爾(John Barrell)在審視了1730年到1840年的英國風景畫後得出結論:風景畫是英國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安•伯明罕(Ann Ber⁃mingham)在【風景與意識形態】(1987)中也指出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的風景畫是意識形態的工具,風景被以風景畫的藝術表征方式符號化、具體化,被權力機構和統治階層給予政治、文化和社會賦值。
總之,主要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影響,風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權力的文化實踐過程,是歷史、文化、地理、政治及經濟等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文化表征,是資本運作、國家立法、權力和社會公平作用於不同種族、性別及階級等復雜關系的具象化。 風景不僅是客觀的物質存在,更是人類主觀意識的體現,反映不同社會階層文化立場的差異性。
三、西方馬克思主義風景的研究主題
除了風景的內涵得到重新界定外,風景的研究主題也得到拓展,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風景與社會公平、風景與女性主義、風景與權力以及城市景觀與空間政治。
第一,風景與社會公平
社會公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過程中逐漸系統化的思想,包括政治公平、經濟公平、教育公平胡民族公平。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社會公平的本質,對資產階級的社會公平觀進行了批評和否定。風景與社會公平正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關註最多的話題,涉及國家立法、司法、執法、社群、民族、種族及性別等方面。
馬克思【資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本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下社會的財富,表現為‘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商品背後是真實存在的貨幣、資本關系,尤其是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的秘密。資本主義市場中經濟現象之間的關系是物化了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風景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媒介和社會意識形態符號,成為了一種商品——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的象形文字」及它所隱匿的社會關系的象征。由此,風景成為切入社會公平/不公平話題的途徑。風景的社會公平性主要包括:一是法律、公平胡政體,二是「風景民主」、公共參與和政體,三是勞工、階級與生產,四是國家、種族與記憶,五是日常沖突和歸屬權。肯尼思•奧維格(Kenneth Olwig)主要透過「實體性」,考察風景生產、再生產(背後是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實踐過程)以及風景的視覺和文字再現過程中,風景是如何呈現社會公平的:「風景不必只從地域或者景色角度來理解,它還可以被看作社群、司法正義、自然和環境公平的一個連結點。」
喬治•亨德森(George Henderson)認為風景是一種社會空間,認識論意義的風景是一種人類實踐和人類思想的物質再現。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風景的真實性具有欺騙性和虛偽性,因為風景是一種「觀看方式,尤其是一種很享受的凝視方式,透過有特權的透視法來宣稱主權。這不僅僅是一種觀看方式,而是地方的真實物質構建。」
溫迪•達比(Wendy Joy Darby)也認為透視法凝視滿足了商業資本主義維護社會秩序和法律的需要,其執行模式有兩個,一是能使觀眾體驗真實空間的再現性,二是政策性,歐洲透過「掌握所有實際的和象征性的測量結果而實作了領土擴張」。唐•米契爾(Don Mitchell)多次重申風景主題的模糊性和隱晦性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本和流通整個過程中,最終的決定因素是權力,風景的政治性和公平問題是普遍的存在而非地方性問題。因此,唐•米契爾建議風景的概念和理論化需要把資本流通、資本的危機、種族、性別以及地緣政治和權力等因素考慮進去。
鄧肯夫婦(James S. Duncan and Nancy J. Duncan)透過研究紐約市郊區貝德福德小鎮的景觀,揭示風景、階級和社會公平之間的權力關系。貝德福德小鎮是特權階層的生活場所,是特權階層的社會地位、社會能力的反映,因此小鎮的鄉村田園風景、風景所象征的歷史記憶和社群文化是小鎮居民全力保護和維持的。
例如,為了保護位於小鎮中心、被視為小鎮象征的「貝德福德橡樹」,社群和居民們多次透過立法和環境保護組織阻止開發商在橡樹附近施工。該小鎮的風景「被看作美學產物受到嚴格控制……居民們很自信地認為透過保持開闊的綠地,他們的審美利益就可以透過空間隔離得以保障,這樣,居民們從空間和視覺上把自己遮蔽在令人煩惱的種族和貧困問題之外」。然而,風景政治涉及的階級、種族、宗教和性別關系等話題,小鎮風景的特權性和不公平性在全球化以及日益復雜的權力體系的當今時代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最主要的批評來自維護小鎮景觀的拉丁美洲工人,他們作為廉價勞動力被僱用,卻被特權群體排斥在外,被迫居住在小鎮之外的廉價社群。
第二,風景與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一直十分密切。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的「女性作為觀看的物件」章節裏,指出歐洲裸像中往往女性為畫作物件,畫家、觀賞者及收藏者通常是男性:「這不平等的關系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中,以致構成眾多女性的心理狀況。她們以男性對待她們的方式來對待自己。她們像男性般審視自己的女性氣質」。在新舊文化地理學發展的任何歷史時期,男性都是風景的凝視者,風景被女性化,是男性觀察、評論的物件,對風景和女性的表征反映男權主義意識形態。溫迪•達比直言,「風景一直是男性的領域。大多數地形學方面的工作反映出男性和軍事性的眼光。
遊覽歐洲大陸,欣賞沿途風景的人最初大多是男性;藝術市場由男性主宰,他們是風景畫派的資助人或是生產者;爭論風景的範疇及其對人類身心影響的美學家是男性;早期風景旅遊的倡導者也是男性;有關徒步旅行和登山活動的討論也反映出一種性別化了的風景象征主義;風景,無論是再現的還是實際的,都是身份的附屬物,正如妻子、情人和女兒們是擁有土地並管理國家的男人的附屬物一樣。」科斯格羅夫認為風景的意識形態體現在其與父權制話語的合謀上,「文化被界定為‘男性’的內容,而自然則屬於‘女性’的內容……這些‘女性特質’表現為非理性、任性和野性,有時也感性、溫柔和馴服—但自然屈服於男性理性和獨創性的控制力,則是一個一貫的比喻。」
女性主義地理學家批評地理學被男性所壟斷,所關註的空間、地方和風景是從男人的視角出發的。瑪格麗特•菲茨西蒙斯(Margaret Fitzsimmons)指出在人文地理學話語中,自然被女性化,風景被女性化,風景與女性都被視為他者。因此,風景經常被認作女性的身體和自然之美:「諸位地理學家主要興趣所在是大地母親的外表和特征。為此,我們務必了解地質學的基本原則,如同畫家要對人體或者動物的解剖有所了解……地表的特征和地球的內在特點值得學習、了解和領悟的是它們的美。」
女性主義學者吉莉安•羅斯(Gillian Rose)十分關註知識生產的政治性,她指出,地理學傳統表現為「一種大男子主義凝視景觀方式,這類凝視具有二元性,既有觀者支配與掌握的主動性,也包括作為女性而建造的‘自然化的’景觀的被動性;既有研究者所宣稱的科學理性,也隱含了被壓制的視覺愉悅。」20世紀7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作家安妮特•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批評了環境敘事的主流視角是白人男性,土地被女性化,女性如何以花園作為自己的風景隱喻對抗男性話語。
1996年,路易士•衛斯特林(Louise H. Westling)首次考察了美國小說中的性別與風景主題,指出美國超驗主義作家雷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強化了美國田園思想核心的帝國主義懷舊——對待女性化風景和自然生物的自作多情的男性凝視掩蓋了對於原始荒野的征服和破壞。
第三,風景與權力
權力與社會公平是緊密相連的社會話題。在【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一書中,達比認同米契爾關於風景是文化權力的工具,風景背後隱匿的是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及其之間的賽局等觀點。他從18世紀英國的風景意象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開始,考察了風景占有所代表的階級沖突和矛盾,展示風景表征與政治表征之間的關系。達比把18世紀英國風景傳統按照文化生產的形式分成風景與早期劇場、權力的印刷與銘印、17世紀風景畫與18世紀英國鄉村別墅、18世紀舞台布景與全景畫,從文化歷史角度,揭示階級概念是如何透過不同時期的風景表征得以傳播、合法化。
在這一復雜的文化過程中,「地理空間和社會形態按高低有序的等級建構起來」,而「在其他領域發揮作用的各種層次的象征性等級制度不斷推進、強化或分解」等級建構。達比還以英格蘭湖區(Lake District)和峰區(Peak District)兩大風景區的立法史為例,揭示了隱匿在風景問題之中的權力關系—「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呈現為風景進入權與政治進入權的沖突與互動等。
唐•米契爾以1913年到1942年的加利福尼亞州農業風景和流動工人為探討物件,揭示了「土地的謊言」。米契爾強調「風景的形塑是妥協的產物,是權力體系和政治經濟學執行產生的多種權力狀況的產物」,每一處風景都是人類勞動基礎上的社會建構。加利福尼亞的農業風景主要是來自不同移民國家的流動工人辛勤勞作創造的,他們為加利福尼亞乃至全美的農業綜合體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被監管和被動隱形的流動工人、勞工營以及失業者、流浪漢留宿地的惡劣條件背後的決定因素是資本的占有和權力運作。流動工人在改造農業景觀中的作用不僅被有意識忽略,他們應當享有的平等和社會權力被資本家剝奪。
第四,城市景觀與空間政治
城市景觀是城市空間研究的主要物件,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對城市景觀的空間生產、區域劃分、空間表征和象征意義等給予大量關註。哈維有諸多關於城市空間生產、資本執行等城市政治的論著。例如,在【公平、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一書中,哈維指出,西方世界卷入了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化或時空發展不平衡的全球過程,所有的新技術進步、快速城市化過程帶來的城市問題以及政治差異都是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驅使。從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理論出發,哈維對城市的意義進行界定,在他看來當代城市是一種復合景觀,一種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工改造的人工制品。
唐•米契爾在【城市權利:社會正義與公共空間之爭】中回應列斐伏爾所說的「城市權利」,以美國城市中的公共空間實踐為例,提出這樣的問題:誰擁有城市權利和公共空間?這種權利在法律層面和街區是如何被決定的?城市權利是怎樣被監督、合法化或者削弱的?這種必須被限制和抗爭的權利在美國城市中是如何被形塑為社會公平或者不公平的?這些問題的背後是米契爾所關註的城市弱勢群體,揭露無家可歸者如何被國家立法排除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之外或者受限進入公共空間。
美國城市社會學家莎倫•佐金(Sharon Zukin)的研究重點是工業化、消費社會以及審美經濟興起的社會背景下,現代城市空間生產背後的資本運作。她多次參照哈維、愛德華•蘇賈(Edware Soja)等人的理論學說,沿續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的批判,認為以文化、藝術符號為代表的「象征性經濟」起到了重塑城市的重要作用,同時,不同的社會階層也在城市空間生產和運作中進行了重組。
她在【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中分析了美國五種不同的城市市區型別,揭示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構建城市風景中的不同模式和形態,以迪士尼世界和亨利•福特產業綜合體為例項探究強大的利益集團是怎樣改造土地的使用權和土地規劃的。佐金在對紐約蘇荷區(SoHo)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變化以及紐約城市的變遷進行多年研究後發現,20年來該區已經被一些特權階層通常是藝術家重新占領,他們改變了蘇荷區的模組屋和生活。佐金指出,風景以一種物質形式表現權力關系,尤其是後現代資本主義的權力關系:「視覺意義上的不對稱權力意味著資本主義吸取潛在的形象能量、發展真實的或者象征的一系列風景的巨大能力,這些風景界定著每個歷史時期,包括後現代性,這顛覆了詹明信的權威論斷——建築對後現代性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資本主義的象征。相反,建築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象征主義的資本。」
佐金直言在現代社會,風景早已超越了「實體環境」的地理學意義,而是物質與社會實踐及其表征的復合體。狹義意義上的風景代表權力機構強加的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關系的體系結構;廣義的風景涵蓋人們所看到的全景:「有權有勢者的地景——大教堂、工廠和摩天大樓——以及無權無勢者附屬的、抗拒的、或飽具鄉土氣息的地景——村落禮拜堂、貧民窟和廉價公寓。」因此,權力、壓迫和集體抵抗把風景形塑為社會的縮影。對激進地理學家來說,風景是一塊資本積累的白板,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歷史階段的空間性。無論是地方還是國家,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是自主的還是被動的空間移動,經濟力量是決定性因素,用哈維的話,「資本創造並破壞了自身的地景」。
結語
20世紀80年代,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與新文化地理學交互作用和共同開發中,風景的內涵得以延展,研究內容和視角得以充實。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龐雜,派別眾多,文化地理學仍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西方馬克思主義風景觀仍然匯集了眾多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然和文化關系的深刻反思和激進的改良社會思想,其革命性、創新性、實踐性和多元性必將在未來的文化地理學研究中得到深化和完善。
西方馬克思主義風景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既關註風景的歷史、地理發生及發展史,又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政治及經濟息息相關,背後是資本主義資本運作、空間生產、權力和社會公平等政治議題的表征和具象化。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沖擊,城市化行程和流動性的加快,風景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內容將愈來愈強。風景與社會公平、風景與權力涉及民族、種族、性別及階級等諸多社會因素,必將引起更廣泛深入的探討。此外,城市風景背後的空間生產和空間政治隨著後現代社會出現的新矛盾和新焦點必將呈現更加錯綜復雜的關系,城市景觀將成為未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研究的重點話題之一。毋庸置疑,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革命精神和開放性大大促進了文化地理學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拓展延伸,也將為中國文化地理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