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族史(national history)興起於二十世紀初,始自梁啟超在1902年前後刊發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和【新民說】等系列文章。由於深受日本、歐洲民族主義的激蕩,這些文字大力鼓吹旨在救亡圖存的「史界革命」,稱:「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遺憾的是世界史(world history)卻沒有人來提倡,長時間裏都沒有得到學界的充分關註。直到1952年前,即使最被贊譽的頂級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諸先生的研究,最遠沒有超出西域、中亞及印度。再就開設的相關課程來看,當時除了清華有雷海宗先生講授的世界史之外,就連由胡適、傅斯年一手打造的北大也只開出了西洋史,許多高校的史學系僅為一形單影孤的中國史。
共和國成立之後,世界史得到了空前重視。旅美歷史學者陳懷宇教授自2011年以來就在【文史哲】、【歷史研究】等期刊上刊發的相關文章,於2024年1月以【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為題結集出版,詳細講述、討論了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學術會議、1955年中西史家在萊頓漢學會議上的接觸,1955年在萊比錫舉行的東亞學會議、1956年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以及1950年代新中國的「亞洲史」研究、中國中古史研究怎樣走向世界等事件和議題。結論是此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表現出強烈的去歐美中心化和去殖民化色彩,世界史的發展也直接挑戰了西方、日本及蘇聯的「東方主義」。(【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台北:秀威資訊出版公司,2024,第1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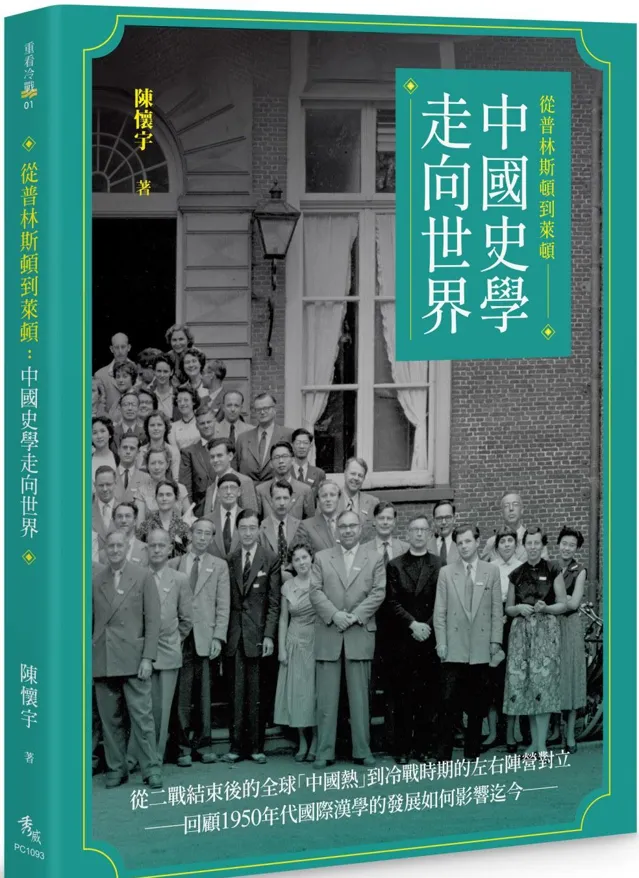
【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書封
是書重點談及的翦伯贊先生,研究領域雖在史學理論及秦漢史,卻是那個年代發展世界史最熱衷的提倡者。早在1943年刊發的【略論中國史研究】一文中,他指出過去與現在的史家,都把中國史當作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歷史,並不關註與世界史的關系;其認為:「中國史固然有其自己之獨特的運動和發展,當作世界史中的有機之一環,則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又絕不能劃出一條絕對的界限。」如是書由此談及1956年9月2日至8日在巴黎舉行的第九次青年漢學會議,有一個晚上討論中國史與世界史相結合的話題,翦伯贊撰寫的【會議紀要】標明了與會者的共識——「世界通史必須註意中國的歷史,而研究中國歷史,必須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觀察。」(第146頁)
作為實際推動者,翦伯贊對世界史學科的發展更是居功至偉。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翦伯贊出任北大歷史系主任,1954年前成立了國內第一個世界史教研室,匯聚了可謂當時最豪華的研究陣容,如楊人楩、齊思和、張芝聯、張蓉初、胡鐘達、張廣達等。再至1963年北大率先成立世界史專業,又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這一發展不僅對北大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產生了深遠影響,且還對推進國內相關教學與研究貢獻良多。就此,著名中國史研究者林滿紅教授說:「中國大陸史學在帝國主義侵略論的強調下,有時較台灣更註意世界史。」(【以世界史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頁)
值得濃墨重彩的,是本書專辟一章談及新中國的亞洲史研究。1954年,為給高年級的學生開設亞洲史,北大成立了由原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周一良領銜的「亞洲史教研室」。1956年,周一良與南開吳廷璆教授共同完成了【亞洲各國史大綱】的起草,隨即在北大率先開出了從古至今不同時段的【亞洲史】課程。此時雖說是「一邊倒」的學習蘇聯,教育部規定原則上所有院系和課綱必須參照蘇聯模式;然無奈蘇聯繼承了太多俄羅斯帝國的思想遺產,學科設定中只有殘留不少種族及文化偏見的「東方史」。此時我們另辟蹊徑創辦「亞洲史」,思想史意義如本書所言:「從學術和教育領域來支持亞洲的反殖反帝運動,從而也將自己與蘇聯陣營區別開來,無疑是一大創舉。」(第170頁)
按照作者的說法,這種在世界研究研究中推陳出新的「亞洲史」,反過來也影響到了蘇聯的東方學研究,這「從1960年蘇聯科學院的‘東方研究所’改組並更名為‘亞洲民族研究所’可見一斑」。(第169頁)如果由此追溯翦伯贊等人的思想脈絡,或可認為這基於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理論設定。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言:「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透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註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革命,強調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打破了各民族原有的孤立狀態和自然分工,歷史就愈成為世界歷史。(Michael K RÄTKE, 「Marx and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018, Vol.63, No.1, pp.91-125)
馬克思繼承德國古典哲學,可以說受到了啟蒙思潮的深刻影響。畢竟,致力啟蒙的歐洲知識人早在十五世紀前後就已形塑了一個所謂「文人共和國」(Respublica lilleraria)的身份認同,不同國籍的學者自由穿梭於巴黎、阿姆斯特丹、維也納、日內瓦和倫敦等地,運用彼此諳熟的拉丁文進行溝通和寫作。在討論歷史話題時,他們大多認為應從中開掘普遍的人類精神,即便撰寫一部特殊民族的歷史,也當努力展現那些可視為人類進步、自由和博愛的永恒法則,即被時人稱之為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就像1788年歌德介紹席勒擔任耶拿大學歷史教授,首堂課他開講「什麽是普遍史,為什麽要學習普遍史?」主題是【歡樂頌】中吟誦的:「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
該校當時共有800-900學生,約一半學生慕名前來聽課,而席勒是康德的最忠實信徒。1784年,康德發表了【具有世界性目的的普遍歷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一文,最先對「普遍史」進行了理論闡釋。由於相信人們的行為不論多麽復雜,都由普遍法則所決定,其中理性和自由意誌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康德認為盡管歷史充滿著混亂和沖突,卻是朝著一個更高的道德目標邁進。即使到1800年前後,當赫爾德、席勒和洪堡鼓吹德意誌文化的世界使命時,也沒有對自己族群的歷史表現出太多興趣,而是期望在康德的「普遍史」意義上找到能讓世界更團結和更開明的可能性。(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 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34)
自十八世紀末的美國和法國革命首次提出現代國家的理念,史學隨之與民族國家的強勢發展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被視為國族史的創始之作,是英國史學家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於1848 年出版的【詹姆士二世即位以來的英國歷史】,講述的是自十七世紀以來該國如何擺脫迷信、專制和混亂,創造了制衡性的憲法和具有信仰和言論自由的前瞻性文化,成為人類進步的榜樣和楷模。另一部也被世人極為看重的經典,是法國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 ,1798-1874)撰寫的多卷本【法國史】。該書自1830年代初開始寫作,至1867年方才完成,用三十多年時間,重點講述了究竟有哪些人、哪些事,讓法國能夠成為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個國家」(such an important nation)。
當時的英、法兩國,史學專業化尚在初創階段,不論是麥考利,抑或是米什萊,不時遊走於文學、政治等其他公共領域,並非專職史家。與之相較,德意誌史學的專業化程度最高,史家獲得教職後多不再轉行;再以大學與國家關系密切,升等、出版及各項榮譽難免不受政治權力的幹預,國族史就較英、法同行更為風行,走得更遠,也更註重「科學史學」的研究規範。以蘭克的愛徒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為例,1841年畢業於柏林大學後,先後供職於波昂大學、馬爾堡大學、慕尼黑大學,1875年擔任了由俾斯麥親自任命的普魯士檔案館館長。其時他撰寫的【威廉一世統治下的德意誌帝國的建立】,重點講述了德國的統一大業,宣稱史學應「對宗教、政治和國族等驚天動地的重大問題采取特殊的立場」。(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pp.34-35)
實際上,當時已被稱為「科學史學」之父的蘭克,對自己的國族史就沒有那麽熱衷。1871年他從柏林大學退休之後,開始了早就著手準備的【普遍史】之寫作。年過八十的他行動不便,只能透過口授,請兩位助手將之整理成文。該書第一卷於1880年出版,以後逐年出版一卷,至臨終之前第七卷交付印刷,最後兩卷由門生杜費根據其從前的講稿整理而成。晚年的蘭克曾經寫道:詩人是天生的,音樂家和數學家也通常渴望年輕時取得傑出成就,然歷史學家必須要到老年。這不僅是因為其研究領域過於廣泛,需要厚積薄發,且還在於漫長一生賦予了其對歷史行程的深刻洞察力。所以,有人說:「令人尊敬的蘭克是以一部普世史而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with a Universal History)。」
蘭克的冷靜與平胡,引起了年輕一代激進國族史家們的強烈不滿。他於1847-1848年出版的【勃蘭登堡家族回憶錄】、【17世紀和18世紀的普魯士歷史】,將普魯士視為一個中等國家,且未放置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引發了許多言辭激烈的批評。前述最鐘愛學生的西貝爾,雖於1856年由老師推薦到慕尼黑大學擔任歷史教授,然倆人不久就分道揚鑣。至少在學術上,西貝爾蔑視蘭克,認為其徒有「失去靈魂的虛名而已(as soulless respectability)」。另一位更激進的國族史家特雷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 於1872年讀到蘭克的新著時,在給朋友的信中禁不住怒斥道:「此人應生活在英國或義大利,在那裏其偉大是可以得到毫無保留的贊賞。」(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pp.37-38)
糟糕的是,這些激情過於四射的國族史家們,為爭取民眾對當前施政的支持,難免會對自己的國族歷史進行某種不適當的美化和誇耀。就像馬克思稱麥考利為「歷史的系統篡改者」那樣,此時沈浸在德意誌統一喜悅之中的這批史家,極為推崇普魯士的尚武精神和好戰意誌,大力鼓吹德國人是上帝的選民,無論在文化,抑或在精神方面,都比其他民族更為優越。再以前述的特雷奇克為例,1866年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教授之後,在課堂上及撰寫的【19世紀德國史】中充斥著對德國歷史的極端解釋——所謂「勇敢的民族擴張,懦弱的民族衰亡」,強烈主張德國占領、獲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世界霸權。這也被漢娜·阿倫特稱為「民族主義中最危險的概念」(the most dangerous concept)。
二戰結束之後,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了較大的擴充套件。共享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理論的蘇聯、中國,堅持「厚今薄古」,論及世界現代史的演化,一個強調1917年「十月革命」的重要影響,另一個偏重於亞、非、拉各國「反帝反殖」的獨立運動,兩者並非完全一致。反觀此時的西方,至少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報告曝光,及匈牙利事件爆發前,學者普遍左傾,國族史業已不再獨霸。具體說來,英國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崛起,法國則是年鑒學派的大行其道。前者,以「次國家」的階級為研究主軸,更多講述底層勞動人民的反抗及其對歷史的創造;後者區隔出「超國家」的中時段、長時段,將政治列為「事件史」的「短時段」,稱不值得學者們特別關註。
至於二十世紀以來的「普遍史」,可以說在此領域裏踽踽獨行,做出驕人成就者,是撰寫【歷史研究】的湯因比。在當時主流史學排斥宏觀思考的學術氛圍之中,湯因比早就立誌撰寫一部能夠涵蓋古代與現代、東方與歐洲的歷史巨著。該書自1927年動筆,1961年完成,歷時三十多年,共十二卷、九千余頁,討論了愛斯基摩文明、鄂圖曼文明、斯巴達文明等二十四種文明的誕生和演化。其中包括已經「衰亡」的十四種文明,另外七種仍然「活著」的文明。湯因比以「哥白尼的方式」(Copernican)否認了國族與西歐在人類歷史的中心地位,更看重文明「在全人類和全體生命的表現與成就中所顯現出無所不在的力量」。( 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J. Toynbee: A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64)
當下學界多認為「全球史」的寫作理念,源自於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於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一書。1940年,還曾是康乃爾大學博士候選人的他,偶然機會讀到了剛出版的【歷史研究】之前三卷,被深深吸引而欲罷不能,決心也要撰寫這樣一部關於文明演化的歷史巨著。不同於湯因比將文明視為彼此獨立的單元,麥克尼爾強調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促進與彼此影響,並聲稱自己的研究只是對湯因比歷史觀的一項改進。再當1989年,他撰寫的湯因比傳記出版後,一篇書評稱其是當代少許幾位能跟得上湯因比步伐的史家,自然是此傳記的最合適寫作者。(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3 ,Jun., 1991, pp. 821-822)
由此說來,全球史或可視為當年「普遍史」的2.0升級版。1985年,麥克尼爾當選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就職演講中說:「狹隘歷史編纂學必然擴大沖突,相反,明智的世界史卻可以培養一種個人對於人類勝利與苦難的責任,從而減少可能遭遇的淪陷。我確實感到這是當代史學專業的道德責任。我們應該發展一種普遍史,這種歷史應有足夠之處來容納人類諸多差異性。」(「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1 ,Feb., 1986, p.7)同樣受到全球史家們高度尊重,即撰寫【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一書的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前兩年也聲稱自己作為老派的啟蒙思想辯護者,堅信那些普適價值在危機日益深刻的今天,仍然有著非常重要意義。
就其時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話題,陳懷宇之書指出可以用三種寫法。一是全球史,講述世界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和演變;另一是國族史,講述中外關系的發展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還有則是世界史,講述不同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第108頁)考慮到我們眼前的現實,國族、世界和全球都是斬釘截鐵的客觀存在,只要不想入非非、走火入魔,這三種寫法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不必非此即彼,也沒有高下優劣之分。關鍵在於從這三種研究視角出發,不論由哪個方向切入,我們看到的僅是一些特殊性、偶然性、或碎片化的「歷史真相」。就像蘭克所說每一樁歷史存在之中都可辨識出無限,都出自於一種超然於萬物的永恒,故歷史真理也就「只能有一個」(die Wahrheit kann nur eine sein)。所以,在那些具體史事之上,如何進而開掘和尋找那個更具超越性、前瞻性和包容性的歷史真理,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掂量。
胡成(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