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於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共同舉行題為「深度比較歷史分析的貢獻與局限——【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的讀書會。會議由【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一書的作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和文凱作引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張長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田耕、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杜宣瑩、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韓策、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崔金柱進行評議。限於篇幅,本次讀書會文字稿分三篇呈現,本文為五位學者對【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所作的評議。
杜宣瑩(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剛到英國念書時,接受到的最大的學術沖擊是,有別於中國政治史的訓練首先立足制度的訓練。然而,現在英國的近代早期政治史訓練已脫離制度層面。自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英國政治史研究基本上以制度史為核心,但是到了20世紀後期,開始突破顯性的「制度」,走向隱性的「關系視角」。近些年,許多研究者似乎擔憂,制度研究恐淪為「失落的史學」,促使史家逐漸回歸制度的研究,但采用不同的視角。和老師的這本書和近年來的其他一些歷史研究展現出制度史的研究同趨。下面我談一下對這本書,特別是對英國史部份的理解。
首先,這本書在英國史的內容主要闡釋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的財政發展,包括資訊的控制、金融的擴張及其帶動的制度變革,而相關財稅制度的變革包含了官僚制、稅制、國債、貨幣、分配等方面的變革。此書希望透過金融所引發的一系列變革(政治和經濟制度方面的革命),重新解釋英國的崛起。和老師將研究視野放置在宏觀的歷史語境,啟發我們重新思考,為何當時整個歐洲普遍面臨著16世紀的物價革命和絕對君主制,但唯有17至18世紀的英國進入現代財政國家的階段?
書中提及絕對君主制和16世紀的物價革命導致英國的財政困境,進而造成政治關系,尤其君主與議會,的緊張關系。其實,議會與君主的關系存在前後時期的差異,比如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君主與議會陷入劍拔弩張,而在都鐸時期,二者關系卻相對緩和,因為都鐸時期有「代理人」(men of business)文化,王室與顯貴安排人馬進入下議院,管理並協助透過法案。而在斯圖亞特王朝,正是因為未安排「代理人」,致使其關系緊張。再加上17、18世紀,斯圖亞特王朝後期推翻都鐸孤立外交傳統,參與歐洲戰爭,遭遇內憂外患的困境。一方面有外部戰爭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內部革命及財政危機也迫在眉睫。內外雙重形成的政治危機引發了後續變革。和老師論述的改革啟發我重新思考,比如書中指出的高度官僚化機構,但近代早期英國當時是否已達到高度官僚化,這是我想要請教和老師的問題。為何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從中世紀以貴族為核心的執政團隊,突然一躍變成了高度官僚化的行政群體?
和老師這本書建構了一個非常大的歷史圖景,描繪了「近代國家」 (modern state)或「近代政府」(modern government)的建構過程及整體結構。本書關註到20世紀中期重要的英國史學辯論,即謝菲·艾頓(G. R. Elton)的「都鐸政府變革論」,以財稅制度的視角,打通這段歷史。艾頓認為亨利八世政權先後由兩位主政大臣推動政府制度變革,使得「近代化」「官僚化」和「國家性」的政府體制提前出現在十六世紀前期。這套理論遭受很多批評。和老師這部書實則重新推動這一領域的討論,讓我看到了「新制度史」或「新政治史」的回歸。
我想請教和老師的三個問題。第一,這本書呈現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的高度制度化,比如書中提到17世紀初,中央政府文書的制度化運作,國王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而非個人的角色。但我們是否高估了近代早期英格蘭政權或政府,尤其是16至17世紀時,它的制度化程度及其實際的落實程度?艾頓提出「都鐸政府變革論」後,戴維·斯塔基(David Starkey)反擊主張當時主導整個政權運作的並不是在制度層面,而是在國王的「自然身體」及其延伸的人際網絡。換言之,國王「自然身體」所在的內廷而非政府,才是真正的權力核心。
所以,國王統治國家和政府時,並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其私人關系進行運作。這就是斯塔基的「親密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imacy)理論所強調的。「親密政治」還顯著體現於伊莉莎伯女王時期。官僚們一方面抨擊女王透過「自然身體」形塑的內廷制度及人際關系幹預政策,但另一方面,官僚們同樣在自己私宅裏復制私人式的門客文化,藉此幹預政治運作。換句話說,內廷和門客系統形成都鐸時期穩定的「雙軌制度」,即「關系」和「制度」並列的政治文化。這尤其顯現在文書方面,雖然都鐸時期已建構一套政務文書制度,但如果檢視國家檔案,會發現當時中央政務文書的真正經手者及行政中心不在政府,而在掌握行政文書的國務大臣(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的私宅,透過字跡可發現文書皆由門客書寫,且門客鮮少擔任政府官員。總而言之,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高估了「制度」在16和17世紀英國政治中的作用。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財政方面。都鐸政權有非常多規避監管的隱性財政,例如女王的官僚豢養大量的間諜,且酬傭方式並不是由國庫支付,而由女王個人金庫支付。此目的便是規避政府的監管,彈性強化女王對財政的掌管能力。其中,女王還會對表現突出的間諜施以特殊恩惠。比如,間諜Nicholas Berden的家族獲得王室家禽供應商的特權。這些都是隱性潛在的財政支出。另一方面,王室也透過封建監護權或投資等實作獲利。我們應當註意隱性財政支出和收入,且透過上述文書、權力運作和財政看到都鐸政治呈現一種「蠻荒的狀態」,即雖然有正式制度,但是大家都遊離於制度之外。

法蘭西斯·沃爾辛厄姆,伊莉莎伯一世首席國務大臣
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即官僚體系。和老師指出,17世紀出現了高度專業化和制度化的官僚,為什麽在近代早期遊離在制度內外的英政權會突然形成這樣的官僚群體?在中世紀時,貴族並沒有受到職業性的行政訓練,為什麽最後會形成如此專業性的官僚?主要是在都鐸時期,當時文書行政基本上依托門客系統。這些人之所以成為門客,部份原因是他們沒有辦法透過正常的渠道實作升遷,轉而依附權貴,成為私屬門客。這群人的出身不同於鄉紳,也不同於貴族,大部份出身商人家庭,基於家世背景、投資知識或職業需要等,接受牛津和劍橋大學,以及律師學院等法學(而非經濟學)訓練後,成為職業性門客。表現優異者被舉薦至中央,擔任顯貴在政府的耳目,或被安排入下議院,形成先前所述之「代理人」。 總之,這群人之所以成為高度專業化的官僚,原因並不在於制度,且他們受益於本身的私領域背景如親屬地緣關系、商會網絡或特許公司投資等,得以收集和掌控精確的稅收資訊,因此才能實作大量的稅收,完善財政制度。
最後一個問題是和老師這本書裏提到了在近代英國進入財政國家階段,三種財稅的變革——稅、債、幣(也就是紙鈔),及其相關的信用危機。信用危機不止反映在商業和產稅方面,還反映背後擔保人的身份轉變與信任感。這涉及「君主身體」剝離的趨向及其對之後信任觀念的長期影響。中世紀時期,「君主」與「國家」捆綁在一起,而在書中論述的時期,即近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王」和「國」開始進行了切割,所以國家主權者的變移會影響對原擔保物件,即君主,的信用度。與之相關,民眾對於「君主」或「國家」作為主權者的擔保能力之認知,連帶影響稅、債與幣的內容由君主的私內容轉向國家的公共性,值得討論。
崔金柱(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和老師書中有兩章是講明治時代的日本,從1868年寫到1895年甲午戰爭。我在2015年寫博士論文時,閱讀了書的英文版,收獲很大,當然也有一些疑問。我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談自己的理解。
第一,雖然本書將英國與日本作為比較物件,且論述的是同一制度,但我覺得二者存在明顯不同。因為英國可以被視為是「原發」的財政國家,而日本只是模仿或「繼發/後發」的國家,二者不能等同視之。第二個問題,其實與第一個問題相關。和老師傾向於否定個體能動性的作用,一系列的表述當中都采取比較負面或否定的態度,認為個人(包括聰明的領導人)在面對危機和特定的社會結構時,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情境,無法做出絕對理性的選擇。此時就涉及上一個問題,即日本與原發狀態下的英國很可能是不一樣的。
以材料來看,本書的日本部份除了使用二手的論文和著作,主要使用的是大隈文書(大隈重信在1881年之前執掌日本的財政金融)和有關松方正義(其從1881年到1895年來執掌財政金融)的個人資料,同時借用了澀澤榮一和五代友厚的資料。總之,運用的都是他們個人的資料,當然他們記錄的東西是政府的事情,但文書卻都是他們個人的東西。但反過來講,和老師否定說這些人不夠理性,也缺乏知識,不足以掌握實際情況,所以他們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大的情境當中肯定會出錯。出現錯誤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從比例上去做這樣一個判斷,我覺得需要討論一下。

松方正義
我主要讀的是松方正義的文書,關註的是他擴軍的過程。具體是指,松方正義在面臨國內政治洗牌和國外國際危機的雙重背景下,是如何從1881年開始進行的政治改革。透過考察松方正義在19世紀70、80、90年代與別人的書信往來和他自己主編的各種政策檔,我認為我們不能太過於低估這幫年輕的革命者。因為他們幹革命的時候只有30歲左右,正值壯年,對於很多事情的考量和判斷其實超出我們的想象。所以,和老師強調的觀點對於英國可能是適用的,但對於作為後發國家的日本和晚清需要再討論。當然,「後發優勢」是現代社會的詞匯,但這不影響我們用這一含義去理解當時的日本。而且從這些做出關鍵政治決策的領導者的史料來看,日本的確存在後發優勢。
接下來,我做一個同一時期中日之間的比較。翁同龢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長期執掌戶部,甲午賠款借款之事,主要操刀的人便是翁同龢,他應該算是最終決策人之一。我看翁同龢的文書,發現他與恭親王奕訢的通訊非常有趣。翁同龢經常在日記裏寫道,駐俄公使許景澄發來一份電報,裏面全是一些現代財政名詞,翁同龢老是問,電報裏寫的是什麽意思。同樣的電文也發給了奕訢,奕訢馬上給翁同龢寫信說,不懂這些財政概念很麻煩。比如電報裏說,俄國人說了,如果以清政府的名義去借貸是6%或7%的利息,如果加上俄國人的擔保,利息會降到3.5%至4%,一下能省很多錢。結果翁同龢一看非常高興。但是奕訢馬上提醒他說,不能這麽做,這麽做就代表我們可能成為俄國的保護國。然後翁同龢馬上反思道,說自己真是什麽都不了解。
反過來再去看松方正義,則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狀態。他經常自信地說,自己30多歲的時候跑到法國去,跟法國的前財長坐而論道,從中吸收到很多經驗,比如外國的國債能否借貸,以及不能借貸的原因,再如借貸外國的錢在國際法上有什麽具體的規則等。
因此,我覺得不能低估了日本這種後發國家的學習能力,因為它們已經有了模仿的物件,而且十分清楚成功和失敗的例子。日本在學習和模仿外國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的因素,即在未推翻舊政府之前,已經派遣了大量人員到歐美各國進行學習,至少是逐漸學成了語言,而且他們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組織轉譯。換言之,他們在進行革命之前,已經轉譯了大量的西方概念體系。所以,為什麽我們現在看他們原來的文書會感覺很奇怪——竟然與現代人完全沒有隔閡?這是因為,日本很早就以同一套西式概念來表達對於現代財政的認知。
當然這只是日本的情況,我覺得和老師對英國的判斷沒有問題,只是說日本具有獨特的後發優勢,再加之其本身情況又比較特殊。因為日本對於自己的政治理念也好,或者說大一點的文化主體性也好,可以隨時放棄這條文化路徑,實作巨大的轉變,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及的。
另外我有一些小問題想請教和老師。第一,我們怎樣去界定「財政」與「金融」的關系?在本書的分析中,金融指的就是財政的一部份嗎?因為現在財政與金融分離了,但好像在本書的描述中,我感覺二者是混合在一起,沒有加以區分。金融就關涉到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包括國債等方面,當然國債也可以是財政的一部份。我想問的是,無論是17世紀的英國,還是19世紀的日本或清朝,在那個時候,財政與金融本身就是不分的嗎?我覺得日本在這個階段至少已經有分離的趨向了,因為它有央行。
第二,是對蒂利(Charles Tilly)學說的疑問。和老師特別指出,日本在沒有發動大規模對外戰爭的情況下就構建了現代財政國家,這就挑戰了卓思·蒂利的理論學說,尤其是他那本經典著作【強制、資本與歐洲國家】中的觀點。我在想,我們是不是只把真正爆發出來的戰爭看作是戰爭,還是說把準備戰爭也看作是戰爭的一部份?雖然日本在1880年至1894年間沒有爆發戰爭,但是它長期在準備戰爭,本書也印證了這一點。因為日本的目標很明確,軍方認定清朝是第一假想敵,而且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盛行很早,國家議會實則也支持對清戰爭。因此,我認為目前本書關於日本案例的介紹和論證好像還不足以用來完全否定蒂利的戰爭理論學說。
最後,談到英國的模式,就是議會和財政的關系。在英國表現為,只有一個有權力的、擁有財政權的議會,才能正常順利地發展和鞏固起現代財政國家。和老師又以日本的案例質疑上述觀點,因為日本是在沒有議會之時就逐漸建立起了現代財政國家。所以,這兩種不同的模式,想進一步聽聽和老師的解答。
韓策(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接著兩位老師的思路,我先談一下日本的部份。崔老師剛才講了作為後發者的日本,其實清朝也是日本借鑒的一個物件。鴉片戰爭結果一出,日本很快吸取了清朝戰敗的教訓,包括後來北洋海軍的建立,日本都是從中吸取了經驗,提升了它的海軍作戰能力。
另外,在財政和其他方面,日本對於西方的了解程度,的確高於同時代的清朝。剛才崔老師特別講到了翁同龢,他確實是不懂西方財政知識和觀念的一個例子,雖然清朝有一些比翁同龢更懂的人,但從總體上來講,從皇帝、太後、王爺到李鴻章、盛宣懷,再到中層的戶部人員,整體落後於日本。而且中央財政官員在年齡結構方面,晚清和日本之間差距也較大,日本都是一幫30多歲年輕有為、有沖勁的改革者,而清朝則是一幫年齡偏大、功成名就的官員。因此,這兩群人的行事動力存在很大差異。

翁同龢
甲午戰爭確實是中國的轉折點,也是東亞世界的轉折點。在甲午戰爭之前,我看資料的感覺是,清朝高層主要是在防備俄國。一方面,是因為俄國於1892年再次侵占帕米爾高原地區;另一方面,是因為俄國在修建西伯利亞鐵路,雖然還沒修成,但是作為駐俄公使的許景澄不斷強調鐵路修成之後對東北的威脅性。因此,清朝在1888年海軍建成以後,將很大的精力放在陸防上,主要是針對俄國,因為它並不覺得日本是最大的對手。
我非常同意和老師講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甲午之後的結局(甲午慘敗)來往前倒推,批評清朝這個如何錯,那個如何錯。在甲午年,清朝完全沒做開戰準備,中心工作是在忙著給慈禧太後過六十大壽,而日本則是在精心準備戰爭。再加之,清朝高層裏很多人對於中外情況不甚了解。日本當時蓄謀已久要把清朝拉進到戰爭旋渦裏,所以清朝則是被迫卷進去,毫無準備,所以甲午的結局確實帶有一定的「偶然性」。
和老師反思三個國家的時候有一些基本對比條件,例如,為什麽英日能發展成現在的財政國家,而晚清就無法發展?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就是晚清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中央跟地方形成了新的財政格局。晚清是否缺乏足夠的動力去推動財政集中?因為集中財政的下一步就可以用所謂的長期信用來融資。還是說,晚清有動力去做財政集中,但實際上無法做到?這兩個問題緊密相關。
我覺得晚清應該有動力去集中財政,因為從皇帝和大臣的角度來講都想把財政集中控制起來,至少從獲益來講是有很強的動力,比如赫德(Robert Hart)整天給恭親王等人講集中財政的好處,而且從現實來看,清政府在關稅上的收益也的確讓高層看到了切實的利益。雖然中央層面有動力去推動此事,但後面種種的歷史情境迫使其難以實作。為什麽難以做到呢?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事情,其中關涉到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系,這是近代史中非常核心的問題之一,之前學界一直有爭論。一種觀點認為,晚清最後是「地方財政」,中央完全失去了控制;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央依然有很強的財政控制能力。其實這兩個觀點都能找到許多材料作為支持證據。
我在【江督易主與晚清政治】一書裏專門反思了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如果說兩種觀點是矛盾沖突的,而各自又有理由和範例,那麽我們是否考慮要用一種新的理解思路來推進既有的研究?和老師在書中指出,中央不是完全失去了對地方財政的控制,但我覺得中央財政相對地方財政來講是很弱勢的。一方面,我們看到雖然到1890年財政收入漲到了8000萬兩,但中央實際能直接控制的估計只有2000萬到3000萬兩,而且其中還有好多是固定要發的,所以中央或者說戶部能直接機動的錢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地方的錢不僅體現在賬上,還有好多隱匿的錢,且隱匿的量很大。據相關財政研究,隱匿的量甚至跟賬面上的量持平。晚清各個地方都在哭窮,誰都不敢說自己富,因為一說富就要被迫拿出錢來。但又像和老師所言,面對緊急的事地方又能湊出來,這說明其實地方是有錢的,只不過事情不夠緊急的情況下,中央讓地方湊錢的理由就不充分,地方也就缺少湊錢的動力。因此,在面對非緊急事情之時,地方則是能拖盡拖。從這一角度來講,中央確實難以控制地方的財政。
還有一點,就是不同類別的督撫也有很大差別。如和老師書中提到的山西巡撫張之洞和陜西巡撫邊寶泉,他倆都是京官出身,而且都是北方人。他倆剛到地方做官的時候,山西和陜西的厘金相對較少,而南方省份就不同了。另外,像出身軍功的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等督撫重臣,手上管很多軍隊和洋務企業,而且又是長期任職一個地方,權力更大。雖然理論上來講,清朝可以隨時把他們罷免,但實際並不會這樣做,而且這些人一不高興還要辭職,中央一般要竭力挽留。所以種種跡象來講,清朝雖然保留了任命或者罷免地方督撫的權力,但這一權力與乾隆、嘉慶乃至鹹豐時期均是無法比擬的。總之,中央的權力受到了很大限制,政治上體現出一種「同治」的局面。此外,中央跟地方的財政關系有時候也涉及中外夾雜的因素,像赫德這一方面就是例子。總的來講,我認為晚清應該有動力去集中財政,但是難以做到,因為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發生了變化。所以中央去向地方征錢時,地方會各種討價還價,像以前是中央財政的情況下,地方沒有那麽多討價還價的余地。這便是晚清的社會經濟結構,亦是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存在的隱性局面。
和老師書中還從社會經濟結構、人的能動性、事件的偶然性等方面做綜合性的比較分析,使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都能接受和認可,我特別贊同和敬佩這一研究思路。
首先,談到人的能動性這方面,剛才將晚清與明治時期的日本領導人做了一些對比,我覺得我們不能苛責前人,因為他們面臨的形勢過於復雜多樣,加之對手準備的過於充分,更顯得前人處理不足。但晚清的領導也確實存在重大問題,甲午海戰之前的狀況是,當局覺得現在國內的秩序得到了很大改善,又組建了北洋海軍,並且認為在中法戰爭中與強大的法國打成了平手。這一切都使得晚清高層誤判了形勢,高估了洋務時期的軍事、經濟和外交發展,也低估了海外其他國家對清朝的侵略意圖。
現在的歷史敘事都是以甲午的結局來往前推,認為甲午慘敗的後果應當要以十年前上台的這批人承擔,所有的板子都打到他們身上。他們應該是有責任的,但不至於將責任都推給他們,這是一個問題。當然,晚清的領導人確實有局限。例如,在中法戰爭之後,最高領導人也就是慈禧太後的一個很大心願是想要恢復制錢。當時很多專業人士認為難以恢復,正常應該是進一步統一貨幣。為什麽要恢復制錢呢?我們推測她的心理是,她要為她的丈夫鹹豐皇帝扳回一城,因為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清朝財政大亂,鹹豐大肆發行紙錢,弄得一塌糊塗,所以等於是慈禧恢復了秩序,想為鹹豐扳回一城。但這一政策最終沒有推行下去。
再如,當時晚清想要辦置銀行,但是戶部反對,因為銀行全由李鴻章來聯系,戶部認為李鴻章已經占據了很大的財產,現在再創制銀行,權力將會更大。赫德也是類似的情況,只要他一有苗頭,李鴻章與地方上的督撫(如張之洞)就馬上反對,說赫德已經掌握了那麽多財產,不能再讓他掌握更多的權力了,所以就層層地制約赫德,致使其很多事情都難以開展。用和老師的話來講,在那個時候,清朝在中央財力有限的情況下,開始做一些長期的信用,比如發行外債和國債,向外借債等,但是戶部尚書翁同龢和許多高官都反對借外債,所以事情就難以施行。總之,這都是當時人的能動性的問題。
其次,像甲午戰爭這個偶然性的事情,和老師講發生一個「信用危機」之後,會發現清朝一系列的舉措表明它可以發展成為現代財政國家。我認為這是一個契機,是事件的偶然性,有時候做事情需要一些契機在,但這個契機好像不是只有財政一個方面。
我們看到,甲午戰爭之後,淮系李鴻章的山頭倒了,湘系劉坤一等人也因戰事不利失去了發言權,故戰爭暫時打散了地方的權勢。這時大家要共赴國難,洋債勢必要借,於是晚清中央政府透過抵押借洋債償還賠款,即用關稅抵押、厘金抵押。甲午的那三筆借款抵押了很多東西,到庚子時更是把東南地區的鹽稅、厘金全部抵押了出去。當時督撫不敢違反洋債,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督撫當然不能拖,因為這都是最緊急的事情,定然要按期還款。
在這個意義上,厘金和地方的財稅作為抵押來還債,其實變相地就從地方收回到了中央,雖然錢沒到中央的賬上,但是在給中央還賬。接著海關統收這些財源,理論上意味著還完債後這些財源就是中央的錢。再到清末新政時,中央更是逐漸地收回了地方的財政。庚子事變之後,國家只有1億的收入,到了宣統末年增長到了3億,這十年之內就翻了這麽多,雖然有經濟發展和稅收增多的因素,但主要是集中了地方的錢。因此,從甲午之後往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發展中,可能裏面還有更多復雜的因素在。
張長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剛才聽幾位老師的發言學到了很多,有幾個點與我之前在想的有些相似,也加深了我的一些認識。我主要就三個點來談談感想和思考。
第一點,前面三位老師都提到了,就是從理論上來講,戰爭與國家建構之間的討論。之前大家大多會認為國內戰爭的摧毀性更強,對國家建設的破壞性更大,而這些年的一些研究也指出,在某種條件下,內戰對國家建制有建設性的作用。
另外,像外部戰爭的結局,剛才韓老師說得很明確,它背後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之前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有篇文章就在論述戰爭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系,認為其中存在非常多的偶然性條件,所以二者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有一個比較復雜的因果鏈條。尤其是在籌備戰爭期間,國家需要征稅或需要借貸,這裏的細節值得深入探討。
我筆記這裏寫了一個叫「賭國運」,剛才韓老師也講到國運的問題,像日本籌備了這麽多年其實就是在賭博——贏了戰爭就能實作翻身,輸了就是另外一種結局。如英國、日本贏得戰爭的結局就是實作貿易擴張,當然像日本還會收獲大額的賠款。日本為了備戰向英國借債,對於它們的當權者來講多少是有賭博的成分在。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日本來講,先借到錢實作生存是最現實的策略。但當日本打贏之後,很快就實作貿易擴張,稅收也快速增長,相應地,還貸壓力減輕。更關鍵的是,日本國內普通民眾的借貸信心也會倍增,戰爭的勝利直接提振了國內民眾的信心和未來預期,這反過來也會降低日本政府的收稅成本。總之,戰爭及其勝利,實作的是一個良性的迴圈。
然而,假設結果是戰敗,那這一良性迴圈就不復存在,反而會變成惡性迴圈。這種情況下,國內外貿易會開始萎縮,像清朝便是如此,而且還將面臨到巨額的賠款,還得被迫向列強借債。很大程度上,外部的借款擠壓了國內債券市場的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和老師書中的內容更多的是補充了這一邏輯鏈條,而沒有去挑戰戰爭與國家建構關系的理論。
再者從這三個國家的戰爭的可比性作為出發點來講,清朝確實是更困窘一些,因為國內戰爭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對國內經濟的淪陷性程度太大,嚴重毀壞了國內的政治秩序和經濟市場,對國家建構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狀態。
第二點是我自己特別感興趣的,因為我計劃寫1949年以後的中國財稅改革及其背後的政治經濟邏輯,但到現在我都還沒敢動手研究時間這麽短的中國財稅歷史,所以從這一點上我特別欽佩和老師有如此強的勇氣和信心投入到三個國家的財政歷史的研究中。和老師這本書提到了,財稅改革的背後其實是一些政治鬥爭,是不同派別的政治博弈。像剛才韓策老師提到的非常鮮活的例子,如李鴻章想創辦銀行時受到的質疑和阻礙,實則是改革行程中遭遇的權力派系的牽制。當然,日本當年改革時面臨的亦是同一問題。這個問題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改革的文獻其實很有啟發。
我在想,是不是在這三個國別裏面,像日本和英國的改革派透過一系列具有偶然性也兼具結構性的因素,使得成功掌握了權力,進而將改革措施真正推行了下去。而像清朝,要麽是大家都缺乏改革的意識,要麽是有改革意識的那幫人缺少能力實作權力統合,所以改革的事情就夭折在了初期。這些思考邏輯均是受啟發於本書的內容,我感覺是讀起來還不夠過癮,包括像書中講到的「行動者的過程」——當然這部份可能受篇幅的限制,如果把每個國別都單獨成書的話,可能寫行動者的戲份會更多一些。
第三點,就是制度主義和制度變遷理論的運用,我認為這裏還涉及路徑依賴的問題,包括和老師強調的「序列」(sequence)的問題。方法論上爭論較多的一點是,怎麽選取以及如何選取一個所謂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將英國、日本和清朝放在一起比較,我認為清朝的情況稍微特殊一些。書中講到了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的過程,之後便是開展財政改革等措施。然而從時代的可比性來講,清朝後期其實是「國家再建設」(state rebuilding)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康熙至雍正時期,清朝是國家建構的創始階段,如雍正發現政治上有許多財政危機,於是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財政改革(如「火耗歸公」);而本書論述的這一時期的清朝,其實已經處於非常嚴重的政治衰敗階段,整個國家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相較於中央政府來說,國內的地方統治勢力又相對強勢。因此,從更大的層面而言,晚清的政治結構與英國和日本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像日本和英國雖然國內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但總體上的路線和方向是一致的,大家整體是向著同一方向在努力。如果我們套用奧爾森(Mancur Olson)的「分利集團」理論,會發現晚清存在很多分利集團,國家很難統合和控制地方上的勢力。總言之,晚清與英國和日本面臨的挑戰遠不是一個量級上的。
以上就是我的三點讀後感,以及對我的一些啟發,謝謝和老師和各位老師。
田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長聘副教授):
剛才幾位老師主要是談書的某一部份,而作為社會學者,我有兩個方面想請教和老師,其中一個是理論方面的設計,另一個是比較意識的問題。
和老師這本書的結構,我理解包括三層,第一層是三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歷史的重構,其實是圍繞著現代國家財政制度在三種維度上的成敗展開的闡釋,這是現代財政國家的歷史肌體。第二個層面是,歷史制度領域出現的「信用危機」及其解決策略的問題,這是本書所謂「現代財政國家」的分析核心。第三個層面是社會科學當中比較歷史方法的關鍵問題,比如關鍵時間點的選擇、多重的可能後果及其排除、時序的確定、以及從歷史情境出發考察選擇而非從結果倒推,這些都是方法論上的比較意識問題。
第一個層面,剛才幾位老師談得都很充分了,我主要談一下後兩個層面。首先是第二個層面,即理論方面的問題。這三個比較案例中,本書在英格蘭部份選擇的歷史時段是最長的,從17世紀一直寫到了七年戰爭之前,而日本的時間最短,中國部份,加上最後一章,時間有所延長,但實際上中國本身的時段也相對較短。那麽,中日的案例,更類似財政國家的「改革史」檢討,而在本書涉及的時間裏,英格蘭的「財政國家建設」就遠不只是改革史了,它不僅經歷了圍繞內戰造成的黨爭、政體、護國體制的迅速轉變,而且在進入18世紀後,面臨著密集的王朝戰爭,例如,從1700年開始,和西班牙王室的繼室戰爭,還有和法國波旁王朝的全球性爭霸。七年戰爭非常深地觸及到了信用體制的變革,即英國為何被迫轉向了輝格體制竭力要避免的大陸重商主義體制,來解決因戰爭帶來的共同危機。和老師的處理,間接地把英格蘭的歷史及時段的選擇,置於其和重商主義的對抗過程當中,先是尋找英格蘭的特殊性,進而審視英格蘭和歐洲大陸進行對抗的過程。這個時段的選擇充分地體現出歐洲區域競爭的歷史。而這一特點如何在日本和中國的案例中均衡地展現,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改革史當然也包含了跨國因素,但在相對較短的分期下面,作為改革史的財政國家建立,和作為區域政治經濟的財政國家建設,如何協調?剛才韓老師已經談到了在中國的案例裏面區域競爭的史實,尤其是競爭對手從俄國轉變為日本,帶來晚清體制改革的影響是至為關鍵的。
相應地,本書從制度分析中析出的概念,信用主義的危機,就大致包含「長時段的危機」和「短時段的危機」。「長時段的危機」就是和老師在書中論述到的走出領地國家,集中財政管理,進而實作現代財政國家的轉型,這個過程當中,改革選項會被嘗試,獲得成功或是失敗。另外,還存在一個非常顯著的「短時段的危機」,用社會學的話說就是充滿了緊迫性的改革情勢。正如剛才幾位老師提及的,找到和厘清需要改革的問題是一方面,在復雜多樣的權力制衡體制、黨政體制、改革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開展行動是另一方面。杜老師前面提到了一個核心觀點,即「家產制格局」其實在所有案例裏都存在,但是其對不同國家及其制度改革發揮的影響程度有所不同。與之相似,和老師本書展現了不同國家應對信用危機的過程,及其反映出的差異化改革特征。而這一特征恰恰能夠決定解決問題的方法付諸實踐的程度。
有兩本與清史相關的著作能夠體現出國家面對危機時的改革情勢和改革背景,一本是石泉先生的【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另一本相似的是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的【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兩本書都涉及制度變革,以及面對危機的時局反應。
信用危機及其國家克服,幾乎是整個前現代國家轉型時面臨的普遍問題,這本書的關鍵起點是,在我們難以列舉的差異背後,許多國家卻是面臨著共同的危機感的,和老師的著作在共同危機感的提煉及其闡釋,堪稱歷史社會學著作的典範。然而,這種長期的、普遍的危機和對它的感知,不僅是檢驗不同改革措施的標準(哪些改革措施可以推進,哪些不能),而且會深刻影響當權者對於局勢、情勢的理解和判斷。這也是上述兩本書(【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和【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共通的出彩之處,即豐富地展現出長期危機在短期改革形式上的作用及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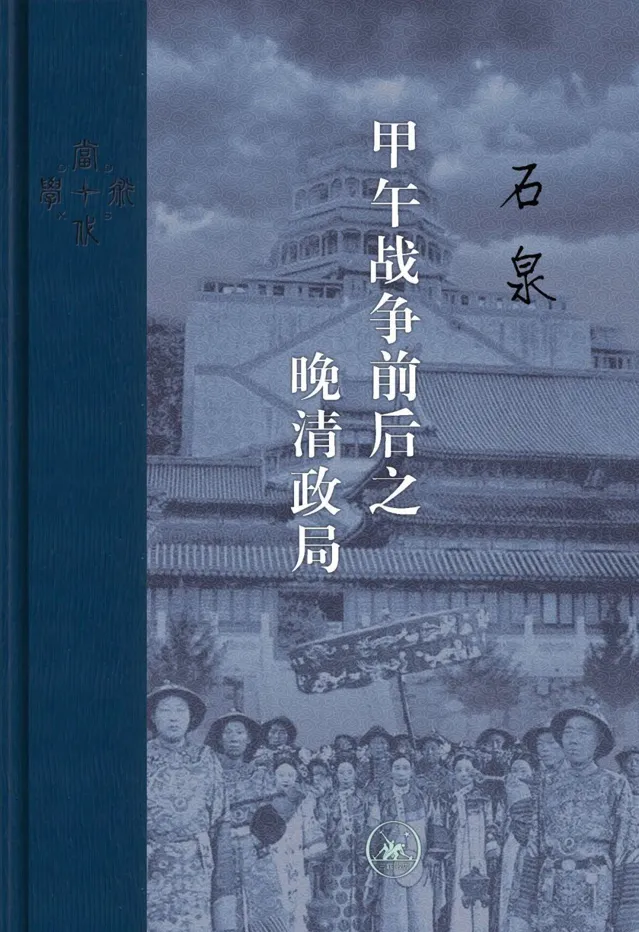
【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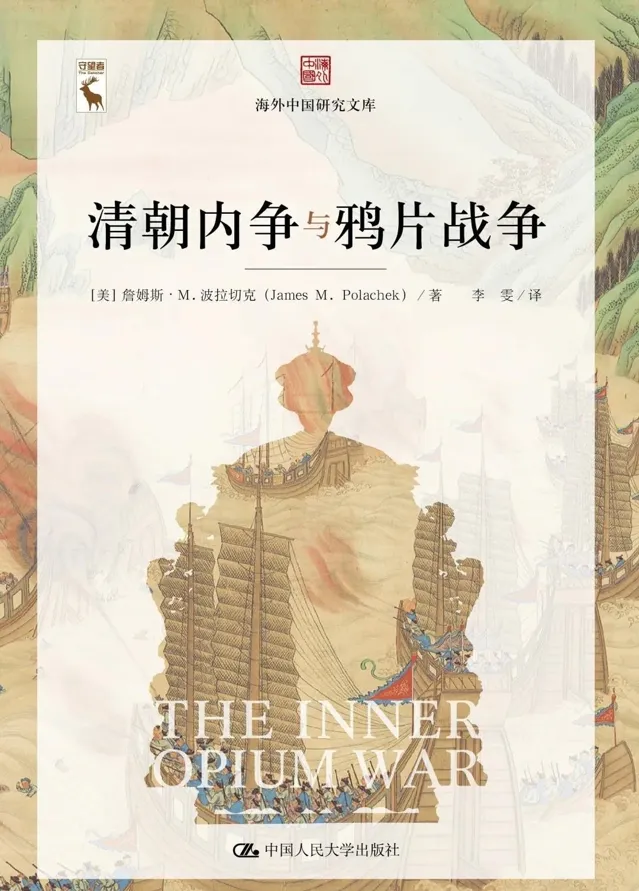
【清朝內爭與鴉片戰爭】
在讀本書英國史部份時,我也會想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卷中談到的問題。這個問題具體是指,在18世紀中期時,英國解決戰爭危機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派為輝格主義的觀點,另一派為托利黨人的思路。托利黨人主張土地財富制,強調對殖民地的直接管理和占有,為母國分擔財政危機。而這一點正是輝格黨人所不贊同的地方,因為其背後是成功的北美殖民者和英國生產商(manufacturer),他們需要確保一個大的生產商和市場,所以無法接受很強的集中管理土地的方案。這也是和老師書中尾聲所講到的關鍵一點,英格蘭長時間的輝格主義政治發生了重要的黨派爭論,強烈地制約了英格蘭從商業共和國走向求富的君主國。
納米爾(L. B. Namier)及其「納米爾史學」認為「權術」是理解英國政治發展及路線改革的關鍵視角。換言之,圍繞在國王身邊的一些權臣以及他們的結黨,被認為是英國政治運作的核心。與之相對的是,有些史學家認為輝格主義和托利主義的黨爭本身並非權術之爭,而是關涉到治國理念的路線差異。實際上,石泉先生的那本書也觸及到了這一問題,即清朝後期的派系之爭究竟是政治上的權術爭鬥還是有其實質上的內容之辯。和老師這本書的微妙之處就在於,試圖將解決制度困難的問題寓於政治歷史的行程中。這是我對中間這一層「實質理論」上的一些感受。
最後再說比較方法,和老師這本書特別有價值的部份是對構成比較的一些基礎手段提出了挑戰。這個基礎手段其一就表現在剛才張老師講到的,什麽是「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以及怎樣選擇「關鍵時刻」?關鍵點和轉折時刻的選擇,究竟是要透過財政史數據,還是要透過數據及歷史檔案背後的政治節奏感來進行判斷?其二就是共性與異性的比較。以上幾位老師提到的內容是對歷史比較研究非常關鍵的問題,核心點是,對建設現代財政國家來說,早期探索國家和後發國家在處理同樣改革問題方面的不同。也就是說,將英國和日本、中國進行比較時,需要考慮的是早發國家和後發國家的差異性,對於後者來講,後發的位置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它們有「學習接受史」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對其改革效果有影響。在針對制度改變和建設的歷史研究來說,國別或區域案例比較,本身是和制度沿革形成經緯交織的。歷史制度,也許不止是一個可以傳統區域差別的「硬考核」(能透過就可以建設制度,不能透過制度就無以建成)。我覺得,這恰恰能夠提示比較歷史的研究,因為純粹孤立地研究每個案例有著很大的挑戰和風險。反過來說,後發國家學習先進國家的歷史,本身也是其改革的一部份,只不過需要在方法上加以更精細地考量和處理。總之,和老師這本書在歷史比較研究領域進行了非常有價值的嘗試和探索。
劉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22級博士生)整理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