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聾啞劇院之夜】,【美】伊利亞·卡明斯基著,王家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7月
卡明斯基詩劇【聾啞劇院之夜】,是關於一個二戰時期烏克蘭的虛構小鎮的聾啞人木偶劇團和居民起義的故事,因為詩劇的特質,使得文本在虛構與史實之間的遊離遊刃有余,讓讀者恍兮惚兮不知此夕何夕——
因為裏面殘酷的世界呼喚你把自己民族經歷的苦難代入,同時詩的語言又警醒著你:世間的苦難有細微的差異,而我們要辨識這個差異,使苦難不流於號哭和數據。譯者王家新參照本雅明在論卡夫卡時所說的話:詩人在這裏要做的不是「以童話來對付(歷史和)神話中的暴力」,而是如科倫‧麥肯所說「闡釋並照亮我們共同的聾啞」。
群眾造就抗爭者,也戕害抗爭者,這個永恒的悲劇以詩演示,則獲得了一些額外的可能性:也許是希望的卑微化身。而所謂群眾,它們依然是滋生抗爭的沃土,詩人保留著這點空間給與未來。而在這之間,聾啞狀態由否定變成積極的拒絕,是不屈的火種。
「你還活著,我對自己悄聲說,因此有些東西在你的傾聽裏。」此乃本書的要義,也是所有幸存者的要義,這裏的「說」和「聽」因為物理上的不可能,引導我們前往更形而上的理解。「聾,像警笛一樣在我們中間穿過。」這樣的悖論詩句不但是金句,還是對思考切實的痛擊。
當然,在2023年閱讀此書,加上過去近兩年烏克蘭的戰爭背景,我們還是無可避免地要面對現實炮火的震耳欲聾。書中反復出現的這句:「什麽是一個孩子?/兩場炮擊之間的寂靜。」已經成為卡明斯基代表烏克蘭人對整個世界的質問。還有更溫柔的:
「開始了:我看見我的國家的藍色金絲雀
從每個公民的眼睛裏啄出麵包屑──
從我鄰居們的頭發中啄出麵包屑──
雪離開了地球並直接落在它應落下的地方──
有一個家鄉,這太重要了──」
這不得不讓我們回憶起大半個世紀之前,保羅·策蘭那句催人淚下的、他早年悼念母親的名作【冬天】的開頭:
「在下雪,媽媽,烏克蘭在下雪:
救世主的王冠是千萬粒悲痛。
我全部的淚水白白向你流淌。
驕傲無聲的一瞥是我全部的安慰。」
詩歌不允諾救贖,那是欺騙,但詩歌與廣大「無用」之物一起屹立在世界的廢墟之上,成為永存的家鄉,因為「在這大街上,耳聾是我們唯一的路障」。

【偏僻之地:斯奈德詩集】,【美】蓋瑞·斯奈德著,楊子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雅眾文化,2023年10月
這本詩集把我們帶回去那個血氣最旺盛時代的蓋瑞·斯奈德,那個「禪瘋子」,他為自己心中沖突著的欲望和對真的渴慕,在世界遊走尋找主流社會以外的「偏僻之地」,而他自己就成為了憑空開拓出偏僻之地的先行者。
斯奈德不是寒山,也不只是後來我們所見所意淫的一名深山隱士。這些詩裏面充滿著一種屬於荒野的力道,似乎在為他散文裏倡導的自然之道、自由法則——The Practice of The Wild等等給出範例,斯奈德從此就是一個詩人合一的踐行者。他的詩的運作方式和詩中人的行為,無不正當、健康、不矯飾,讓我們這個疲乏世代的詩人相形見絀。而他的詩理應成為我們最需要的一種呼吸、一種瑜伽和勞動。
【偏僻之地】的前半部也許你還能讀到,不動聲色的「反文明」的暗示,處處反諷現代社會生存模式的可笑可憐。但就像後面【嘗雪】所寫:
「我曾經一邊笑
一邊親吻,心想,
鉆到被窩裏多舒服——
讓他們睡吧;
這下我才能去獵場。
刀刃鋒利,毛發直豎
走在一塊塊圓石上
渴望著
嘗到雪。」
斯奈德是透過對塵世的確認、對生之欲的廣且深的體驗之後走向荒野的,而且不忘帶上他愛的人、愛過的人和將要愛的人:我們。這本詩集裏占了五分一強的詩和性、性愛、生殖繁衍等有關涉,這個主題一直延伸到他五十歲的【斧柄集】乃至近年的【山巔之險】和【當下集】,其中當然有他沈迷研究的古印度哲學的影響,但更迷人的是他在其中的坦蕩無邪,呼應的依然是1960年代青年文化的解放性以及溯源沖動。
我們皆知斯奈德轉譯寒山與中國那形而上的自然發生關系,但看到足本的【偏僻之地】最後一輯方知他也轉譯過宮澤賢治,與近代日本詩人的進取、對自然的深邃抒情也極有關系。這猶如一個更微妙的押韻,宮澤賢治的殉難者精神原來在斯奈德身上隱藏極深,成為牽引他不落入美洲開拓精神的樂觀主義的一個有力向度。閱讀斯奈德版本的宮澤賢治,也是為後者賦予更多當代性,兩人的幸福觀相異,卻殊途同歸於阿修羅的憤怒和悲憫。

【上京】,李唐著,中信出版集團/中信·春潮,2023年1月
自張北海【俠隱】之後,久沒見到如此「民國風」的武俠小說——當然【上京】的故事背景就發生在民初那灰與紅暗湧的大時代,同時和【俠隱】一樣,它有武俠小說的面子,裏子卻是關於微塵一樣的人在此狂潮裏如何自我教育、隱存或者犧牲的成長小說。
那個消失了的、說起來近乎不曾存在的北京城,自然也是其中主角,它的隱存或者犧牲同樣啟迪那個不願意在風沙中銹蝕的「夢生」——主角的名字並非槐樹南柯之虛無,一如當年的「虛無黨」其實是最勇猛精進的革命者。夢生寄寓的是作者李唐向往的小說裏憑空生長之力,以及曾經被寄予希望的一百年前中國青年的變革之夢。作為對後者的牽絆的北京城,竟然漸漸站在了青年這一邊,這也是李唐的詩意而非小說意之任性。
任性但美,這部詩意長篇,還讓我想到寺山修司的電影與詩,內有大量成熟到老氣橫秋的小說所缺乏的青澀之血,與百年前北京的雪相輝映。這是汲汲乎盛衰的當代人所難以理解的,其折現出來的蒼茫淒清的美感導向六個字:「置生死於度外」。如此說來,它又觸碰到了武俠精神的本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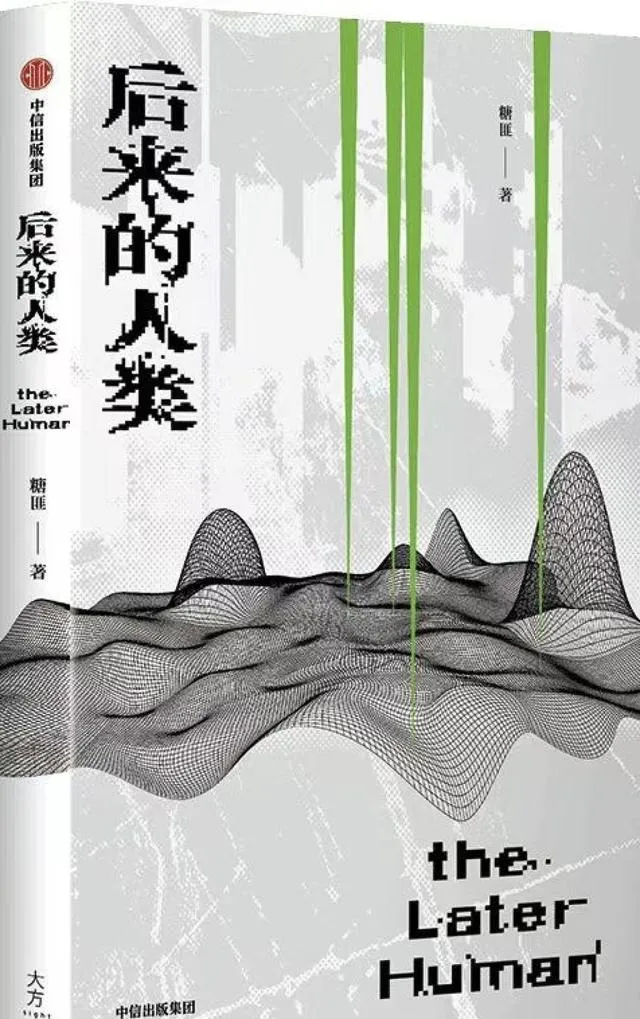
【後來的人類】,糖匪著,中信出版社/大方,2023年4月
今年我因為在大學研究院開設華文小說課程,重讀和新讀了數十本華文小說,最讓我耿耿於懷的,是課程結束後讀到的這本中篇小說集【後來的人類】。它的魅力是無以名狀的,盡管無論其「科幻」意義還是其現實意義,都給熱衷於在閱讀中尋求快感的人帶來不適。這種不適感曾經出現在【北京折疊】也出現在【瀨戶內海】裏,而前者走向主流思維,後者偏向地下文學趣味,糖匪超越了這兩者,同時比同道前輩韓松克制極多。
於是我們得以進入中國科幻罕見的蒼涼壓抑氛圍,從糖匪散文詩一般的後記可知,這跟過去幾年的封閉有關,但糖匪沒有屈從於絕望,她直面絕望而嘗試旁逸斜出,剖開的僅僅是現實,留白的是未來。她說自己是坐在路邊的科幻作家,「不飛,也不俯瞰」。但我不同意,她飛,只不過她不是以科幻飛,反而是以人情飛,正如【快活天】一篇寫到監視一切的「家神」時,她會問一句「家神能看見阿姆嗎?家神能看見鬼魂嗎?」也許是因為「她忍不住對大型家電產生共情,覺得它們像她,或者,她是它們中的一分子,身體神秘共振,暗中締結聯盟」。
【快活天】讀得驚心動魄,寫作技術精湛;但第一篇【看雲寶地】更叫人心有戚戚,表面上這是指涉人口老化問題,實際上它更接近魯迅的幽冷、決絕,涉及一個人該如何從這個世界結束而不謝幕的隱忍——這是每一個認真生活過的人都要考慮的問題,在這個取消尊嚴的時代。
而自然,也有批判和憤懣。三篇都涉及科技帶來的異化,但異化畢竟基於人欲,而克服也源自人之誌。後來的人類也是人類,他們不是我們的後代,而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握著自己的遙控器。
廖偉棠(詩人)
責編 邢人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