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眾號改版後,
為了方便大家以後找到我們,
不要忘記 「星標」 哦 ~
「
這場大雪似乎會持續到永遠,它們來自一團混沌的灰色旋渦,填滿了無邊無際的虛空,仿佛每一片雪都誕生於我感知到它的那一剎那。
-
[美] 菲利普·肯尼科特
」
最近幾天,你的城市下雪了嗎?
身在北京的未讀君,這幾天由衷感受到了大家的快樂,在社交媒體上也刷到了來自南方的羨慕。
不過話說回來,為什麽明明長大了,還是會像孩子一樣期待下雪呢?
每個人對雪的願景不盡相同,但一場大雪,能為我們帶來冬天最特別的記憶。
在你的印象中,哪場雪最讓人難忘呢?
在 柯克斯書評2020年度最佳非虛構作品 【復調】 中, 菲利普·肯尼科特 回憶起童年時的大雪,以及與母親不算美好的相處,坦誠成長歷程中的思考。

[美] 菲利普·肯尼科特|著
王知夏|譯
未讀·文藝家|出品
天還沒亮就開始下雪了,當鬧鐘在六點半響起的時候,地面上已經積了幾英寸的雪。學校停課了,我滿心歡喜。窩在暖和的床上,打著瞌睡,我暫時幸免於每天早晨去上課前都會填滿我內心的恐懼。
那年我十四歲,正在上初中,受到一幫殘忍暴戾、喜怒無常的校園混混兒欺淩。不過這一天卻屬於我自己。

母親關在自己的臥室裏不出來,這可是喜上加喜。早上起床以後,我下樓去她存放大學時代的舊藏書的地方,翻出了一本從未讀過的但丁。
我驚訝地發現它居然如此通俗易懂,很快我便迷失在他的【地獄】裏,為之驚心動魄,我又害怕又激動地邂逅了「忿怒者」「憤怒者」「褻瀆者」,看到軟弱善變的天使們太害怕在諸神的爭鬥中站隊,因此永遠徘徊於天堂和地獄之間。有的名字我認識——狄多、崔斯坦和阿基里斯,還有其他一些人名我完全沒見過——塞米勒米斯、忒瑞西阿斯,還有寧錄。我渴望認識他們所有人,這些富有魅力的悲劇人物來自不同的神話、歷史和傳說,被苦難聯系在一起。
然後我開始練琴,在走音的鋼琴上彈了一首舒伯特的即興曲——盡管已接近正午,我還是害怕驚動母親,故而專門挑了其中相對平緩的部份來彈。
到了午飯時間,母親依然沒有動靜,我只得走到她的門前,輕輕地敲門,請求她允許我給自己做個三明治。對我來說,餓肚子是家常便飯。

那個午後我美美地吃了一頓,直到饑餓感退去,而雪還是下個不停。 我想要沖進雪裏,盡情撒歡,感謝它為我帶來了記憶中最美好的一天 ,於是我決定給母親一個驚喜,自發把車道和小徑鏟幹凈。地上的積雪又濕又重,足足有一英尺多厚。
這活兒幹起來雖然累,卻讓人心情愉快,我一邊鏟雪一邊哼起了歌,哼著舒伯特和我最近學會的其他樂曲片段。我想象當母親發現我主動認真地完成了一項不討喜的體力活時,該有多麽吃驚,多麽高興。
在傍晚分時的灰色暮光中,我感覺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大功告成以後,我脫下靴子,把它們留在了前門邊上,然後回到自己房間,鉆進被窩裏接著讀【地獄】。

我又一次沈浸在但丁的書裏,突然間,我聽到她在喊我的名字。她向來如此,當我自己一個人在房間看書的時候,她就會變得焦躁不安。
她以前上過文學課,我看的書大部份都是她的,裏面遍布圓珠筆寫下的筆記,字型很小,運筆嫻熟,字跡漂亮。可是隨著歲月流逝,出於某種我永遠理解不了的原因,她開始對讀書產生了懷疑,尤其猜忌別人讀書。
我父親是通俗小說的狂熱愛好者,尤其偏愛驚悚小說和間諜故事,他習慣把書藏在屋子裏的各個角落,偷偷摸摸地看。
我年幼的時候,身體可以塞得進沙發和墻壁之間狹窄的縫隙,我常常躲在那兒看書,一連看好幾個小時,或者至少躲到她發現我不見了然後開始喊我的名字為止。
我總是事先就做好了閱讀隨時被打斷的心理準備,特別是在沒辦法把它偽裝成作業蒙混過關的時候。 對此我已然形成了一種慣性,無論何時只要我開始讀書,我的註意力就會分一部份去防備她的出現,時刻準備著被她打斷。
而她但凡知道我在看書,就會編出一件要我立刻去辦的事情,一些突然變得緊急的閑差事,什麽打掃車庫啦,把書架上的雜誌按大小和顏色排列整齊啦。
有時候,當她的喊聲驅散了我的白日夢以後,我走到她跟前,會發現她楞在那兒,一時間想不出什麽事來差遣我。她搜腸刮肚地想啊想,終於想出一招:把二樓窗戶的窗軌擦幹凈,用濕紙巾把客廳護壁板的凹槽擦一遍。我答道:「可我昨天才擦過了啊。」她這才死心,放我回去繼續看我的書。

這一次她喊我,我還以為會看到她眉開眼笑的樣子,甚至還能得到她的褒獎。可她的聲音卻帶著怒氣,當我跑到前門的時候,她已怒不可遏。靴子,只聽她說,任何時候都必須放在後門。「我們不是動物,」她嗚咽道,「我們不住在牲口棚。」
我從沒聽過這個規矩,可能是她在那天下午新制定的。我囁嚅了幾句鏟雪的事,她卻依然怒火中燒。她用兩只手扇我,打我的胸口,打我的頭,她讓我拿著靴子,沿著門廳把我一路推到後門。她個 子小,打人不怎麽疼,除非手邊有掃帚柄或梳子之類的工具可抄。
挨打是件丟人的事,但也無非是看著對方大吼大叫,揮舞雙臂,被摑幾巴掌而已。
可這一次,她的憤怒卻甚於往常,也有可能是她誤判了自己的力氣。
我就這樣被趕到了房子另一頭,那裏有一扇通向露台和後院的滑動玻璃門,我看到她的靴子整整齊齊地擺在下面的墊子上,於是我俯下身把我的放在它們旁邊。她一掌狠狠地打在我後頸上,我一個趔趄撲倒在地。我趴在那兒,臉貼著地面,雙臂緊緊地抱住頭。我哭了起來,眼淚讓我羞愧難當。我想對她大吼,要她明白她打傷我了,可我還在變聲期,從我嘴裏吐出來的話語只不過是孩子急促的尖叫。
「別他媽演戲了。」說完,她氣沖沖地走掉了。
我想,她大概是在生自己的氣,氣自己讓暴力失去控制,超過了平常的限度,我也生氣,因為我哭了。
我拼命喚回了我的尊嚴,哪怕在學校裏被男生們折磨毆打我也一刻不曾放手的尊嚴。我終於止住了眼淚,強行壓下喉嚨裏正在轉為啜泣的抽痛。我一點力氣也使不上來,不僅因為鏟雪鏟得太辛苦,更因為完美的一天就這樣毀掉了。
母親已逃回她的房間,房子裏又一次只剩下我自己。我在地板上翻了個身,仰頭望著天空,大片大片的雪花密密麻麻地從那裏落下來。

這場大雪似乎會持續到永遠,它們來自一團混沌的灰色旋渦,填滿了無邊無際的虛空,仿佛每一片雪都誕生於我感知到它的那一剎那。 它們讓我的意識變得迷蒙,我躺在那兒,在白晝逝去前的最後一絲光線裏,試圖想象自己身在別處。
我想跟我不存在的朋友聊聊但丁。我想找博覽群書的人請教一下,但丁的地獄為何誰也不饒恕。為什麽未受洗之人就必須受苦受難,哪怕他們為人正直,心地善良,一生完美如楷模?為什麽在地獄的現實和神怒的威力抹消了對上帝存在的一切懷疑之後,受天譴的人還是一個個怨氣滔天,滿口咒罵,互相攻擊,甚至反對上帝?我想,他們可能是在怨恨主,怨他的規則翻來覆去,怨他殘忍無情。他們也有自尊,他們都在心裏認定了一個事實:他們罪不至此。
我把這一刻定為我個人神話中的一座紀念碑。 從此我決定告別童年,至於這個決定是否確實是那個下雪天我躺在地板上做出的,其實並不重要。
我只是選擇以此來紀念那個時刻,即便不是那一次,它也必定發生在我人生中差不多的階段,也許是另一次挨打以後,也許是她當著別人的面打我——那就更讓人難堪了。 無論如何,我下定了決心,我不值得淪落至此,不值得這麽丟人現眼,躺在地上哭哭啼啼,生悶氣。
剛才我還讀著但丁,自主地承擔了掃雪的職責,我還覺得自己獨立了,長大了,誰知一轉眼又變回了小男孩,任由母親擺布。
於是我決定立即結束我的青春期,全身心投入重要的事情。 至於重要的事是什麽,除了但丁和舒伯特之外,我還不太確定。但我隱隱覺察到在書籍、音樂和藝術之中還存在另一種生活,比起將我引至眼下這個時刻、這種卑微境地的紛亂瑣屑的人生,那兒要充實得多。

那天下午我制定了自己的規則。我把母親設定為我的敵人,下決心再也不被她偶爾的親善迷惑,再也不跟她說任何重要的事,再也不要信任她。我看透了,如果不將她從我的生活裏連根拔起,她就會把我的人生撕成碎片。
我會行為端正,舉止得體,最重要的是不失體面。 可我知道我必須跟她保持距離。 我知道我必須遠走高飛,再也不回頭。
要將這些決斷付諸實踐並不容易。 我還要跟我的家人和這個家綁在一起好幾年,權宜之計就是以退為進,自我放逐,縮排一副沈默寡言、捉摸不透的軀殼裏。 而一旦有了機會和條件,我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做嚴肅、有意義的事,然後我開始嚴格地踐行我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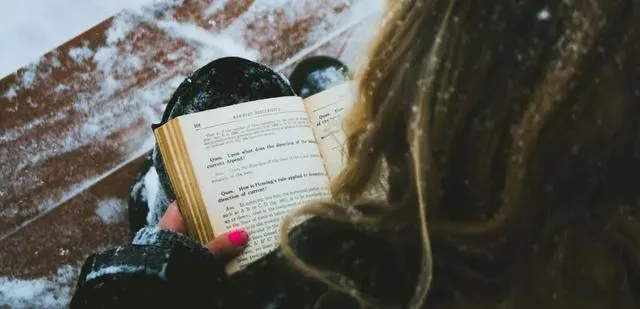
如今回想起來,把自己的情感生活建立在這樣一個東拼西湊的脆弱基礎上,此種做法似乎愚蠢得很。但我別無選擇,更何況隨著歲月流逝,借來的東西或許終將屬於我們,成為我們實實在在的所有物,如同我們生命中其他任何事物一樣真實。
所有的品位都是從別處得來,我們要麽主動在世界中找尋最佳範例,要麽下意識地將身邊的事物照單全收。
起初,讀書不過是一項生存技能,讓我遁入母親永遠無法尾隨我到達的玄秘之境,久而久之卻成了一種生活習慣,與我真正的自我意識融為一體。
說實在的,我並不喜歡看爛書,哪怕是消遣性的閑書我也不大愛讀;我也從未對流行音樂產生過絲毫興趣,除非有些歌與舊日戀情有著不可磨滅的聯系。 我依然相信每本好書、每首偉大的樂曲都蘊藏著救贖的希望,哪怕我心裏一清二楚,說到底這不過是一種迷信。

-本期話題-
你記憶最深刻的那場雪,發生了什麽故事?
留言區分享~

編輯| 泰若克塔
封面|【小森林 冬春篇】
圖片|網路











